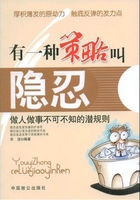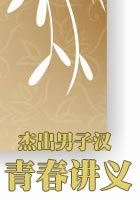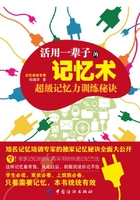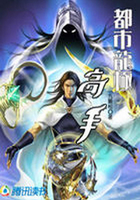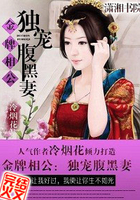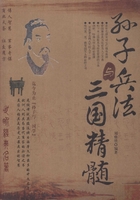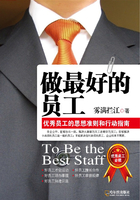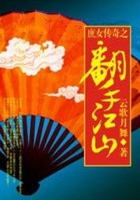在演讲的过程中,有一个应用蔡氏效应的策略,那就是适当留一些空白,会取得良好的演讲效果(蔡氏效应应用到演讲里叫作"空白效应")。在演讲中出现空白,听众的大脑就会一直想要完成整个过程,致使注意力不断提高。在广告学中,也可以应用蔡氏效应,所以广告都是插播的。插播广告不但不会给节目效果减分,反而会让你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电视机里看《甄嬛传》,比自己在网上看要爽得多,原因还是蔡氏效应:不断插播的广告,会让电视机里《甄嬛传》比网络上一点儿不卡、一点儿没广告的在线播放体验要"爽",这都是插播广告的功劳。
蔡氏效应的生理基础是这样的。人的神经链经过三次完整的行为就能初步形成,因为每一次完整的行为都能在两个神经元之间放一次电。每一个完整行为,可以细化三个步骤:要做这个行为的想法→进行阶段→做完,这三个步骤对应着两个神经元之间的放电过程:准备放电→积累电压→放电成功的过程。
比如要让醉汉形成"地板=睡觉"的神经链。我们已经知道两个神经元之间要有一次完整的经历,才能放电一次,之间进行第一次尝试链接;第二次再有一次完整经历,就再放电一次,建立一点点链接;第三次再有一次完整经历,使得神经链初步完成,就可以让醉汉认为"地板=睡觉"了。
而万一经历不完整的话,会怎么样?地板出现了,醉汉想躺下,放电准备;于是两个神经元之间开始积攒电能,积累电压,准备放电。一切就绪,就等他躺下就放电了……这时电话响了,他不得不去接电话。
一切都结束了吗?不。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电压还在,它没有释放!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积蓄着还没有放电的电压,会让神经元觉得憋得慌。而且,这个电压就永远存在在那里了,这就是蔡氏效应的生理基础。
一件事儿没有被完整地做完,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电压就会一直存在,总会有释放的需求。它才不管这个神经链是否能经历三次并最终形成,也不会管你是不是会觉得不舒服呢!反正这个没有被释放的电压的神经元是不舒服的,它会不断积累电压,不断提醒你:注意,这里还有活儿没干完呢。
有了电压,就得释放。你觉得这是坏事儿还是好事儿?我说,这只是我们的生理基础,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它让服务生记得所有没付过钱的就餐者,也让醉汉总有一天必须睡一次地板才行,它只是让任何事情必须完整地做完,必须被了结,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神经元之间的放电被延迟,就可以叫作"半途效应"。应用在成功学里,就是所谓的"大器晚成",积累的时间越长,爆发力就越大。英语里把这种人称之为叫作"lateboomer"(发育晚,一发育就爆发),或者叫作"蘑菇原理"。蘑菇原理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批年轻的电脑程序员。当时许多年轻人生活并不太理想,就经常自嘲"像蘑菇一样活着"。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失败者,而是"尚未成功者"。
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桑代克,他侧重研究惩罚性神经链,他认为学习就是试错,积累的错误越多,学得越多,成功越有可能出现;另一个叫作斯金纳的心理学家则侧重研究奖励型神经链,他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小步强化积累。比起这两个,我最喜欢科勒(WolfgangKohler)的顿悟理论:科勒把黑猩猩苏丹利关在一间放置着数个零散箱子的房间里,然后在屋顶上挂了一串香蕉,苏丹利怎么都够不到它。苦思冥想了数日后,苏丹利终于顿悟,它把箱子摞起来,并拿到了香蕉。黑猩猩的智慧是有限的,也没有得到任何来自科勒的提示,但经过几天的思索,它终于变"聪明"了。这也说明,两个神经元之间虽然不能放电,但是,积累的电压越来越大,总有会放电的时候;而一旦放电,就让苏丹利的智力得到了瞬间爆发式的突飞猛进。
美国艺术家摩西奶奶在退休好多年后,居然发现自己有惊人的艺术天赋,七十五岁开始学画,八十岁举行首次个人画展。于是神经元放电不成,又产生了个新词--"摩西奶奶效应"。
其实,不管是蔡氏效应、蒙太奇效应、顿悟效应、大器晚成效应、蘑菇效应、摩西奶奶效应……都在说明半途而废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美丽即美德:漂亮的人怎么会是罪犯?
美国心理学家戴恩做过一个研究,让人们看一些照片,照片上的人分别是具有魅力的、无魅力的和具中等魅力的,然后让人们从与魅力无关的方面去评价这些照片上的人,如他们的职业、婚姻、能力等。结果发现,有魅力的人在各方面得到的评分都是最高的,无魅力者得分最低。
"光环效应"是奖励性神经链的一个佐证。我们对他人的评价会被其外表所左右,如果一个人长得漂亮,那么我们的情绪就会良好。于是,所有把良好情绪打包起来的神经链都开始起作用,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应当拥有那些品质,比如善良、聪明、理智等等,直到有相反信息出现。所以,名人的丑闻,才能称得上丑闻,而我们自己如果有不好的行为,基本上都称之为不良习惯。
1977年,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E.Nisbett)开始对"美丽即美德"的现象进行调查,他们想知道耶鲁大学的学生是如何给老师打分的。
学生们被分成两组,分别看两段同一讲师的不同视频,要求学生们在看完视频后给老师的口音打分。这个老师有浓重的比利时口音。其中的一组学生看了这位老师西装笔挺地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另一组学生看了这个老师胡子拉碴地回答同样的问题。
第一组学生认为他的口音很有魅力,第二组则不然。而且,在重复试验的情况下,学生们试了很多次都给出了同样的评分,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评分。实验结束后,学生们被暗示,自己对老师的外表喜欢与否可能影响了他们的评分,但是大多数学生都解释说,他们对老师口音的判断,完全取决于他说话时表达是否充分,和他的穿着打扮与长相等外在因素完全没关系。
同理,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的"陪审团"饱受诟病,因为一般长得漂亮的、帅的嫌疑人,经过陪审团合议,都会和法官的判断相差甚远。
中性神经链:你不打呼噜我怎么睡啊?
最近有人对猴子做研究,他们带来一只猴子,把它一只手的四根手指压住,在另一根手指(大拇指)上掰来掰去。一次又一次地做,做了成千上万次之后,就发生有趣的事情。你每次弯动猴子的这根手指时,都可以想象是在猴子的脑袋里把神经元一个个地连接起来,动一次猴子的手指就做一次链接,动两次就做两次链接,做了成千上万次之后,猴子此时已经被连线好去这么动了。
--选自安东尼·罗宾的演讲
奖励性和惩罚性的神经链形成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是中性的,和情绪没有关系的。有些人的脑袋一碰枕头就犯困,有洁癖的人看到脏东西就擦。还有个故事是这样的:老婆埋怨了老公一辈子,说他睡觉打呼噜,老公就去开了好些药,很管用,但老婆晚上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最后忍不住大叫:"你不打呼噜我怎么睡啊!"还把他的呼噜药都给扔掉了。
中性神经链完全依靠不断的重复行为所形成,它能使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形成的过程会比较慢,但是一旦形成就会牢不可破。张大千是个大胡子,胡须垂到肚子上。有人好奇地问他:"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被子外面,还是被子里头呢?"他一愣反倒答不上来了。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胡子先放在被子外头,觉得不对劲儿;又放在被子里面,觉得不自然,结果一宿没睡好。同时还说明,中性神经链对睡眠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如果每次躺下就睡,不困不睡,那么枕头和睡觉之间就建立了稳定的中性神经链;反之,如果人们总是躺在床上看电视,倚着枕头看书,就会建立起"躺在床上+不睡"和"倚在枕头上+不睡"的稳定的神经链,从而破坏"枕头=睡觉"的神经链,因为那中间的部分正储存着我们最顽固的习惯。
固执的中性神经链在我去西藏时发挥了作用。记得第一次吃糌粑的时候,我觉得很腥,吃了特别不舒服,其实这就是神经链在捣鬼。看起来仿佛是身体在拒绝糌粑,但是身体怎么会拒绝脂肪和淀粉呢,拒绝它的实际是神经链,是神经链认为这不是食物。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助手去拜访某个社区里三分之二的家庭主妇,让她们把一个小招牌挂在窗户上,有一半人答应了;过了半个月,助手再次拜访这个小区里所有的家庭主妇,请她们把一个大招牌放在庭院内,这个牌子很不美观,之前未被拜访的那三分之一主妇中,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同意放大招牌;而放过小招牌的家庭主妇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放大招牌;曾经没同意放小招牌的家庭主妇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同意放置。弗里德曼把这种现象叫作"得寸进尺效应",是中性神经链的一个变形应用。
这个原理还有很多叫法。比如"温水煮青蛙效应":把一只青蛙放在沸水中,它就会一下子跳出来;把它放进温水,然后再慢慢升温,青蛙就会一直若无其事地待在水里,直到被煮熟;比如"秃头论证":如果发生"鬼剃头",一夜掉光头发,或者是某个理发师技术不到位,没把顾客的头发理好,到最后只能给他剃个秃瓢,人们就会暴怒、恐慌;但是,如果人们只掉了一根头发,就不会那么担心;再掉一根,也不担心;慢慢地也就觉得掉头发是很正常的事情,最后变成秃头了,也觉得是正常结果。再比如,往一只骆驼身上放一根稻草,骆驼不会有负重感,再加一根,骆驼还是没有反应,又加一根……直到最后一根轻飘飘的草压到骆驼身上后,骆驼就被压趴下了,这就是著名的"一根稻草压死骆驼"的谚语,又叫"稻草原理"。
从中性神经链的形成角度来讲,各种仪式都是很重要的,绝对不会形同虚设。比如在封建社会,娶个媳妇要三媒六聘、八抬大轿、跨火盆、射三箭……虽然夫妇双方都经媒妁之言,在洞房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多数都会厮守终生、相扶到老。为啥?经过这么多道仪式,中性神经链形成得太牢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