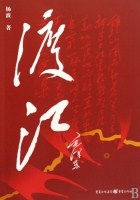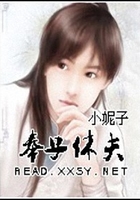四、个人的与人类的、诗人的和学者的、风格与个性
在当今,一个作家的著述20年之后甚至是在10年之后,不被人们看成是陈腐得可笑的、散发着时代异味的,已经很少见了,大多数作品面市一年两年之后就淹没于汪洋般的出版大潮而不见。这是否是作家这个职业的宿命?从事文学创作在当代是否注定要领受被遗忘、被漠视的命运?难道作家这个职业的特征不正是以永远价值、不朽业绩为特征的吗?作家们曾经沉醉于其中的那些作品,那些散发着激情的文字是否就注定会被当成信口开河?也许我们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例子,如曹雪芹、施乃庵、鲁迅等等,然而他们的命运又能好多少呢?纸面文学作品的读者正被电影、电视掠夺而去,文学家及其作品正被主流媒体逐渐淡化,这难道不是不争的事实吗?
这实在值得我们就作家这个职业思索一番。作家何以写作?他的创作在什么意义上有价值?他为谁写作?进而作家在何处得以安身立命?过去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
作家一方面应该是一个诗人,另一方面他还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深邃学者,他应同时具备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深邃,他应是诗的想象与哲学的思辨的混合。从本质上说他应该是社会上最具有历史感的那一种人,他们不仅为现实写作还为未来写作,不仅为民族、国家写作,还为人类写作,然而为什么事情恰恰相反?他们的著作成了这个时代最没有历史承受力的?
作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埋头捕捉各种生活细节,沉湎于生活表象的那种人,他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历史风云际变,在现实的人生声故事中感受世态的变幻无常。但是,很显然仅有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对人类历史等外部客观的兴趣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与观察者主观没有关系的客观生活现象,作家所要揭示的并不是生活表象真实,读者对这样的真实并无多少真正的兴趣。作家,只有从他的对人类、对历史的整体性柔情和关怀出发,让自己博大的历史悲悯和人类情怀照亮眼前的事事物物,按照自己对于人类的整体性立场来关照生活表象,以一个爱者、思者、超越者的身份去展示过去、描写未来、揭开当下的时候,我们说他才真正地获得了写作的立场。
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他才获得了卓然独立的作家人格,他的写作风格才不会因为一个阶级、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盛衰而随波逐流地亦盛亦衰,他的风格才能在超越历史的意义上为更多时代接受,他的语言才能横跨有限的时空跟几乎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文学艺术精神生活紧密关联。
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事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不同于前代也不同于后代的独特的时代命题,这些命题对于人类来说也许仅仅当下才是有意义的,超越了当下的语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于这样的当下性命题,作家们是否应当拒绝呢?难道它不应当放弃或者反对吗?不应当从历史的高度和人类的广度上来选择他的题材,而拒绝那些注定要被淹没的时效性材料吗?不是如此。比如鲁迅,如果他不是那么深切地对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心,就不会去写杂文,今天,尽管我们会说鲁迅在杂文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应当把精力集中于小说创作,鲁迅过度关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人类使命、超历史使命云云,但是,换角度而言如果鲁迅不是那么真切地观察了他的时代,他如何能在小说创作中捕获得对人类、对历史的种种超越性见解呢?他把中国封建史概括成“吃人”的历史、用“阿Q精神”来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等等,都是来自于他对其时代生活的敏锐观察。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类视角实际上都来自于个体视角、民族视角、国家视角。但是,反过来我们又要说,任何人类视角、历史视角都不仅仅只是个体视角、国家视角、民族视角、时代视角,而是对这些视角的超越。
但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要为自己的时代作出牺牲,他不仅要为超越的世界写作,还要为现实的世界写作,就如同哈维尔、索尔仁尼琴、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一样,他们为未来而写作,同时也为现实而写作,并愿意为此而付出重要代价,有的时候甚至为此而流放、监禁和牺牲。就如同鲁迅一样,他们不仅是文学家,同时还是革命家、思想家,人民为此而永远牢记他们,他们不仅仅用语言在大地上竖立起了自己的丰碑,同时还是斗争的意志和反抗的呐喊为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奠定了不朽地位。
换而言之,作家必须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他的历史感是以灼热的现实情情怀为基础的,也许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实情怀还更重要一些,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与现实进行对话,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纯粹的历史兴趣(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历史兴趣)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必要的,也许那种口口声声声称自己为历史、为未来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恰恰是最没有永恒价值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发展史已经说明那些在专制、暴力、压迫面前用沉默表示了认同的作家,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作家,那些没有为人民鼓呼的作家,几乎都成不了什么大气,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可以生活得很好、很有地位,但是离开了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便会像他们的生命一样被时光抛弃。
作家是否应当抛弃自己的偏见?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站在更为普遍的立场上,作家就要改造自己、抛弃自己,把自己改造得越是彻底就越好,真是这样吗?事实上那种纯粹的不受个人偏见左右对于生活和历史的观察是不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与认识的可能都要受到三个先决因素的制约。一是“先有”。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经先占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占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这种存在上的先有作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发生的先决条件,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现实、历史、文化和传统。二是“先见”。它是我们在思考和理解时所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和运用语言的方式自身会给我们带入先入的理解,这种先入的理解将参与我们所有的理解行为并影响其结果。三是“先知”。在我们理解和认识新的事物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推知未来的起点和参照系,它是理解和认识得以发生的前提。[殷鼎:《理解的命运》,第26-27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海德格尔的这一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作家,作家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的主观性不仅表现在对已有对象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两方面,而且甚至还表现在一个作家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上,“每一个主体总是选择符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的那些东西作为评价的对象。”按照现代解释学者加达默尔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受人的有限性与历史性的制约的所谓的自主的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历史的直接缠绕与伴随这种缠绕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主体,针对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某些说法他反问道:难道仅仅通过采取一种态度,认识者就真的能使自己离开他当下的情景吗?加达默尔认为历史性并非仅仅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偶然的和主观的条件而是一种本体论的条件,在历史理解的一切过程中早已本质地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事实上,现代解释学,把认识者束缚于自己当前视域的特点以及认识者同认识对象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一切创造性理解的基础而不是作为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和障碍来认识的。我们的偏见并非使我们与对象相隔,而是使对象向我们开放,它是社会认识得以进行的积极条件。正是这一意义上加达默尔说“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9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总而言之离开作家的当下的历史处境和偏见作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认识,因此这种当下性和偏见性并不是作家必须要克服的。[ [捷]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第73页。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8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对于作家来说解决了这一点,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曾经论证了,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个人视域,因此作家只能从自身的视域出发来写作,但是作家又必须服从人类的义务,这两点如何统一呢?理由是这样的,黑格尔曾经很好地论证了类与个体的同一性,类的历史就是个体的历史,类的特征就是个体的特征,如果黑格尔在这个说法没有错误的话,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就会发现作家深入自身作为个体的深处,也就深入到了类的深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挖掘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二元分裂也就历史性地道出了人类的二元困境的问题。就如同作家在解决历史关怀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困境时,必须把现实关怀作为历史关怀的必要步骤和方法来认识一样,在类与个体的夹缝中,作家也必须把个体当作通达类的方式和方法,类不在抛开了个体之后的彼岸,而就在个体之中。由此出发,他应当深信,他真诚地代表了他本人说话,说了真话,也就代表了类,每个个体真切地代表了自身,那么人类也就在这“个体”自然而然地见出了。从这个角度,法伊尔·阿本德的“所有的人都是个人[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第3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换一个思路,“客观的真实是否存在”、“作家是否可能超越个体立场”的问题也可以转换成“谁能代表客观的真实”、“谁能代表人类”的问题来讨论。我们承认那个客观的真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谁能代表那个绝对客观的真实说话却是有疑问的,也许在人的世界里,我们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人类说话,代表的方法是“不断地返回到他自身去”;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进一步说,正是无数个“我”的众声喧哗,合成了“我们”(人类)。质而言之,作家只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人,他代表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但是,同时他又是有诚实的自我质疑精神的人,他知道在自己说的同时还要让别人说,听别人说,这样就构成了平权的、民主的文学话语场。
文学家在什么情况下是一个考据家,什么情况下是一个幻想家?他对事实取的抱考据的态度,不着一个没有来历的字,不写一句没有依据的话,他放弃一切想象、猜测、抒情、同情的权利,他小心翼翼地克制着他自己的情感,以防他的情感阻碍了他的严谨考究。这是否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显然这不是文学家对待事物的态度,但是在现实中,恰恰有许多人这样要求文学家,要求他们像历史学家一样记录人类历史,像社会学家一样考察社会变迁,我们说这种要求对作家来说是不合理的。一个文学家,他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他应是一个对历史与现实都同样满怀深情,他关注的种种也就是他同情的种种,站在现时回望历史他毫不吝啬他的悲悯之情,他也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关注、当下的关注超越了对历史总体的关注,他对个人的关注超越了对阶级、民族、国家的关注,他更愿意站在全民的立场上,站在先进文化的立场上,站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上来看问题。作家不仅不把自己从对对象的体认与同情中拉出来,相反他们是将自己放到与对象同样的立场与对象作同情式的心灵沟通,如果说他是在反映一个时代的话,那么他显然是通过主观心灵史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的。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描述单位应该是什么?独特的“这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这是他的观察基元,他是从“这一个个人”(典型)身上直接见出人类生活的历史继承性、人类精神的内在矛盾性,呼唤他所呼唤的、指斥他所指斥的。他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机械的演绎来研究生活的,而是通过“这一个”独特的典型来诗意地整合生活的,他凭借他的直觉一下子就在“这一个”的身上看到了一切,而不是相反。他用诗性思维认识他的对象,他用想象力、同情心来抒写他的对象,他让自己的灵魂越过历史时空在自己的文字里爆响,他和自己的主人公一起探入人生的深渊,从更深的生命底层来体验它、承受它(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在这个过程中,他注定要经历和主人公一样的心理历程,他将和自己的主人公一道承受时代赐予的悠长无止的苦痛。也因此,他们——在精神上要活得比常人痛苦百倍,对于这样的灵魂,教条的说教,一个没有相应的对于生命的深渊般体验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加以认识的。
作家是那种具有对人的本体性关怀,以人的本体论为中心,揭示人的存在价值和本体意义,进而张扬人的生命意识的人,对于那个大写的“人”来说,他是解释学家,而不是批判家,只有在对那个“人”所生活的环境“社会”而言的时候他才是批评家、否定家。他只会永远地赞美那永恒的人性,批判那压抑它的一切,而不会对人性的光辉说半个“不”字。他应当具有博大的宗教情怀、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对世界之道的苦苦追求,但同时他也是把这些奠基于对“人性”的解释学基础上的。
历史的深处就是现实,个人的深处就是人类。一个真正的作家他必须具有博大的类意识,他不仅为他所处的时代言说,还为整个人类言说,他的超越性追求、人类学情怀、彼岸精神、终极取向是他创作的动力,并且他把这种动力焊接在他对单个人的生命的同情式体验上,他不仅是一个热爱现实的人还是一个热爱未来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热爱个体的人还是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他追求个人性和共在性的统一,他视文学艺术是存在的敞亮,存在的去蔽,他将作家的使命理解为将这种去蔽与敞亮的真理昭示给人们。由此,他就获得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史的参照,他的创作也就得到了博大而恢宏的历史意识、人类意识的支持。他的创作目的由此而上升为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法则的苦苦追寻,他的工作是他向着人类的变动不拘的生活之中的永久性质素的一种询问,为“人”的整体的诗意的栖居寻找坦途,成为他的创作的所致力的最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