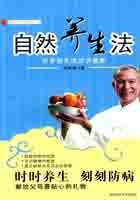姜云霄在天香阁等了足足两个时辰,直到了掌灯时分这才瞧见她的木鸟由半开的窗户飞了进来。只见她抬起左手面,那只鸟便乖乖地停在了她微翘的食指上,她用右手拨弄了下鸟喙便听其腹部传来顾连城的声音:“云娘,那日我已将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虽说敬王府并非久留之地,但我只求在这里暂时安逸度日,早日钻研出人偶秘术,完成师父的心愿。至于您今后有什么打算,连城不愿参与其中,他日若真能完成秘术,我自会回北漠重振师门!保重、莫念!”
听完顾连城这番话,姜云霄无可奈何地轻叹一声自言自语道:“这丫头的脾气较两年前倒是变了许多,兴许也算是一种成长吧!”
她想既然时机未到,也就不必操之过急。自打两年前到这京城,她摇身一变成了这天香阁的主人,虽说时间并不算长久,但其间也打探了不少消息。毕竟是烟花之地,招揽来的大多是前来寻花问柳的王公贵胄,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些什么也并非难事。现今趁着世事太平,要为以后的事情早做安排。当年顾连城得了千机派掌门真传之后,她便在心底暗暗谋划,她相信,终有一日,凭着顾连城与她的机巧之术,她姜云霄定能得偿所愿。
当晚,敬王齐澈破天荒地与顾连城一起用了晚膳。顾连城打小与师兄弟们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并没有觉得哪儿不自在,但今日与齐澈独处这么一会儿让她觉得有些别扭。她不能坦然地去面对他,眼光偶尔落在他俊逸的面庞后便慌忙移开,若是多瞧他两眼便觉双颊发烫、心跳加速。想到前些日子还与他剑拔弩张地斗嘴,而现在却忸怩不堪,顿让她心里头觉得疑惑不解,许是现在的他突然变得温柔亲切令她有些不知所措吧!
晚膳过后,齐澈仍没有离开的迹象,反倒是极悠闲地从书架上取了书翻看。顾连城只爱看些民间话本,对于书架上的那些藏书并无兴趣,无奈不知该怎么打发这二人独处的时间,也只能随意地找了本百无聊赖地翻瞟上几眼。
约莫到了戌末时分,顾连城正困得上下眼皮打架,冷不丁听齐澈丢来这么一句:“我今晚要在这里歇了,你若是困了可以先睡下。”
顾连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一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虽说当初走投无路时她已抱定卖身青楼的决心,所谓的处子之身对她来说自然没命重要,可是如今事发突然,她一时还真无法接受。
齐澈瞧见她神情紧张,不由挑唇而笑,心里头却是百味杂陈。他知她已不是完璧之身,早先他那位皇兄与她春宵共度,未及封她为妃便被他抢先请旨赐婚,软磨硬泡之下他才无奈答应。当年是他这位皇兄生生拆散了他与郑锦瑟,而他所做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顾连城正要强打精神继续翻看手中的书卷,却见齐澈向侍立于殿门边的宝珠使了个眼色。不多会儿便见宝珠走近附在她耳边说:“请王妃更衣沐浴!”
长于北漠的顾连城自小对当地干燥的气候无法适应,每日养成了沐浴泡澡的习惯,即使到了京城也仍是如此。宝珠虽一如往常地伺候她入浴,但在这当口却令她倍觉尴尬,顷刻间只觉得浑身血液上涌,双颊也开始微微发热。
沐浴之后,她仍着了平常的素衣,并声称天凉找宝婵要了件袍子披上,这才磨磨蹭蹭地回了寝殿。瞥见齐澈仍坐于书桌前翻阅书卷这才稍稍安下心来,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掀起铺于床里面的那床锦被钻了进去。她心里有些慌乱,索性又往床角挤了挤,整个身子隔着帐幔几乎要贴到了里墙上。
齐澈的心并未放在手中的书卷上,他时不时地用余光观察着顾连城,见她如猫一边裹着被子缩于床里,心内觉得好笑。这般幼稚的举动,他还真是第一次见,顿时让他起了捉弄之心。他假装打了个哈欠,低声换了宝珠捧了热水来用,之后便命她掩门挑灯而去。
顾连城缩在被窝里,却一点睡意也无,竖着耳朵听着室内的动静,不知不觉出了一身的汗。直到齐澈走到床边坐了,她下意识地又往里缩了缩,紧张得浑身发抖。
齐澈一身月白睡袍,乌亮顺滑的头发披散于肩,偶有数绺垂于两鬓,更显得俊逸脱俗。他望着床角的一团,唇边笑意更浓,若是可以,他真想放声大笑。他刻意加大动作的幅度,躺下的时候往床里挤了挤,而在床外边留下了好大一块空地。
顾连城努力地将自己缩成一团,整个人又往墙边靠了靠,紧裹的被子闷得她差点儿喘不过气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她实在受不住被中的闷热,悄悄地由被中探出头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凉气透着鼻腔吸入肺腑,顿时令她倍觉舒爽,也让她就此下定了决心。横竖都逃不过这一天,与其畏畏缩缩的倒不如鼓起勇气接受,比起女子的贞洁,她觉得小命更为重要!
她这厢内心挣扎不已,而睡于身侧的齐澈正以肘支着头优哉游哉地观察她这边的动静。见她忽然探出头来,忍不住开口问了句:“现下虽是秋日,但也不至于这般寒冷,你将被子裹得如此严密就不怕热吗?”
顾连城才刚舒了口气,忽然听他发话,觉得装睡太过虚伪,索性坦然地扯下覆于头上的锦被答道:“方才吹了些冷风,因此觉得身子凉,现在好些了!”
“哦?可别是受了风寒!”齐澈装模作样地伸手要触上她的额头,惊得她慌忙往被中一缩,顿时他的手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