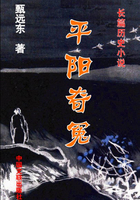一
六月的北半球,正是草长莺飞,生机勃勃的时节。此时的我,正坐在国航北京至洛杉矶的航班上,飞机巨大的轰鸣和被窗外云上的夕阳染红的舷窗并没有让我感觉多么的兴奋。
起飞已经十多个小时,我坐在机舱正中间的座位,右边是一个美国胖子,此人只穿一件超人的文化衫,大大的“S”将腹部的赘肉衬托得有一丝讽刺。他一边大嚼特嚼飞机上发的零食,一边抓着自己那一圈有着黑泥的脖子并努力让自己肥厚的臀部舒服些。左手边则是一个在北京做传销的大妈,目测岁数在50岁上下,拿着看不出真假的“驴”牌手包,全程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为我勾勒着未来。被他们夹在中间的我只感觉呼吸粗重,昏昏沉沉,倍感压抑。连空姐发的入境的I-94卡都填错了两次。
在一阵颠簸后,飞机终于落了地。虽然我对美国无甚好感,但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闻着机场泥土混合着机油的味道,我着实感到了一阵内心的悸动,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梦?我问自己。当然,是一个没有传销和垃圾食品的梦。
明天开学,今天才落地洛杉矶。即将开始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生活,我却一点也不兴奋。我找了无数借口,在北京拖到最后一天。家人的理解是,从来都没有离家这么久,肯定是不想走。但其实是,我恋爱了。头一次,真真正正地爱了。
正对着我家门口有家雕刻咖啡馆,里面的装修是我喜欢的风格,全木制地板,木头桌椅,楼上还有几扇大落地窗。每到下午,阳光就顺着窗户一缕一缕地射进来,照着空气中飞扬的灰尘,让人心中暖暖的。我有时喜欢坐在楼梯边的那张小桌子旁,有时则喜欢倚靠在楼上落地窗旁的大红沙发上。
从结束申请留学后,我几乎每天都会耗在这里看小说。也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老头。
这是我来这家咖啡馆的第三天。对面那个被电脑屏幕挡住了半张脸的男人,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光头,屏幕的光亮打在他的脸上,再散射到他的光头顶,会让我想到“佛光普照”四个大字。他脚上的那双绿条白底的旅游鞋,和身上的一条居家的宽松黑绒裤,让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别扭。他的电脑旁放着一大杯牛奶,这是他每天在这里享用的饮料。当他认真严肃,操着带有磁性的声音向服务员说出:“我要一大杯牛奶”的时候,都会“勾引”走我的目光。除了发型,他的动作、行为、声音、眼神,包括喝牛奶的样子都能让我想起那部至爱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男主角。
我来咖啡馆的第五天是个周末,楼上楼下满满当当。那个男人坐在楼上窗边的一张双人小桌旁,他厚厚的黑色羽绒服充满了他身边那个空椅子。我从他旁边擦身而过的时候,一个声音将我叫住。
“坐这儿吧,我把衣服拿走。”他边说边把羽绒服塞到了自己的身后。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在礼貌地道谢后,坐在了他的身边。
我掏出小说,用余光偷偷打量身边这个奇怪的男人。从他“沧桑”的面相来看,年纪应该在三四十岁。他鼻梁很直,大眼睛双眼皮,低头的时候还能清晰地看到那对长长的睫毛向上翘起。对于我这种没鼻梁又小眼睛单眼皮的女孩来说,每当身边出现了这种人的时候,心里全是无法言表的羡慕嫉妒和恨上加恨。老男人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骨节清晰。我自幼与大众的审美不同,除了不喜欢长得帅的、有肌肉的男人外,还比较偏爱男人的手。要是这人的手好看,手够MAN,我就会下意识地觉得他人也很帅。自打成年后,我的这个逻辑曾让很多兄弟姐妹都折服过。
自从我坐下后,这个男人一句话都没说。他一直盯着电脑,时不时端起手边的杯子,喝上一大口牛奶。我悄悄地探了探身,试图看清他的电脑屏幕,但他敏感地突然转过头,瞪着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的上半身情不自禁地往外一闪,后背却吓出了冷汗。可能是因为这个惊慌失措的表情和夸张愚笨的肢体动作,逗得他左边的嘴角向上翘了翘,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看什么呢?”
“没……没看什么。”我更加不知所措。
眼前的牛奶让我有了台阶。
“你怎么这么大了还没断奶,像Leon大叔一样。”
男人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嘴角又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再一次拿起“奶瓶”喝了一口。
“我看你每天都在这儿。”我故作平静地低着头问他。
“家里太乱,我不能安心工作。”
“你不用上班吗?”我继续问道。
“不用。”他头也没抬地回答。
“噢,是个淘宝大叔……”
男人看了看我,认真地说:“我是个杀手。”
“噗”,我嘴里的半口咖啡喷了出来。
“我在写个杀手的故事。”
“作家?”我愕然。
“编剧,称不上作家。”
“差不多吧。能动笔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我感叹。
男人淡淡一笑,便又没了声音。
我惊讶地看着他。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观察,我都觉得他的外表跟写作这件事毫无关系。一个长相如此粗犷,身材瘦高,剃了光头留着碎胡子的老男人竟然是个靠文字吃饭的文艺男,真是让我们这种正在崛起的文艺小青年们大跌眼镜。但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正面直视他。他的脸很瘦削,嘴唇微微有些厚度,鼻梁笔直,眉骨清晰。可以说他强硬的眼神是他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但这一瞬间,当我看到他嘴角残留的那一抹白色奶沫,我似乎感觉到,像Leon一样,他应该也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
从这天起,我们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坐在一起。起初,他会跟我聊起他的工作,回答我提出的所有幼稚问题。之后,他会跟我聊聊年轻人的人生,他的朋友,他的爱好。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是那样的有道理。他所表现出的诚恳,他对事情的分析能力深深吸引着我这个不经世事的小姑娘。我对眼前这个成熟的男人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最后,他终于跟我聊起了他的家庭。
那又是个周日的中午,咖啡馆里一个座位都没有了。我们一起溜达到了不远处的星巴克,坐在了马路边的露天铁桌旁。
原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是他38岁生日。他25岁第一次结婚,婚后便有了个小女儿。之后他一直忙事业,28岁那年,老婆红杏出墙提出离婚。死扛了两年的他还是没有逃过命运的捉弄,在30岁那年领回了离婚证。
他是个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患者,但人却很简单。他不但极易相信别人,还不会把人往坏了想。离婚后,他一人来到北京重新开始。后来,他因工作在外地认识了一个女人。两人在一次酒后发生了关系,不久以后,她居然挺着肚子来到了北京。他母亲反对。但他却不舍得了,心软了。在纠结了五个月后,他们俩领证了。
这个原来对家人关心有加的女人开始变得脾气暴躁。不管他买了多少新玩具、新衣服给刚出生的小女儿,女人都觉得他们家人只爱大女儿。她急了就会骂人,还会打孩子,甚至会对他说出:“如果你不把你的咖啡壶放在柜子里,哪天烫着我女儿,我就在你睡觉的时候用开水从你头上浇下去。”
最后,他决定离婚,女人不知为何,跟发疯似的成天不但自己闹着要死要活,还嚷嚷着要掐死孩子,他对这样的生活绝望万分。无奈之下,他把她们送回了娘家。虽然他当面告诉了她的家人自己决定离婚,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女人关于办理离婚手续的通知。
他的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
从他们闹开了以后,他便把咖啡馆变成了自己的书房。这里安静,放松,适合创作。最主要的是,那个家,让他精神崩溃。他说他来咖啡馆的第一天就因为我手中的小说注意到了我,因为那本书他刚刚看过。
通过每一天的交谈,他已完全得到了我的信任和青睐,包括从他口中得知的所有关于他家庭的情况。我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不够理智,也知道这样一段感情中所存在的巨大风险,但十天以后,我们还是接吻了。
二
“心怡!”一特响亮的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
“这儿呢!前面!”我转过头,往前一看,原来是小白脸。
小白脸,我的发小,在美国读书已四年。现在虽然毕了业,但还没想好接下来的路。所以,就先继续在美国当混混。小白脸在人群中特别显眼,一是因为他的皮肤又白又嫩,二是他人长得又高又帅。再加上,洛杉矶这地方本来老墨和黑人就多,所以更能显出他的这些个优点和优势。
“辛苦辛苦!欢迎来到美国!”小白脸一边接过我手上的推车,一边满脸堆笑地说。
“你在这儿养得可以呀,脸蛋儿嫩得都能捏出水儿了吧。”刚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再加上被海关“戏弄”,看见小白脸心情又好气色又好,我马上毒舌怨妇上身,还做出了想狠狠用手捏他的动作。
“大小姐,谁又招着您了,我已经努力表现出我的全部欢迎之情了。”小白脸向后一闪,赔笑道。
“美国人都无聊疯了吧。刚才那人一看我听英语特紧张,就不停地问我各种没用的问题。要是觉得工作无聊就别干了,反正这儿福利也好,干吗折磨人玩儿呀!”我咬牙切齿一脸凶相道。
“哪个人!找死呢吧!敢招我曹姐!我跟他拼了!”小白脸边说边假模假式地拉着推车往回走。
“行了行了,别得瑟了。赶快吃饭去,饿死我了。国航的饭闻着就想吐。”我真是饿得快犯低血糖了,边说边拽着小白脸往外走。
“得嘞!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众朋友也已经在等您了。咱走着!”
我三年前跟家人来过洛杉矶旅游,当时就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现在又一次坐车走在这条坑坑洼洼的高速公路上,毫无激动之情。
就是在三年前来美旅游的时候,我那神妈认识了一个同团的徐阿姨。她自己报团出来逍遥,儿子却在准备出国考试——万恶的GRE。这个阿姨很是能说,在为期七天的美国游中,徐阿姨列举出了种种出国留学的好处。我妈本来就属于典型的顺风倒,没主见,再加上自己就出自名牌大学,一直对我只考上了二本院校感到不满。
听着徐阿姨滔滔不绝地说着留学之路的光明前景,我知道,我妈完全中招了。“你看看现在,研究生算什么,博士都满街跑了!女孩子不用太高文凭,但读个研究生还是很有必要的。不说找不找得到好工作,现在没个研究生文凭连老公都找不到像样的……”徐阿姨兴高采烈地说着。我在一边不停地用嘴吐气,试图控制自己随时都会爆发的情绪,但嘴上唯唯诺诺哼哼唧唧地说我知道,我那悠闲自由的生活结束了。
“到了。”
我的思绪又被小白脸那难听的、垮了吧唧的嗓音拉了回来。抬头一看,“南海渔村”四个大字摆在了我的眼前。再环顾四周,视线所及全是各式各样的中国餐馆。
“这是……美国吧?”
“洛杉矶是咱华人的天下,这只是一小片,慢慢再带你一家家吃去,在这儿就没有你想吃但吃不到的中国菜。”小白脸自豪地说。
我们刚走进餐馆,一个长相很干净的姑娘迎了上来。她一头瀑布般的秀发,玲珑有致的身材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你好,我叫程宣,早就听他说过你,说你是唯一一个能跟他拼皮肤的姑娘。”程宣上前热情礼貌地跟我握手。
我打量着面前这个小白脸的现任女友,完全被她的话说愣了。
“还有你梦寐以求的小姐姐。”
小白脸话音未落,站在后面的一个姑娘便走上前跟我来了个久违的拥抱。
“可算来了,想死我了。”
她叫李易童,是我的小姐姐。我妈跟李易童的妈是十多年的同事。李易童18岁就来美国读书,至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九年。生活独立性格坚强的她,现在在一家很牛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持有美国绿卡。四年前小白脸刚来洛杉矶的时候,就是李易童帮他安顿的。因此,小白脸一直对李易童心怀感激和崇敬之情。
“我想你飞机上肯定吃不好,刚下飞机肯定还是家乡饭顺口。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带你去趟超市,买点吃的用的。”李易童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
去完超市,三人把我送回宿舍已经晚上12点了。这个宿舍三室一厅,听说是跟一个台湾“四眼儿”合租。
我走进这间属于我的房间,屋子很小,摆设简单。一张单人床,一架落地台灯,一个书桌,紧挨着书桌的是一个两层小书架和一把木头椅子。
“还行吧,这可是我当场拍了一千五百美金才抢来的房。”小白脸笑眯眯地说。
“挺好的,谢谢你们。”我真诚地点了点头,以表感谢。
“不用,你先将就两个月。等你有了车,我们带你去找好的房子。”程宣笑着说。
“你收拾收拾就赶快睡吧,这都12点了。明天等我下了班来接你吃晚饭。”李易童边擦着桌子边说。
我有洁癖,自认为年纪越大,反而越严重。我的书包从不能放在地上,桌子也一定要擦干净才能放东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所都一样。李易童知道我这个毛病,所以擦完桌子才敢把从超市买的大包小包放上去。
“你们快回吧,感谢感谢,我自己收拾就行了。”我拿过李易童手里的抹布。
“那行,我们先走了。”小白脸早有困意,但又不好意思说。哈欠刚要打,就拿手给捂了回去。
“好,快回吧。”
我把三人送到门口,自己回到了宿舍。可没想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我那个传说中的男室友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手里的杂志,却没有开灯。
我鼓足勇气礼貌地上前打了个招呼:“同学,你好,我叫曹心怡。”我没有跟男孩握手的习惯,微微冲他点了点头。
“我听程宣介绍了。要不是熟人的朋友,我也不会同意你住的。”“四眼儿”男操着一口台湾腔儿,一边说,一边还看着杂志,眼皮抬都不抬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我诧异得很。连灯都不开这是看什么呢?说话还这么生硬无礼,这房子又不是你的,谁住你管得着吗?
要搁平时,我肯定撺了。但出国前家人就千叮咛万嘱咐,到了美国,凡事都要忍着点儿,对待男孩儿也要友善。万一赶上一个精神不正常或者心眼小的,把你砍了,那就不值当了。
话说就在我出国前一个月,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在吃饭的时候被对面的男孩用手上的餐刀把脖子给割了,原因就是那个女孩不同意做那男孩的女朋友。
我爸妈看了报道之后十分担心,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没顾及过男孩的自尊。话从来都是横着出,用词从来也都既血腥又刺耳,杀气腾腾。心眼大点的就让着我,当我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心眼小的就再也不来往了。但我知道,这种恶言恶语的风格,是因为我从小就缺乏安全感而造成的,尤其是在感情上。当然这些理由,便不足以对外人道了。
我想着爸妈的嘱咐,深呼吸了好几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睡了,你慢慢看。”说完,我便转身往里屋走。
还没走到一半,四眼儿男又说:“噢,对了,那个铁锅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你不能用。旁边那个黑色的锅是原来那人留下来的,你用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