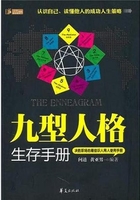文/杨建华
到邮局取稿费,见人很多,便默默地等在旁边。无聊之际,突然见一位女孩进来。女孩来到柜台前问工作人员:“打长途多少钱?”同时握着钱的手越过前面的人伸向柜台。也许是嫌她不太礼貌,工作人员既没有抬头也没有吭声。大家各顾各的,除了我,并没有人注意她。女孩脸红了,她悄悄扫了大家一眼,尴尬地收回了伸出去的10元钱。又过了一会儿,看到工作人员停下来,才怯怯地,但口齿清晰地说:“我想打个长途。”交了50元押金后,她便来到一台电话机前。
我本无窃听他人隐私之意,只是邮局内的空间太小,女孩那毫无顾忌的一声“妈——”不仅使我,连屋内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都为之一惊。此时的女孩少了刚才的忸怩与羞怯,一声方言把“妈”喊得热烈而又奔放,她那急切的、激动的、颤抖的、哽咽的声音拨动了我尘封已久的情感之弦。在电话那一头的母亲大概早已惊喜得难以自持了,因为接下来女孩只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不要哭,妈。我挺好,不要惦着我。妈,不要哭。”她虽然在劝母亲,但她已经被离别之舟载离了海岸,任由奔腾的情感巨浪淹没、托起——时间、地点、人群统统失去了概念,天地之间只有她与母亲。
在场的人被姑娘感染着,都静静地,以便给姑娘,更是给亲情一个最佳通话环境,大家又都悄悄地、遮遮掩掩地,而又贪婪地分享和传递着人间挚爱。姑娘终于放下了电话,显然她还没有从刚才的喜悦里挣脱出来,更没有注意到大家对她的注目与赞赏。她结完账,默默地离开,脸上带着满足与如卸重负的轻松。回想起来,她并没有说出实质性的事情,打电话就是报个平安而已,母亲也无非是通报全家安好之类,但是,一个“妈”、一个“好”字却蕴含了千言万语。深深的情、浓浓的爱、沉沉的牵挂与悠悠的思念在电话线的两头肆意地弥漫、缭绕……
我想,女孩是在外打工?亦或是求学?她羡慕城市,努力适应城市,甚至想用美丽的青春装扮城市。但是她那单纯的心却根深蒂固地为家乡保留着一块净土,一旦被亲情、乡情撩拨,任何装饰都显得苍白无力——不是吗?我在外求学、工作、结婚、生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虽适应了这个城市,融入了这个城市,然而,一旦遇到挫折和艰难,我都会退缩到生我养我的家乡,用亲情、用乡情来舔拭伤口。母亲已经88岁,她给予我的除了母爱还能有什么呢?然而正是这伟大的母爱才使我战胜了无数风风雨雨。每每想起她,不年轻的心也会像年轻人一样激动不已。我不会像那女孩一样对着话筒号啕大哭,只是,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捂着被子悄悄地让眼泪流个酣畅淋漓。
我想得过于专注,猛一抬头,邮局内空荡荡就剩我一人。慌慌地取出稿费,犹豫半天,现在虽不是年节,也不是岁尾,但我还是把兜里的钱统统汇给了母亲。留言栏里只有一句话:“妈,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