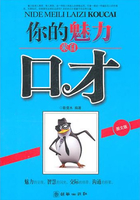第一站 就这样漂到了上海
2008年7月,我被臭汗淋漓的人浪挤出了上海火车站出站口,正式开始海漂。这是我毕业后为自己做出的最大的决定。但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义无反顾。
卡奴禾田
1.2008年7月,我被臭汗淋漓的人浪挤出了上海火车站出站口,正式开始海漂。这一决定做得并不突然,我在宿舍里纠结了小半个月,然后发短信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我想去上海闯一闯。”消息发出去立即炸了锅,亲戚好友纷纷打电话给我,绝大多数都持反对态度。对他们来讲,上海那种竞争激烈的城市,对于民办大学毕业又举目无亲的我来说,找工作基本属于天方夜谭。父母的思想工作持续了几天,我始终态度坚决,最终,父母选择了妥协。这是我毕业后为自己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决定。然而一直到坐上了火车,对上海这座城市,我脑子里除了东方明珠、城隍庙这几个熟知的旅游景点的名字,其他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那时候的我,对旅程的好奇和对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向往盖过心头上所有不安。几天之后,在一个人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后,我站在了上海火车站的广场上。到的时候正赶上正午,广场被烈日肆无忌惮地炙烤着,水泥地闪着一片一片白亮的光。我原以为自己会很兴奋,但那时才真正明白,连坐两天火车的人,是根本没有力气去想这些的。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地方安顿自己,然后填饱肚子。作为曾在西安上学的学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大学城:房租便宜,街头巷尾散落着各种特色小吃,价格实惠,万一有意外情况混得穷困潦倒,还能去高校里蹭食堂。至于找工作的事,安顿下来之后再做打算。跟地铁安检员简单地聊了聊,得知上海最大的大学城在松江,规模宏大全国知名,于是我就兴冲冲地出发了。一路上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小心翼翼地盯着地铁上的线路指示灯,车厢里的乘客很多,跟火车上一样嘈杂闷热,冷气倒是开着,但是在层层“人墙”前面,仅仅是心理上的安慰。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站在松江大学城的街间。但瞬间明白,我被自己的自作聪明坑惨了。7月中旬的松江,下午,太阳当空,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湿气,我拖着行李走了半小时也没看见一辆车经过。大街上空空如也,我拉着旅行箱从一座座大门紧锁的大学前走过,如同行走在一座科幻小说中才能出现的无人之城。松江大学城这类真正完善的教育产业集团,根本不是我脑海里西安的那个充斥着乡土气息的样子。一天一夜的火车加两个小时的地铁,我还背着大书包提着行李箱,背后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太阳,脚下是晒得铁板烧一样的柏油路,到上海刚刚几个小时,我就已经绝望了。我试着问了问学校周边的旅馆,一晚上竞然要200块钱。还好,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看见了马路对面冲我微笑的山德士上校。吹着冷气狠吸可乐,我开始拿着手机查地图,身上的钱不多,要先找一个便宜的地方落脚。
2.又是地铁上一个多小时回程的颠簸,等到夕阳西下之时,我终于在杨浦大桥脚下找到了这家“金桥求职公寓”,推开玻璃大门的时候,两只脚像踩在棉花上,小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求职公寓只接纳来上海旅游和刚毕业的大学生。说直白点,这里就是一间普通的六人宿舍,环境略差但价格便宜,能够让你迅速安顿下来。关于住宿,我能够选择的范围并不大,住在酒店里面找工作显然不现实。在上海租房子的规矩是付三押一,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支付四个月的房租,这显然成了一个问题。更何况,就算钱的问题解决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租也需要时间。于是,人才驿站几乎是我这一类的求职学生最好的选择。墙上的价格表做得非常醒目:空调房28元,普通房22元,一次**一个月的钱可以适当优惠。这价格比起路边动辄200块钱的旅馆,性价比爆棚。本来是打算住空调房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公寓里的空调房并没有市场,当时来找工作的同学,几乎都住在普通房里。最终我也决定随大流,外地来上海找工作的人聚在一起,平时可以互相聊天解闷儿,找工作也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毕竟还是学生,人际关系建立起来会很容易。这是一栋废旧的老楼,紧邻黄浦江,一楼主要是娱乐休闲的功能,有一个可以视频点播的挂墙电视屋,一个放着各种旧书的小型图书室,一间卖日杂用品的小卖部。在大厅的走廊里,贴着一张上海市的交通地图,一堵贴满了曾经住客留下的祝福墙,一些招聘资讯,我大致地扫了几眼,里面的职位大都惨不忍睹。二楼和三楼分别是男女客房,布置大体相同,一人一个柜子,桌子共用,有网线,电脑自备。四楼是一个干净的无烟小型网吧,以及员工宿舍,有一个活动大厅,用来在节假日里办晚会。公寓对面有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这里的饭菜价格低廉又实惠,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当然,有时候天气糟糕人又犯懒,可以直接去前台让服务员拿加了卤蛋和火腿肠的康师傅。就这样,我终于安顿了下来。相比很多学生公寓高昂的价格,金桥公寓的价格算是便宜的。很多学生公寓环境很差,是小区里的居民楼,金桥比较正规,而且各类设施齐备。金桥最大的劣势,就是所处的地理位置太偏:下了地铁还要坐十分钟的公交车。虽然偏了一些,但我还是建议你能找一个类似这样的学生公寓房。作为刚刚进入社会没什么钱的人来说,那里真的是最棒的选择。
3.禾田是我在公寓里遇见的第一个朋友。我拉着行李进宿舍的时候,禾田正趴在床上睡觉,那个点,太阳已经快要落山,宿舍的木板床上还留存着太阳暴晒过的余温。他赤裸上身,穿着一个花色的大裤衩,躺在床上睡觉。见宿舍里来了新人,他睡眼朦.地坐起来,一边给我打招呼一边摸眼镜。男生宿舍的卫生状况向来堪忧,宿舍里布满了烟头,一地昨晚吃剩下的瓜子皮,桌子上放着半瓶喝剩的矿泉水,吃剩了一半的泡面让屋子里怪味弥漫,搞得刚刚跟我吹嘘环境优雅的前台姑娘瞬间丢了面子,她有些生气。“侬房间收拾一下好不啦,我们要不要做生意啦?”禾田没有理她,她拿起扫把,把屋子快速地打扫干净,一脸鄙视地出去了。我在禾田的下铺坐下,把书包打开,开始整理私人用品。禾田穿好衣服,从床上跳下来,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烟。”我朝他摆摆手,侧脸看着他。细框眼镜下面,小眯缝眼高鼻梁香肠嘴配一撮故意留的小胡子,奇形怪状地混搭在一起,倒还顺眼,样子有点像毛利小五郎。他见我不抽烟,就把烟叼在自己嘴里,拿打火机点着,深吸了一口,一缕青烟从他嘴里出来。“你从哪儿来的?”他带着一丝颓废问我。“西安。”“这么巧,我也是西安毕业的。”我拿着洗漱用品,走到储物柜前扫了一眼,上面红油漆的字母写得不清不楚。“哪个是我柜子啊?”“你看哪个空,就放哪个吧,这没什么人的。”我把洗漱用品扔进柜子里,把被汗浸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了一件干净的T恤。又走到床前,从包里掏出手机,这才想起还没有办手机卡。“这附近哪有营业厅?”我低着头问他。“出门对面有个市场,里面有很多,联通移动都有。你还是办移动吧,联通卡在上海信号不好。”“哦。”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整了一下衣服,“我要去吃个饭,一起去吗?”“走。”两个人迅速熟识。禾田的家在安徽大别山一个不知名的小村里,那里盛产一种茶叶。禾田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茶农,父母也勤勤恳恳地种了一辈子茶叶。赶上那两年长三角流行喝茶,家里的茶卖价很高,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他成绩不好,在西安的一个职业学校混了一个大专文凭,毕业后,作为独生子的他决定出来闯荡——回家继承家业当然轻松,但种茶叶也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安定舒适只是一个借口,碌碌无为才是真的。“谁愿意回去种茶做农民啊?”他吃着菜,跟我说着。到上海的第一天,禾田一个人跑去南京路逛,傍晚时分,他站在人潮汹涌的外滩眺望黄浦江的对岸,这座灯火通明的城市让他对未来信心满满: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赚钱不是一个问题。结果一晃就是一年。他做过很多行业,有奶茶店店员、汽配城会计,寒假的时候还在徐家汇的太平洋里推销过戴尔电脑,最长的几十天,最短的几天。他似乎经验丰富,什么都能干,又似乎眼高手低,什么都干不长,于是就在这座城市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天没一天地过日子。跟没有正经工作比起来,遇见我的时候,他还面临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一年来他办了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并疯狂透支,欠的钱补不上,于是就再办一张另一个银行的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这个窟窿就像袜子上破的洞,越来越大。很快,除去基本的开销,他每个月的钱只够来还利息。他倒是不着急,每天都拿着这个跟我们炫耀。“那你把这些钱花在哪儿了?”我好奇地问。“住宿、交通、吃饭、抽烟、上网,哪样不要钱?”他向我抱怨着,“你这是刚来,呆两天你就知道了。”与我每天焦躁的奔波求职的状态相比,禾田已经把找工作当作儿戏。那几天他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连锁理发店里做收银员。可能全天下最无聊的事情就是做收银员,整天数钱,数了半天钱还不是自己的。第一天上班回来,他兴冲冲地塞给了我一张理发店的储值卡。“我们公司在上海到处都有连锁店,洗剪吹一次30块,这里的钱够你剪半年的头,用完了再来找我。”结果他干了还不到半个月,又辞了职。那天他气冲冲地回来,一脸怒气。“收银台里有一张100元的假币,查不出来是谁的问题,店长说由我赔。我跟他说,你让我赔可以,你拿出证据来,店里三个收银员,你凭什么说这钱是我收的?”争吵愈发激烈,老板让禾田先回家,说工资会打他卡里。他就回来了,走之前他跟老板甩出来一句狠话:“你要是敢扣我的钱,我就投诉你们。工资一分都不许给老子少。”第二天下午他去了银行两次,钱迟迟没有到。第三次去的时候,卡上确实有钱了。老板没有把钱全部给他。他把钱从工行的ATM机取出来,又走到马路对面的建行,把信用卡还了。那时候他还的都仅仅是利息,说白了跟没还一样。他从银行出来准备回公寓的时候,马路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三百米的距离而已,他穿过马路,赶紧跑回公寓。结果刚出来几步,蒙蒙细雨就变成了倾盆大雨,他被浇成了落汤鸡,回宿舍,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换上拖鞋。“我最近真是倒霉透了。”他坐在床头剪脚趾甲,面无表情。后面的几天,他还是窝在公寓里,找到工作了就打两天工,赚了钱就抽烟和上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连住宿费都欠着。他住这里一年多,老板也不太管他。他倒是不耍赖,一有钱立刻就还上住宿费。禾田欠银行的钱并不会无限期拖延。那天下午,禾田的母亲从邮递员手里接到了银行发来的催款单,三万元对这个茶农家庭确实不算一个小数目,她打了个电话给禾田,禾田承认了这一年来所欠下的账款。第二天下午,母亲给他打来了三万块钱。这件事在晚上的卧谈会上被禾田轻描淡写地说出来。我很奇怪,这个在我眼里穿着简朴,生活简单的男孩怎么会欠这么多钱?一直到我后来离开公寓,他都待在上海,他换了几个工作,但依旧在这座城市里漂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却又不愿意回家乡。2011年的时候,金桥公寓因经营不善倒闭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遇见了禾田,工作后到现在,我都没有申请信用卡的习惯。我不习惯透支消费,哪怕透支的额度在我绝对还得起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