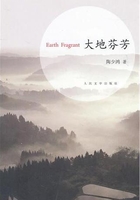第三章 佛说人生苦,儒说人生乐 (2)
如何才能摆脱痛苦?梁漱溟先生说:“在前,我以为看世间人生只有两面,一是向外面去找,走欲求的路,许多圣哲都是顺着这个方向去找一个东西来解救大家;一是取消欲求,根本上是取消问题,这是佛家的路子……(佛家)是去取消欲求,根本是在解脱生命……生命是欲求,他就根本不要生命”。这一观点和王国维先生何其相似!王国维先生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红楼梦中真正得以真正解脱者唯有宝玉一人。梁漱溟先生自己不也是差点遁入空门吗?
在佛家看来,人生无论是苦还是乐都在一个欲念间,有苦必有乐,因此苦和乐都归于“执”。因此,佛家的解脱之道是要从“执”中解脱出来,达到超情绝欲,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无我之境界。弘一法师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生死都是空,他真正从“执”中得以超脱出来,因此在圆寂之际静如秋叶。
与佛家不同,梁漱溟说:“孔子不是如前面所说从取消问题去救人,是从不成问题去”,而是“听他感触应付下去,不加一点意思。”对于儒家来说,生死是一个应该严肃对待的事情,儒家的着眼点就在于“生”,也就是俱生执。生命原来是一个活动,是在生机畅达上,真是无所谓苦乐。生机滞塞,才有所谓苦。只要顺从生命本身之理而行,便可以达到解脱苦的目的了。
泰州学派创始者王心斋说,“乐者心之本体也。”还留下了四句话: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了,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
意思是说,乐本就在人的心中,无需从外面去找寻。仁者虽有事亦行所无事,都是所谓随遇而应,过而不留,安和自在,泰然无事,他感触变化只随此生命之理,所以他时时是调和,是畅达快乐。
孙叔敖原来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
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
孙叔敖回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
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
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孤丘老人很满意,笑着离去。
孙叔敖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被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感到荣耀;你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色。我开始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心态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顺其自然,悠然自得,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
孙叔敖在险恶的仕途风浪中始终不惊不惧,只因他心中淡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只是顺着生活的路上走去,着重生活的本身,不着眼环境的关系,就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经过都是生命,而生命应该是从心出发的,孙叔敖守住了心,顺心而行,生命自然也就随之畅达。
梁先生还以君子和小人来指代这两种生活态度。孔子有言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本是安和自在,种种不成问题,当然时时是乐,故君子与乐完全不离。小人因有许多私欲,故不能安乐……小人去找,所以把宇宙海阔天空大的态度失掉;而仁者不找,所以他的心是通天通地,宇宙是属于他的。”君子只看当下自己心的自然流行,而小人杂念甚多,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拉到了当下,故焦虑不堪。因此一者乐,一者不乐。
无论儒家还是佛家,对人生困苦的问题都得圆满地解决,只不过一个顺生,力求生命的生机畅达;一个是无生,根本在于取消生活。一水中分,殊途同归,并立于中国哲学之高山,良无愧也。
弦外听儒音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师承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李贽是其重要代表人物。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
人生有苦有乐,但是在最为本真的生命意义上来说,只有畅达与否。梁漱溟先生说:“生命本是一个活动,原是生机畅达,这是绝对的乐,原无可说,即是平淡,即是说生命原是一个调和的平坦的,并没一点高低之可言。”生活就像一条河,缓缓向前流淌,纵然遇到巨石横拦,依然可以顺利地绕过去,水流没有滞塞,这都是乐。因此“在条达安和之气象看,真是无时非乐。”梁先生还举例说,小孩之喜怒哀乐,听他喜怒哀乐。听就是“任由”的意思,为何如此说呢?“他喜怒哀乐的时候,也恰是他条达通畅的实际,苦的踪迹安在?而成人当喜不喜,当哭不哭,忍含在心里,乃有苦之可言。”
这种乐是当下的,具体的,因为生活本就当下。这种当下和具体并不是以某一件为乐,某一件为苦,如果是这样的话,实现就会抱定这种态度从这些事情中寻找乐,一旦寻找了,其实就是落入了“虚见”。梁先生说,与此虚见同起者,厥为妄情,正是这些东西扰乱了人原本正常的生活。
梁漱溟先生说,所谓实感者,即当前一刹那苦乐之感,此乃直觉之所指示,离此而去希冀什么便是虚见,因已离开直觉矣。就如同吃一块糖,觉得好吃,心里就有一种乐在。但是有的人会以此推去,以为有千块糖便有千倍乐。而作为实感的乐是绝对的,并无高低之别。“若愈看愈高或愈低则愈错,实则一平淡而已。”既无高低之别,生活就当只存“平淡”可说。人们常说平平常常就是真,这种生活的真就是乐。这种和生命同在的俱生我执正是儒家认为的根本。
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作说: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平淡之中其实有万般滋味,生活也是如此,而且这些滋味其实都可归于一个“乐”字。
梁先生认为实感便是对,如果在此直觉之外再加一点,就成了非是。也就是说如果抱定了糖越多,乐越多的态度,便是落入了虚见和妄情。这是儒家和佛家都要求破的执。
县城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铺里住着一位老铁匠。时代不同了,如今已经没人再需要他打制的铁器,所以,现在他的铺子改卖拴小狗的链子。
他的经营方式非常古老和传统。人坐在门内,货物摆在门外,不吆喝,不还价,晚上也不收摊。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儿经过,都会看到他在竹椅上躺着,微闭着眼,手里是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有一把紫砂壶。
当然,他的生意也没有好坏之说。每天的收入正够他喝茶和吃饭。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因此他非常满足。
一天,一个文物商人从老街上经过,偶然间看到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因为那把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风格。他走过去,顺手端起那把壶。壶嘴内有一记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惊喜不已,因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三件: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一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在泰国某位华侨手里,是那位华侨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上,以56万美元的拍卖价买下的。
商人端着那把壶,想以10万元的价格买下它,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老铁匠先是一惊,然后很干脆地拒绝了,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的,他们祖孙三代打铁时都喝这把壶里的水。
虽然壶没卖,但商人走后,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这把壶他用了近六十年,并且一直以为是把普普通通的壶,现在竟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钱买下它,他转不过神来。
过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他总要坐起来再看一眼,这种生活让他非常不舒服。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来方者络绎不绝,有的人打听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有的甚至开始向他借钱。他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他不知该怎样处置这把壶。当那位商人带着20万现金,再一次登门的时候,老铁匠没有说什么。他招来了左右邻居,拿起一把斧头,当众把紫砂壶砸了个粉碎。
老铁匠的生活原本是平淡而和适的,因为他没有把乐寄托在心外的某一件事物上。按世俗的方法,多一块钱就多一份乐,多10万块钱乐岂不是更要多许多?老人就不得已地陷入了这种虚见之中,生活也不再那么舒服了。梁先生说:虚见本不难破,难破乃在他辗转相资,习而不察,离去事实太远,即离当下太远,使我们不知不觉的入于意必固我而不自觉。老人的失眠就在于想着那把壶可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财富所象征着的幸福,却不知道这些在当下看来都是虚无,落入了“执”之中。但他最终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快乐生活与壶并没有关系,所以他做出了选择。他无法对壶做到视而不见,只能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彻底把自己的虚妄打得粉碎,也算得上是生活的智者。
生活既本是乐,就无需在从外面去找,更不需要从生命之中解脱出来。儒家在生活中看到乐,并提炼乐;而无苦也就无所谓乐,因此佛家把乐也当做了“执”,采取了对苦一样的取消的态度。两家都试图让生活回归到平淡安适,只是方式不同。
弦外听儒音
破釜沉舟:《孙子兵法》上写道“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但该成语为后人所熟知还是源自项羽。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最后大破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