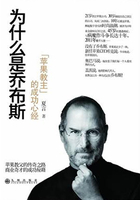因为先生对青年有那样的吸引力,所以无论是十六年在上海时,到劳动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立达学园等处,或十八年及二十一年两次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等等。一听到先生来讲演,青年人像发狂似的,都拥挤到会场,后来的,就只能站在窗子外或大门口来听了。而在北平师范大学,竟因大礼堂容不下众多的听众,致将窗子都打破。请讲者,不得不请鲁迅先生到露天操场上去作狮子吼,因那次听众实在太多了。鲁迅先生晓得站在后面的青年,绝对听不见,他自己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这是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时,以幽默口气讲出的。
固然,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感召力。他的几十册的著作与翻译,是一个动力。但先生讲话能更吸引青年,却是更重要的动力。
鲁迅与世界语
在帝国主义寻找殖民地的当口,语言文字,也是他们利用的武器之一。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德文在中国之盛行,不必讲了。现在日本在我沦陷区,拼命推广日文与日语,总是众人周知的事实。
因为帝国主义找殖民地的目的,不只是要推销货物,吸取资源,还要奴役人类,使其成为他的臣属,于是在除了《圣经》与“大炮”之外,文字语言,也要网布开来。这样,在“大炮”与《圣经》所及不到的地方,文字语言就发生很大作用了。一世纪,两世纪,推广下去。被奴役的人们,眼界既属有限,思想就定型化了。除了甘心为主子做奴隶外,很少会想到别的。这是被压迫的民族,应该提倡柴门霍甫(今多译为柴门霍夫——编者注)所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唯的理由。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路先锋,是刘师甫。支持此运动最有力者,是蔡孑民,蔡先生掌北大时,曾特地拨出经费,聘孙国璋为讲师,在北大设立世界语讲习班,为青年学者开了不少便利。而盲诗人爱罗先河来中国讲学,亦是由蔡先生发动聘请的。
爱罗先珂是世界语学者,但他又是诗人音乐家,到北平后,就住在鲁迅先生的家庭里——当时鲁迅尚与周作人同住在八道湾的房子里——爱罗先河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演,翻译者,不是鲁迅,便是周作人。(爱罗先珂讲演,多用日语)但因周作人讲话,不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很有些地方,竟指名要求请鲁迅先生作翻译。
因了先生与爱罗先珂接触的机会特别多。而爱罗先珂当时,又喜欢用世界语写小说。本来赞成提倡世界语的鲁迅先生这时节便开始了学习。(孙国璋在北大讲习班教世界语时,先生曾经前往听过一次课,据先生说,孙国璋不仅不懂得教授法,更不懂得世界语,讲习班要他教下去,中国是没有人会弄好世界语的。)可惜当时,中国世界语工具太不完全,不特没有书籍与读本,连讲义字典都没有。而爱罗先珂又因环境不宜,不能不离开中国去,所以鲁迅先生的世界语,终于不会学好。
民国十二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学校教务处的陈空三与冯省三,去面请先生来教课讲文学史或文艺理论,先生说: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次一天,先生的通知,即送到学校去了,记得当时是,每星期五,先生去教两点钟。而且一如在北大的教法,两个钟头连续不下堂,一直教下去。
世专校学生,当时将近两百人’而选修先生课的,起先只有四十多个人,因在先生教课的同时间,有一门数学,学习科学的人,这一门课,又不能不去上。所以先生开始在世专校教课时,是在丙组一个小教室里,一星期,两星期,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学校不得不请先生到兼作礼堂用的甲组大教室去,第一学期未选先生课的人,到第二学期,都改选先生的课程了。
可是,世专校当时的经费,非常之困难,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但先生却不收这一批钱。他对当时送钱去的陈空三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
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一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
先生因为赞成世界语,所以他自己不特义务地教了几年书,他经常还鼓动学生,努力从事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为世界语本身奠基础。记得当时受了先生鼓励,而动手译出短篇作品,发表于北平《京报副刊》、《黄报副刊》等地方,就有李端甫、王秋士、李文辉、吕蕴儒等人,而陈声树等人,更号召了用世界语翻译中国哲学及文学向世界传播的大计划。惜世专校因经费困难及风潮关系,这个大计划没有实现出来。以致鲁迅先生的鼓动,算白费力气了。
严谨与认真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一个清朗的星期天,吴曙天女士,随着她的爱人章衣萍,来访鲁迅先生了,据说,她刚由杭州的母家来。在她盘旋的短时间内,她的将近六十岁的父亲,再三称道鲁迅了不起。其原因,是他的父亲看过了《呐喊》,所以才有那样称赞。当时,我很怀疑吴曙天的话,想着六十岁的老头了,会赞成新体小说《呐喊》,不是吴曙天想在鲁迅面前卖关子,便是她的父亲,也许是老留学生,所以才能对于新型《呐喊》有理解,可是后来听章衣萍说,吴曙天父亲,不是留学生,而且是在清朝得过功名的遗老。但赞成《呐喊》,又是的确的。因为吴老先生,还由家写信,给他在北平的女儿,要鲁迅其他著作看。这事情真有点奇怪了。
到民国十四年暑假,我到河北大名府的金滩镇,在那里,看到一家粮食店,长期订阅着北平的《京报》。有一天’那粮食店老板,同我谈起北平各种情况时,忽然问我,鲁先生现在作什么?我问他何以注意到鲁迅先生?他说《京报》各种附刊及副刊上,鲁先生的文章,他是篇篇都看的。觉得鲁迅先生讲话,最懂人情,最有道理,可是,以我所记得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及各种附刊(当时《京报》除每日有由孙伏园主编之副刊外,还有七种周刊,每周各出一次。如《莾原》、《文学》、《民众文艺》、《妇女》、《科学》、《图画》、《戏剧》等。)所写的东西,除一小部分散文诗外,大半是杂感式的短评。不料这些短评,竟为一个粮食店老板看中了。那位老板以他的白须与白胡看来,其年岁总在七十左右了。
还有一件,是张十方先生告诉我的。据说,他有一个世伯莫某,民元前是作革命工作的。以后不愿做官,便在香港作寓公,并兼营生意,其生活,是相当阔绰的。但奇怪的,是他顶佩服鲁迅。因为鲁迅的各种创作,他都收集起来看,年岁自然是五六十以上的了。因为在三十年以前,他就作着革命工作了。
由以上三件例子,使我想到对于鲁迅先生的敬仰,并不只是一些研究文艺的青年,也不只一般中、大学的学生。鲁迅先生以他的极敏感的思想,最深刻的观察才有那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磨练得恰到好处的笔法,向虚伪进攻,向卑污打击。而更对后一代人,指示出路与方法。所以稍微用点思考的,或对社会有若干认识的,便对鲁迅先生的文章,起了共鸣了。其实,不只是共鸣,有些人还认为鲁迅先生的思想与方法,是中华民国复兴唯一的路线呢。曾忆巳故山东蔡寿潜先生,在民国二十年前后,就将鲁迅的警句,一条一则的抄录起来,贴满了他的房壁,以及座右铭呢。
但这些,都是先生在苦难中,用尽了一切精力,才会有那样出人头地的功绩,绝不是一般空头文学家所想的那样简单,一首打油诗,两段杂感,半篇小说,几句批评,马上就可以霸坐文坛,吓倒一切。试举鲁迅先生之认真’就可看出一般了。
民国十三年冬,郑振铎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某期上,误将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芦那卡尔斯基像,排成另外一个文学家名字了。当时,我将所买的一本《小说月报》,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再査封一下看,究竟是不是错,鲁迅先生一看,说:
“他们真胡闹,连照像也可以随便安排。”
先生马上跑到书房里(先生住北屋,书放南屋)不特捡出芦那卡尔斯基像。连错的那个人(名字我现在记不起了)的像,也查出来了。我当时说了一句:那么,代他更正吧,先生紧接着说:
“由你发现,就由你更正吧,证据我这里有的是。”
结果,我就在伏园主编的《京报》上,指出那个错误来。
因为先生曾说,《小说月报》自命为文学领导者,也时常板起面孔,教训青年,不应该有那样错误,教青年人跟着他去错。所以虽是一个相片的小错,
先生也是主张纠正的。
再有就是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因为先生看到,中国新装订的书,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那地方,占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桌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但看毛边书,却非常之麻烦,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边。不切边放不整齐,因此,一般买书的人,多不高兴要毛边,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毛边书,就再三告诉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印成,李小峰将二十一本送给先生,预备供给先生赠人时,书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当时火起来了,问李小峰,究竟怎么一回事?李小峰是这样答复的:
“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性都切了边。”
鲁迅先生马上说: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截边的光本带回去,再为先生送毛边的去,此后为先生送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后,毛边本成了时髦品,那只能又作别论了。
另外,还可举出相类的例子。
鲁迅先生很赞赏已故画家陶元庆的书,所以,在元庆开展览会时,先生不特代他作序言,在陶元庆住在北平的当时,先生所出的几本集子,如《呐喊》、《彷徨》、《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都是陶元庆代作封面的。陶元庆亡故后,先生在上海遇见孙福熙,要福熙为《野草》作了封面,用虽然用了,但先生不喜欢那样多的灰色。此后,大部分集子的封面,全出自先生手笔,有时,勾些古物,有时写几个简单字,也有用颜色配合一下,然后再题上字的。总之,先生没有再接触到可佩的画家,所以不找人做封面了。
由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认真、坚持、谨严,换了话说,就是先生有毅力,有韧性,丝毫不含糊也。
虽然,所举的都是些小事,先生却在这些小事上,建立起伟大的基础。
鲁迅论爱罗先珂
鲁迅先生翻译的《桃色的云》的作者——爱罗先河,到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记得吧?
爱罗先珂是诗人,是音乐家,同时又是世界语传播者。但他却是一个瞎子,而且在四岁时就瞎了。
他是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又因为是盲人,所以他的幻想中的“乌托邦”,特别来得明显。
他奔波于欧亚两大洲,但到处都听见残酷的叫喊,到处都遇到冷的空气。所以他的诗篇,总带着感伤的调子,而盲,又阻制了他的行动,所以他终于抱着悲哀的心情,默默地过去了。——虽然他想藉世界语的传播,以便助成他的“乌托邦”的实现。
他曾来过中国,而且有两次。同时,他不像萧伯纳似的,香港、上海,终于坐着飞机,在北方的天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 空里览了一个圈子走掉了。那是观察家,也不像泰戈尔似的,要中国人再发扬精神文明。是捧场家,他在北平居留了相当期间。他作诗,他讲演,他教授世界语,他更出席音乐演奏会,不只是歌唱,还拿出弦琴,弹那优静而略带感伤的调子,他是要激发起中国人的觉醒,虽然假如觉醒之后,应该怎样?爱罗先珂在他的诗篇或歌唱里,并未有明确的概念。但这一点,在现实意义上讲:已经足够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在双重的羁绊下,觉醒还是急切地需要啊!
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爱罗先河已离北平而去了,虽然世专的创立,与爱罗先河很有关系,但他却不及见那新兴的学校成立。因此,对于爱罗先珂,竟没有见面的机缘,所知道的,不过是从学校当局者口里,晓得他是世界语传播者,而且是很热心的一个。
以后,晓得爱罗先珂两次到中国,都是住在鲁迅先生家里,这才有机会听到——爱罗先珂的事故。
鲁迅先生说:
爱罗先珂因为是诗人,所以他特别敏感,记得他第二次到中国来时,北京大学请他来教书。据爱罗先珂讲:中国人与日本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处,是日本人对于事理的呆板与冷酷,而中国人却洋溢着很厚的人情味。其证据是:当他——爱罗先珂——在曰本登岸时,遭受了日本官厅的拒绝。因此,日本警察对爱罗先珂不特搜索了他的身体与行囊,还给了他难堪的侮辱。他在中国虽也遭警察的检查,但警察却对他一点没有横暴的行为。而警察自己,还在一旁咕噜着:他是瞎子呀,我们也太那个了。因此,爱罗先珂断定:中国人只要觉醒起来,很容易得到助力,因为中国人能以同情给人。至日本,那只有到处碰钉子了。因为日本人眼中,已没有别的人类存在了。这是爱罗先珂思想上的敏感。爱罗先珂又因为是盲人,他的身体上的感觉,也特别发达得厉害。天要雨了,天要晴了,他是常常预先知道,要是有人找过他一次,第二次如再去找他,而无论换个什么地方,或换个什么时候,他一听脚步声,就晓得是某人来了,不必等那人讲话或报名出来,甚至有时他听生人的脚步声音,也能断定来者是怎样性格的人。
鲁迅先生对爱罗先珂的描摹,很能使人理想一会那个预言者。可是,鲁迅先生又说到他:爱罗先河非常之害怕女人。有一次,女师大请他去讲演,在讲演完毕之后,学校还预备了些点心。有教职员,有学生,都围来问爱罗先珂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人,则一味劝他吃茶点。爱罗先珂当时坐得笔直,脸面非常之严肃,点心固不吃,连茶亦不肯喝,后来离开学校,回到家里,我问他:“今天那里预备的点心,都是你平素非常之喜欢吃的,为什么今天一样都不动手呢?”他竟说:“那里不是有女人么?”你看,他在女人面前,连吃都不敢了。
“在他自己太太面前也这样?”我很奇怪地问。
“他还是独身啊!”鲁迅先生说过,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过了一会,又继续说:“听说他在日本时候,爱过一个寡妇,一天到晚,向那女人送诗篇,但见了那女人,却什么话也不敢说。结果当然失败了。从此,他就更怕女人,恐怕他还是童男子也说不定。”
这使我恍然于他的感伤的调子的由来。鲁迅先生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