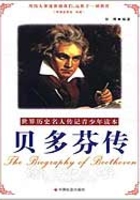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第二个上阵。他将苏轼在杭州出版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诗集献给神宗皇帝,认为苏轼的诗文处处都在讽刺新法、侮辱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这些诗文在朝廷内外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皇上对朝廷实在是大大的不敬。皇上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苏轼在诗中讽刺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皇上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他讽刺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皇上兴修水利,造福农桑,他讽刺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皇上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讽刺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总而言之,只要皇上、朝廷有新举措,他就应口而言,极尽讥讽之能事。这些言论或者刻在书版上,或者刻在石碑上,广为传播,自以为能。而苏轼最近所上《湖州谢上表》,更是对变法横加指责,其言论在街头闾巷广为流传,志义之士无不愤怒。舒亶请求神宗皇帝立即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但是三十二岁的宋神宗并没有明确表态,也许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还在观望犹豫。
就在舒直上言的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终于亲自出马,他上奏皇帝,明确指出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
第一,苏轼此人本来不学无术,只不过偶然考中科举,浪得虚名,在朝廷滥竽充数罢了。他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连续四大罪状,连续四个该杀,这个导火索一点着,火苗就“呼呼”地直接烧到皇帝头上,苏轼不死也难啊!现在,神宗手里攥着好几张措辞激烈的起诉书,他必须也可以作出决定了,他下达圣旨,将苏轼的案子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被称为“乌台”,所以苏轼的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人立即布置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馔前去缉捕苏轼。皇甫馔带着儿子与两名军士,一行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往湖州。情况万分危急,可苏轼还蒙在鼓里!
千里缉捕锒铛入狱
最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是驸马王诜,他的夫人是神宗的姐姐。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他火速通知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苏辙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惊呆了,立刻派人飞马奔赴湖州,希望赶在皇甫僎之前通知苏轼,好让兄长有个思想准备。苏辙派出的飞马哪里赶得上皇甫馔这个官差的骏马?多亏皇甫馔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儿子忽然生病,结果耽误了半天,苏辙的信差终于抢先一步赶到,给苏轼报告了这个爆炸性消息(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馔一行抵达湖州。此时苏轼正在休假,由他的副手、湖州通判祖无颇代知州事。皇甫馔身穿官袍官靴,手持笏板,气势汹汹径直闯入州衙。两位御史台军士身着白衣,头扎青巾,怒目圆睁,脸色狰狞,分列在皇甫馔两侧。衙门上下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苏轼哪见过这阵势!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非常害怕,不敢出去,在衙门后与祖无颇商量对策。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苏轼问:“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名,还不是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他穿上官服,手持笏板,出去见皇甫馔,祖无颇等官员也都身穿官服排在他身后。但见那两位御史台军士的腰间鼓鼓囊囊,好像藏有匕首。皇甫馔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气氛更加恐怖。最终还是苏轼先开口,他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使者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皇甫馔这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祖无颇这时上前问:“您一定带来皇上的诏命了吧?”皇甫馔厉声问他:“你是何人?”祖无颇回答:“代理知州。”皇甫馔于是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馔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士兵立刻上前将苏轼五花大绑,片刻之间,苏轼这位湖州知州如鸡犬一般被拉出城外,拖上官船(事载《孔氏谈苑》)。
苏轼的妻儿老小急忙追赶出来,哭天抢地紧随在后。苏轼心里既慌乱又难过,但他依然不失文人本色,在这个当口儿,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当年宋真宗招揽贤才,有人推荐诗人杨朴。宋真宗立即召见,让杨朴作诗。杨朴说不会,真宗问:“你临走的时候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我老婆写了一首绝句,说:‘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家了。
这个故事苏夫人也听说过,这会儿苏轼回头安慰夫人说:“别难过了,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苏夫人不禁含泪失笑(事载苏轼《东坡志林》)。
这边儿苏轼刚押走,那边御史台就派人去搜查苏轼的诗文。当时苏轼的全部家人正乘船奔赴南都投奔苏辙,官府连夜在宿州拦截这艘船,翻箱倒柜搜查一通,吓得一家人魂飞魄散。个性一向温顺的苏夫人不禁怒火中烧,她气愤地说:“都是吟诗作文惹来这场大祸,他究竟得到什么好处,把我们吓个半死!”一怒之下,将手中残存的苏轼手稿烧了个干净(事载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半个月后,御史台开始正式审理苏轼这起皇帝钦定的大案要案。这个案子怎么审?
起诉书上罗列苏轼的一大堆罪状,几乎都与诗文有关,那就先调查诗文的真实含义再说吧?不行!先定罪再说。审讯一开始,审讯官员就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无誓书铁券。誓书铁券乃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苏轼出身低微,哪有什么誓书铁券?这完全是讯问死囚犯的方式(事载宋·朱或《萍洲可谈》)。可见李定等人早就将苏轼内定为死罪,只等证据拿到,再屈打成招,便算大功告成。
证据在哪里?唾手可得!
首先,将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全部收集起来,选出一百多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公文,务必上交个人手中所有苏轼的诗文,不得隐瞒。结果短到一张便条,长到一首完整的诗统统上交御史台,仅杭州一地就上缴了数百首之多。然后拿出一首,让苏轼自己解释一首。最初,苏轼只承认个别诗作有讥讽朝政乃至新法的意思。御史们立刻暴跳如雷,他们一口咬定苏轼不老实,展开车轮战法,除非苏轼对诗歌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愿,否则就没完没了。
实在不想说实话,那就只有辱骂和暴打了(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面对如此的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前途险恶、生死难料,他的精神多次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就曾想投江自尽,想到兄弟亲人才作罢;入狱后他又准备了一些丹药,想着一旦被判死罪就先行自杀(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究竟有没有写“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这些诗果真罪该杀头吗?我们来看一看、评一评:
第一,平心而论,苏轼的确写了不少讥讽、抨击新法的诗歌。这其中,有的是因为新法中确实存在问题,有的则是苏轼对新法的偏见。比如朝廷在全国推行各种新法,苏轼在诗中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意思是说,农民一趟趟往城里跑,就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法令条例,好处没得到多少,跟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儿反倒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要对付许多的新法条例当然会有些麻烦,但归根结底,这些麻烦的新法还是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好处,总不能因噎废食吧?这就是苏轼的不对了。
第二,只是一般性地讥讽朝政,并不一定针对新法,更不至于讥讽皇帝。比如朝廷实行官盐专卖,增加国库收入,苏轼在诗中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意思是说老百姓吃春笋没有味道,原因是三个月都没有吃盐了,其实就是埋怨官盐的价格太昂贵。官盐专卖是北宋开国以来就有的法令,并非新法的新规定,但也总算是讥讽朝政。
第三,含义比较模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但也被归人讽刺新法一类。苏轼有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杭州着名的钱塘江潮到来时,常常有人到江潮中浮游冲浪,甚至有人借此下赌获利。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皇帝曾下令不准百姓冒险弄潮。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说,龙王如果明白皇上的用意,最好将东海化作桑田,弄潮儿就老老实实去种田了。但是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录,苏轼在拷问中自己承认,这两句的意思是:龙王如果知道皇上喜欢大兴水利工程,索性直接将东海改造成万亩桑田算了,而这显然是荒唐不可行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诗有可能在讥讽宋神宗推行农田水利法不可能成功。但这是在拷问之下逼供出来的解释,究竟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就难说了。
第四,就纯粹属于歪曲诬陷了,这一类在证据中占据大多数。
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确有不忠之心。”神宗吃惊地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我还不至于不忠吧。你为什么这么说?”王珪将苏轼写的一首描写桧树的诗交给皇帝:“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他指着后面两句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就是不忠吗?”神宗虽然年轻,被这个案子弄得焦头烂额,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诗人之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不关我的事。”翰林学士章悖也觉得王珪说得太离谱了,解释说:“龙并不惟独指国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称龙。”神宗点点头说:“自古自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孔明自称卧龙,他并不是国君。”王珪这才不吭声了。但是你看看,他们污蔑陷害的本领有多高!下朝以后,章悖实在忍不住了,问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让苏轼家破人亡才觉得高兴?”王硅说:“这都是舒直出的主意。”章悖不客气地说:“舒宣舒宜,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章悖后来评论王珪的卑劣行径说:“无所顾忌地诬陷残害他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事载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宋·王巩《闻见近录》)
说来说去,究竟有没有一首诗可以导致杀头之罪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结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不过是个做过几任地方官的诗人,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看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有时候也很片面,再加上免不了有些文人习气,喜欢写诗发牢骚,喜欢在诗里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仗着博学多才,喜欢在诗里用些刁钻古怪的典故发泄怨气,在士大夫圈子里传来传去,造成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舆论,但仅此而已,跟杀头的罪名八杆子都打不着。
不过,杀头定罪这种事本来就与诗歌的内容没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只要想抓你,只要想定你的罪,想杀你的头,还担心找不到理由吗?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苏轼是反对新法的。漫长的审讯终于告一段落,苏轼写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们则准备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的罪名起诉苏轼,只等神宗御笔一挥,即可结案。
而此时此刻的苏轼,神经也是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其实即便旷达超迈如苏轼,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又如何能做到心如止水?苏轼在狱中时,曾与儿子苏迈约定,平时苏迈送饭,只送肉与菜,如果被判定死罪,则以送鱼为信。一天,苏迈出城办事,拜托一位朋友代为送饭,朋友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特地送来一尾鱼。苏轼看后大惊,以为死罪不免,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想到家中的妻儿老小,想到远在南都的兄弟苏辙,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平静?绝望之余,他提笔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二首》其一)看来,明年就是我的周年,子由啊子由,我们只有下辈子再做好兄弟了(事载宋·陈善《扪虱新语》)!
难道,苏轼真的要被李定等人牢牢地钉在断头台上了?朝廷上下就没有一个人肯为这个文学天才说句公道话吗?苏轼的生命真的要终结在四十四岁了吗?
当然不会!当时开口救助苏轼的主要有这样几类人--
一是反对派中的退休大臣。七十多岁的退休宰相张方平是三朝元老,与苏家父子关系密切。老人给神宗皇帝写信呼吁赦免苏轼,但是当地政府官员胆子小,不敢转呈给皇帝。张方平大怒,就叫儿子张恕直接去交给朝廷。张恕生性怯懦,在登闻鼓院(专门受理上诉公私利害、朝政缺失、理雪冤案诉状的机构)门外徘徊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敢交出去。后来苏轼出狱后,看到张方平给皇上的这封信的副本,不禁大惊失色,连连吐舌头。原来,张方平在信中劈头就说苏轼“实天下之奇才”,劝神宗本着爱惜人才之心赦免苏轼。苏轼深知,当时说他是奇才,反而会激怒神宗,多亏张恕怯懦,没有交出这封信,否则苏轼下场就惨了(事载宋·马永卿《元城先生语录》)。
二是革新派中的退休大臣。当时早已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给神宗写信说:“哪里有圣明的时代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王安石这句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他是宋神宗器重的人物,虽然已经退居南京,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三是在职的中立派大臣。一天,宰相吴充问神宗:“陛下以为曹操这个人怎么样?”神宗回答:“不值一提。”吴充说:“陛下以尧舜为楷模,自然鄙视曹操。但连曹操这种坏人都能容忍当面骂自己的祢衡,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说了几句怪话的苏轼呢?”一番话问得神宗心里发慌,只好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澄清是非,很快就会放了他。”(宋·吕本中《吕氏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