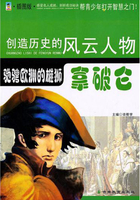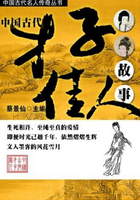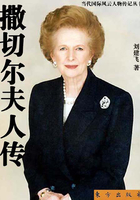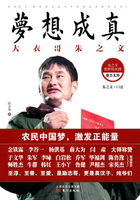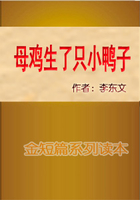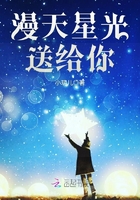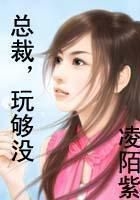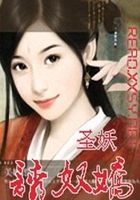苏轼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说:“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事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如果换在今天,您的学生这样回答,您会有什么表现?我想大部分人都会眉头一皱,训斥他不学无术,态度不严谨,用猜想代替证据。而欧阳修的表现又如何呢?欧阳修一听苏轼如此回答,非常欣赏。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谈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语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他还高兴地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觉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语栽欧阳修《与梅圣俞》)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语载宋·李廌《曲洧旧闻》)
想想看吧,以欧阳修在当时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身份,他这样高度地评价苏轼,苏轼又怎能不名满天下呢?就连数百年之后的我们,也不禁为欧阳修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见识和奖掖后进的热忱而深深感动!
苏洵虽然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文章也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评价。欧阳修这样形容他们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他们父子三人在京师游学,我将苏洵的文章献给朝廷。朝野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苏轼、苏辙都考中进士高第,也以文学着称于世。眉山是个距离京城西南数千里之遥的小地方,而苏氏父子一日之内就名动京师,文章传遍天下,后生学者争相仿效学习。”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二月,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一次北宋王朝最高级别的人才选拔考试--制举考试即将举行。曾经在三年前的进士科考试中小试牛刀、一举成名的苏轼兄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准备向这次制举考试再次发起冲击。那么,制举考试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考试制度?而苏轼兄弟在这场制举考试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少年成名的苏轼还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吗?
制举不同于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科”,它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度,倘若被录取,就可以获得较快的擢拔提升。参加制举考试的考生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制举开设次数极少,两宋三百年历史中,只举行过二十二次制举考试;资格审查也极为严格,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很少,能够考中的就更少,考中而成绩优异者则少而又少。宋朝三百年中考中制举的才有四十人左右,而考中进士的则有将近四万人,相差近一千倍本书有关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部分数据与观点,参考了《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以及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着作。限于体例,行文中不再单独注出。特此说明。
苏轼所应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直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所作五十篇策、论通过制举考试。显然,苏轼应考制举的策论文章再一次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不过这次赏识他的还有当朝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与司马光等考官将苏轼点为制举第三等,这是极高的荣誉。按照宋代制举等级的惯例,一、二等都是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算是不及格。自从北宋开设制举以来,只有吴育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通过第三次等,其他人都在四等以下。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大事。弟弟苏辙也不示弱,获得了第四等的好成绩。这一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
苏轼兄弟的学习和考试经历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他们一路斩将刈旗,取得这么好的考试成绩,秘诀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学生都害怕考试,有的人也对应试教育提出很多批评的意见。但是我们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读书读得很优秀的人,不会成为考试的奴隶,而会成为考试的主人。
从苏轼的读书生活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对他要求很严格;第二,他有非常扎实、雄厚的基本功;第三,他有非常科学的、有效的读书方法;第四,他善于灵活地运用知识;第五,良好的机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名人欧阳修对他的提拔奖掖也起了重要作用。所有的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才造就了少年成名的苏轼。正是这样善于读书的人、勤于读书的人,才能成为考试的主人,成为大文学家,才能在政治上实现宏伟的志向。
现在,苏轼有礼部考试第二名、制举第一名的辉煌业绩,还有宋仁宗以及诸位考官的高度评价,年轻的苏轼一定要迎来一个无比辉煌的成功了吧?他一定会得到比一般人快得多的提升吧?少年成名的苏轼在仕途上是否也会一举成功呢?
官场铇磨练
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叫做“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判官”。宋代的官制分官、职、差遣三种,前两种代表名誉、品级,差遣才是实际的职务。“大理评事”是司法机关的属官,但这只是代表苏轼名誉品级的“官”,他的实际职务是“签书凤翔府判官”,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
按照北宋官府惯例,只有相当资历的官员才能担任“签书判官厅公事”这样知府、知州的助理官,而苏轼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这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主要是由于他在进士、制举考试以及文章写作方面出类拔萃的表现。
苏轼决心在这里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用世报国的理想。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脚底板刚走进凤翔府衙门没几天,就遭遇到一连串的不顺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轼年少而才高,深受仁宗皇帝以及朝中大臣的器重,难道还会有人欺负他,给他小鞋穿不成?还会有人小看他,给他找不痛快?还真有。这个人就是苏轼的顶头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
陈公弼也是眉山人,是苏轼同乡,论起辈分来算是苏洵的长辈。在苏轼为陈公弼所作的传记中,我们能够看到,陈公弼这个人身材不高,又黑又瘦,目光冰冷如霜,语言犀利,平时脸上少有笑容,有时更是当面给人下不来台。他疾恶如仇,秉公办事,从来不会考虑自身的祸福得失。对于那些贪官污吏,他严加惩办,决不留情,但对于那些贫寒人家,却又轻财好施,有恩多义。士大夫们在一起游乐玩赏,听说知府来了,就都不说也不笑,连吃的喝的似乎都没有味道了,纷纷散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儿。
苏轼是什么性格?开朗豁达,口无遮拦,想说啥就说啥;加上少年成名,以才气自负,性格上就难免与这位陈知府发生矛盾。而陈公弼呢?才不管你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来到官府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少在这儿摆“少年成名”的架子!苏轼刚到风翔府,陈知府顺手就给了他几个下马威。
第一,苏轼在制举考试中是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科目被皇帝点为最上等,有一个同事就尊称苏轼为“苏贤良”。有一次让陈公弼听到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小小的判官有什么贤良的?”二话不说将那个同事打了好几板子,弄得苏轼非常难堪。
第二,宋朝规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官府按照惯例聚会,苏轼赌气没有去,结果被罚了八斤铜。宋朝每一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斤铜等于罚款一千六百文。钱多钱少倒是次要的,关键是太伤情面!
第三,苏轼以文章得名天下,可陈公弼经常对他起草的文章圈圈点点,反复修改,往往要几易其稿,才得交差,这简直就是对苏轼的极大侮辱。想想看,我苏轼的文章,连当朝文坛宗主欧阳修、当今皇上都说好,你一个区区的知府却乱点笔墨,真是倚老卖老!
所以苏轼在诗中不无郁闷地写道:“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客位假寐》)什么意思?呆在这个糟老头儿的手下,倒也不用担心丢掉性命,只是经常不得不咬紧牙关,忍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的窝囊气(事载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此时的苏轼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气盛,由于才华出众、科场得意,就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备加赏识,这更加使得他对前程充满自信。可是,初涉官场,苏轼偏偏遇上了陈公弼这样严厉倔强的上司,陈公弼的百般挑剔让他实在难以忍受。那么,面对苛刻严厉的上司,他是逆来顺受还是针锋相对呢?
按照苏轼的性格,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报复一下这个小老头儿。机会终于来了!
陈公弼在官府后园建了一座楼台,取名“凌虚台”,供官员们休闲时使用。楼台建好了,陈公弼请苏轼为这座凌虚台写一篇文章,留个纪念。
苏轼的这篇《凌虚台记》是怎么写的?全文不到四百字,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登上凌虚台远望,可见方圆四周都是秦汉隋唐以来帝王的宫室殿堂遗址。想当初它们是多么的富丽堂皇,坚不可摧,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可要宏大得多了!然而多年以后,想要再看看它们的模样,却只剩下一堆残垣断壁,当年宫殿的基址早已化为一片长满庄稼、荆棘的破败田地了!宏伟的帝王宫殿尚且如此,这小小的凌虚台又能如何呢?恐怕也很难长久。凌虚台尚且如此,更何况纷纭莫测的人事变化呢?谁又能预料到个人的穷达得失?命运的反复忽来忽往真是难以把握!有人想借助在世间炫耀自己来满足虚荣之心,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世间万物的发展自有持久不绝的生命力,哪里会在乎凌虚台的存亡呢?
文章的确写得好,虽然是借着小小的亭台而感怀古今,但其中蕴含着一股郁郁勃勃、不可阻挡的生机与活力。不过明眼人也可以看出来,这篇短文也是“小苏”向“老陈”射出的一支小小的讥讽之箭。
那么陈公弼的反映如何呢?依照他冷面的性格,该不会勃然大怒,再罚苏轼一百斤铜吧?恰恰相反,读了这篇文章后,一向没有笑脸的陈知府却笑了,他说:
吾视苏明允(苏洵,字明允)犹子也,某(指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大意是:我对苏洵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苏轼就好像是我的孙子,我平时之所以对他分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色,是因为看他年纪轻轻的就名声大振,担心他把握不住自己,骄傲自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要想办法挫一挫他的锐气,让他头脑冷静一些,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真往心里去了呢,对我满肚子的不高兴呐!
陈公弼虽然是个严厉的上司,但他的心胸非常开阔,他让下级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刻石立碑于凌虚台旁。也许,陈知府就是要通过这篇碑记告诉后代的年轻人,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少年成名,怎样才能真正做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要让年少才高的苏轼领会他的一番良苦用心。
陈公弼对苏轼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就成为家长、亲戚、教师、同学心目中的小明星、小皇帝,大家对他们真可以说是众星捧月。这容易使他们形成一种观念,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上天赐给他们的,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与自己的家人、朋友、老师都没关系。其结果是即便顺利考上了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也只不过是个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不是一个心理生理健康、健全的人。
苏轼是幸运的,在家里有严父慈母的教诲,在学习中有欧阳修这样的导师奖掖提携鼓励,到了工作岗位上,又有陈公弼这样严厉的长辈时时敲打他,这对于苏轼人格的健康成长有很大帮助。多年以后,苏轼曾不无悔悟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在《陈公弼传》中写道: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意思是:我在凤翔做官的时候,年少气盛,不懂事,屡屡与陈公弼大人发生争执,有时候甚至怒形于色。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后悔。
苏轼写《凌虚台记》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还很肤浅;而当他写《陈公弼传》时,已经四十六岁了,在经历了仕途、人生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他自然理解了当年陈公弼严格要求他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以撰写传记的方式表达对长辈陈公弼的深深敬意。苏轼一生只写过十篇传记,其中只有二篇传记涉及当代人物,这十篇传记中,为陈公弼所写的这篇最长,也最为详尽。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回到了京城。皇帝后来想将他招人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做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是宰相们认为苏轼的资历还太浅,经验不足,需要经过更多的锻炼,于是让他改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这对苏轼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降临到苏轼的头上。首先,这一年五月,他的夫人王弗在京城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妻子的丧事还没有料理停当,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于是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老家,按照规矩须为父亲守丧三年。
苏轼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熙宁元年冬,当他准备重返朝廷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而自己后三十年的人生命运将不得不与这场政治风暴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年离开家乡去参加科举的时候,他曾与弟弟苏辙相约,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共享田园之乐,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眉山,这个愿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