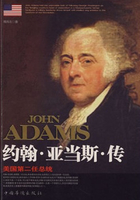下连当兵,受贝当青睐。
返校就学,外号不迭。
刻苦向学,以优异成绩毕业。
对戴高乐来说,考取圣西尔军校,是其军旅生涯的开始。这当然是美梦成真,如愿以偿。但当时国家、军队所处的形势如何呢?
本来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人们都把报仇雪耻、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希望寄托到军队的身上。由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情绪的高涨,整个法国都对军队怀有爱慕、敬重之情。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以考取圣西尔军校为自豪。但自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最初10年间,法国军队声望每况愈下。
首先,顽固的保皇分子布朗热于1886年就任陆军部长后,因主张解散国会、修改宪法,谋取实权,阴谋推翻共和政府,建立波拿巴式的军事独裁,彻底暴露了他的“最忠诚的共和党人”的假面目。他于1887年被免职,1889年因发动政变未遂逃往比利时,不久殉情自杀。从此,资产阶级乘机清除了军界一大批共和分子,在法国“开始了反对****的漫长历程。爱国主义同军队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嘲笑复仇,不再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沦陷而悲伤”。[法]奥利维埃·吉夏尔:《我的将军》,第1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1894年,在法国又发生了一起影响至为深远的事件,即前面已提到的德雷福斯案件。这一事件持续了达12年之久。这是法国反犹太军官团炮制的一个恶性案件。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左派多数人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无罪的;右派多数人认为德雷福斯有罪;而军方则上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尽诬蔑之能事,硬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为了军队的所谓荣誉和威信,反对改判给德雷福斯平反。结果,军方的行径暴露后,军队威信一落千丈。这对军队的伤害是灾难性的。
然而,无独有偶。军队在受到上述伤害的同时,还因政府1880~1905年间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有大批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高级军官遭到清洗。这不仅降低了教会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影响。
这样一来,军队的威信扫地。原在法国对军队、军装和军旗的崇拜已为不信任和蔑视所取代。人们不再颂扬军队,青年也不再羡慕军人。由于这一影响,本来在19世纪末每年报考圣西尔军校的人员有2000人,而到1908年则只有300人了。另有资料说,从1900年到1911年,报考圣西尔军校的人数从1895人减到831人。
在军队面临如此困境,圣西尔军校处于如此不景气的形势下,戴高乐仍然初衷不改,矢志不移,仍决定到军队去,进圣西尔军校去寻找他的法兰西。他后来在《法国和它的军队》中写道:“我之所以报考圣西尔军校,完全是为了阿尔萨斯和让法兰西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对军队仍保有原来的信念和希望。正如他在《战争回忆录》里所说:“当我参加陆军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当时各方面虽然有许多批评苛责之词,然而军队还是镇定若泰地,甚至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上),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戴高乐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心情,遵照共和国1905年3月颁发的关于圣西尔军校新生必须首先下连当兵锻炼一年的规定,于动荡不安的1909年7月背起行囊,前往法国北方,到现为加来海峡行政区中心、位于里尔和巴黎之间的老城阿拉斯,去步兵第33团第9连当兵。
这个又高又瘦的步兵,身上紧裹着一套军装,手持一支沉重的“勒贝尔”步枪,毫无怨言,但却闷闷不乐地开始履行自己的天职。除放哨、演习、队列训练外,打扫卫生、削土豆等公差勤务,日复一日地使他在阴沉沉的兵营里经受没有尽头的煎熬。一些陌生、粗鲁、简单的人,整天盼着礼拜天放假,喝白酒,有些人净说淫秽的笑话、骂人,士官们粗野打人,伙食令人很不习惯。这一切在当地驻军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他对这种生活不禁感到枯燥乏味。
戴高乐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打趣地写道:“真的,我那时认为任何一个天才的联想家,都绝不可能找到削土豆与爱国和收复失地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难得的一点闲暇时刻,他就到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去看僧侣们精心收藏的图书。此外,他入伍时自己还携带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籍。他最喜欢阅读深刻描写士兵遭遇的卓越作家维尼的著作,借以自慰。要知道,维尼是一位热情宣传军人光荣和英勇的作家。他的著作对戴高乐下决心参军起了不可或缺的影响。但是,对戴高乐这个年轻的步兵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维尼的《士兵的不自由和伟大》。因为维尼深刻了解军人内心世界,他说出了士兵职业的真情:“军队是民族中的民族: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之一。这好似从民族身体上分离出来的一个活人,这个活人又好像一个智力不发达,被禁止发展的小孩。现代不打仗的军队被认为酷似宪兵队。它似为自己的存在而羞耻,它自己也不知道它相信的是什么和它在现实是什么。”
维尼的这番话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这个年轻人带着复杂的感情同意士兵是“人类野蛮行为中最不幸的残余,但他同时又比什么都值得民族关怀和爱护……”他特别喜欢维尼所说的一句话是:“一切能促使明理人当兵的最高尚的东西,与其说是战斗荣誉,勿宁说是能自豪无悔地克服困难和不懈地履行有时令人仇视的义务的本领。”
维尼是戴高乐一直喜欢的作家之一。戴高乐常以维尼的话勉励自己。因为维尼的话能给他力量,帮助他克服困难。这时,他的衣袖上有个特别的条纹,证明他是预备军官,在兵营里不过是个临时过客。由于在很多场合别人都把他看作和军士一样,所以他的活比普通士兵轻便多了。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怀有无限的希望,所以他虽比往常更孤独傲慢,但对自己轻松的工作却做得特别无可指责。可是,到1910年4月,与他同期的大多数军官候补生都已得到中士军衔,但戴高乐没得到提升,还是一名下士。这时,有人问他的领导上尉连长杜涅为什么戴高乐的模范行动得不到表扬,得不到提拔?对这个问题,杜涅上尉打趣地回答说:“难道您要让我把一个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心满意足的人提升为中士吗?”
上尉知道自己答话的含义。虽然他的这个士兵,更准确地说,是见习学员,执行列兵勤务很出色,但未必会只想当个军士。
但是,戴高乐对这一不公对待并未当回事。他仍陶醉在阿拉斯的梦幻之中。黎塞留曾经围攻过这个城市。后来,蒂雷纳在此战胜了当时与西班牙人共同反对过法兰西国王的伟大的孔代。在阿拉斯有很多往事值得回忆。这也给戴高乐提供了思维的营养。他对现代法兰西现实的顾虑,比对法兰西历史的顾虑少得多。这只是由于兵营的围墙把共和国的士兵牢牢地与引起国家波动的一切隔绝了。当时,军官们不让他们看报。如果军官发现在列兵手里有饶勒斯的社会主义《人道报》,那会引起爆炸性效应。
那么法兰西当时的形势怎样呢?早在1905年末,即最后通过了“政教分离”的法令。围绕驱逐宗教协会引起的冲突逐渐平息。据一位能说善辩的大臣所说,吸引劳动者注意力脱离农事的圣火已彻底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