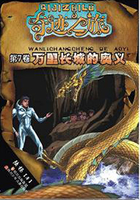尤寻租恍然大悟似的一拍手:“你看,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怎么会那么巧,就在他送钱这天你爹就失踪了,这钱又不翼而飞了。十万块钱啊!要包好大个包呢,足有半尺厚,你妈也能看见,可也巧,你妈也在这一天就不会说话了,这都是巧合吗?”尤寻租越说越邪乎。
俗话说,假话重复三遍也会变成真理了!尤创新也晕晕乎乎的六神无主了,叹着气随声附和道:“现在真是死无对证了,等建公回来再问他吧!”
第二天太阳落山以后,尤建公兴高采烈地赶着马帮回到场院,卸下驮篓让牲口打滚,手中还拽着缰绳,见会计尤季雨迎面走来问他十万块钱交给谁了,便不以为然地说道:“交给铁山大叔了,大婶在做饭,也看见了。”
会计尤季雨吞吞吐吐地悄声说:“创新可说她没找到这十万块钱。”
尤建公把缰绳拴到马棚横梁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给会计尤季雨,余兴未尽地沾沾自喜道:“我比他多卖了四百多块钱,你数数。”
尤寻租从厂部办公室走出来,斜眼看着尤建公,别有所指地说道:“几百块钱是小钱,要比上十万块钱,还差几十倍呢!”
尤建公耿直地说道:“积少成多吗,每次进城多花几十块下饭馆,一个月就浪费好几千块,一年就十多万了。”
尤寻租板起面孔,冲尤建公正经八百地说:“买马那十万块钱呢?不是季雨大婶亲手交给你了吗!”
尤建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我也是到铁山大叔家亲手交给他的啊!”
“收据呢?收条、白条子也没关系,有个铁山大叔的签字就行。”
“什么收条签字的!我替铁山大叔领过那么多钱,哪一回他也没开收条签字呀!”尤建公气呼呼地来到尤创新家,亲自动手又翻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那包十万块钱。
尤建美早已做好晚饭,见哥哥尤建公垂头丧气的回来,她就一边把桃子酱拌到面条里,一边问他卖了多少钱。兄妹俩吃过饭,一个在刷碗一个在点油灯,院里进来两个民兵,二傻子和三混混,他们原先都是村长手下的民兵,帮助村长跑腿打杂和征收农业税,后来尤铁山办起了罐头厂,这两个民兵又成了厂里的保安。二傻子是个三瓣嘴,说话嘴里漏风,吃饭嘴里漏汤,这生理上的缺陷也是近亲繁殖的后遗症。三混混是个短粗胖,像个肉墩子,好吃好喝,有奶就是娘,只要给吃的,帮忙打架都能赤膊上阵,决不后退。他们两个始终保持双重身份。当村长派遣他们跑腿时,他们就是野狼沟村里的民兵;当他们站岗放哨保护罐头厂马匹设备时,他们就是野狼沟罐头厂的保安。尤铁山失踪以后,他们俩都听候总管尤建公的调遣,这两天改朝换代尤建公跑外当供销员,厂长总管的位置落到尤寻租身上。今天晚上尤寻租给他们俩一人一盒劣质烟,“去把尤建公请到厂里过夜,帮他好好回忆回忆那十万块钱,到底放到哪去了。”
他们俩像鹦鹉学舌似的一字一板的把尤寻租的原话转达给了尤建公,然后又歉意十足的冲兄妹二人频频点头示意:“多多包涵!别见怪!”虽然心中十分气愤,却又不便发作,尤建公只好起身同他们俩一块来到厂部过夜。
当尤创新知道尤建公被软禁起来已是第二天了,她板起长瓜子脸责怪着尤寻租:“你没有证据就把人家抓起来,这是犯法!”
尤寻租早就打好了腹稿来对付她,便慢条斯理地说:“侵吞巨款是贪污,是犯罪!二傻子和三混混是民兵,是维护村里的行政秩序,你别光以为他俩是厂里的保安了。”
尤创新听了以为是村长下令叫软禁的,就又来找村长说情。一进村长家就被张文野缠住,问长问短,总围绕着结婚这个主题周旋,尤创新的长瓜子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几乎是哭丧着脸说:“我妈病成这样,我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连大学都耽误了没上。”见到村长出来,便连忙上前去问软禁一事。
村长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是儿子尤寻租假传圣旨,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村长是既不想得罪儿子,也不想得罪未来的儿媳妇,就含糊其辞的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你爸爸最信任的就是尤建公,可惜他英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看错人了!”
一提到父亲,尤创新的心理就不是滋味,很想哭,鼻子酸得让她说不出话来,强忍住眼眶里的泪珠央求道:“把建公放了吧,钱也不见准就是他拿了。”
村长尤保民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些钱都是你的,是你们家的,当然你说了算。”
当尤创新以村长的名义来命令尤寻租赶快放人时,尤寻租早已做好准备。他给二傻子和三混混一人一瓶劣质白酒,叫他们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到厂部来向尤建公请愿,来个长跪不起。野狼沟北坡的群众听说尤建公私吞十万元买马款,造成十万斤桃子运不出沟,眼看就要烂了,眼看又要没粮吃了,又要顿顿是桃子宴:煮桃子、炒桃子、蒸桃子,连猪都不想吃桃子了,牙齿都给桃子酸倒了。他们就三个一伙,五个一帮,拥进厂部办公室门口在二傻子和三混混的指使下,都拉着孩子们一起跪下,有的人还按着孩子的脑袋向办公室磕头。人们不约而同地哭丧着脸央求道:“快行行好吧!尤建公,快买马吧!桃子就要烂了……”
坐在办公室里的尤建公见此情景心中十分惊诧,不由得站起来向窗外窥察,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听清了,是喊他的名字,是在向他请愿,向他乞求,请他交出这十万元买马钱。尤建公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屋里团团转,突如其来的景象令他震惊、心酸、难过,他冲出木门,冲跪在院中的群众喊道:“乡亲们,我也很着急啊!也怕这桃子运不出去,烂在沟里,我也着急买马,可这十万块钱我交给铁山大叔了……”
群众还是不肯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死人嘴里没对证,行行好,把钱拿出来买马吧!”
“要不,我领你们到我家翻去,行不行?要是我昧下了,叫天打五雷轰,出门叫狼吃了……”尤建公声嘶力竭地向众人解释着,好像有些人动摇了,也许是跪疲乏了,想站起来,可是二傻子和三混混在忠实地执行尤寻租的计划,不断地在人群中煽风点火。“别信他瞎掰,钱是真格的,为了钱,人都会害命的。”
双方僵持不下,众人的情绪在跌宕起伏,尤建公嗓子也喊哑了,眼泪也哭干了,实在是有点绝望了,他搬开饲养员给马铡草的宽铡刀,冲着群众说“乡亲们不信任我,我只好用死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他把宽铡刀支成直角立着,自己躺在刀架上,短脖子就横在刀槽上。这把铡刀平常正好能形成直角垂直地面立着,但不稳当,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群众见此情景纷纷围过来,要阻止他冒险,二傻子和三混混也惊异地探头窥测,这时尤寻租走过来不以为然地讥笑道:“死能吓唬谁呀?只能吓唬小孩!”二傻听了似乎恍然大悟,鸡啄米似的直点头,张开三瓣嘴鹦鹉学舌般地跟着喊了一遍。
人群中冲出一个姑娘,用手扶住刀把,粗声大气地抗议道:“大伙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要我哥来赔这十万块钱。哥哥,你快起来吧!别想不开,认赔吧!这得容个空,十万块可不是小数目,咱俩明天就进城打工去,一定还钱,就是把我卖了,我哥也不会不还钱。”
她的声音像座大钟似的,瓮瓮震耳,能盖住众人七嘴八舌的嘈杂声,围观的群众自动让出一条道来,尤建美搀扶着她哥哥向工厂大门走去。背后传来三混混的嘲笑声:“就你那副长相还能卖出价来?”人群也跟着哄堂大笑。
尤建美回过头来边走边骂:“我长得再丑也比你强,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三混混。”
尤建美的相貌也真是丑得出奇,她的脖子比她哥哥还短,可以说是没有脖子,整个一个大脑袋是直接安到肩膀上的。三混混受到讥讽颇不甘心,在后边蹦高跺脚抗议道:“我打光棍也不稀罕要你呀!”
尤建公一直沉默着思考着,他认定妹妹的看法是对的,这十万块钱就是要他来赔偿。妹妹尤建美满腹牢骚:“今晚这场戏就是有人导演,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谁最恨你,就是尤寻租,他把你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嫌你碍事,他想独吞罐头厂,早晚得跟他算账。”
尤建公劝慰道:“你也没看见,只是猜测,别老爱用恶意去猜测别人,要与人为善,这是爹妈生前教导咱们的。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坏事真能变成好事,进城打工还许真能挣大钱。”妹妹愤愤不平地抱怨道:“这十万块钱债扣到咱头上也太冤了!”
尤建公说:“咱沟里这么穷,如果咱俩真挣了大钱,给家乡几十万也不是不应该的。”
妹妹叹了口气摇头道:“你可真会给自个吃宽心丸!”
尤建公苦笑道:“老是生气,那是跟自己过不去,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明智一点的人是不该生气的!”
次日,太阳刚从东山探出头来,尤建公兄妹二人收拾好随身衣物和行李,两个人各背一个包,关上院门,冲房后祖坟磕了头,然后又到厂部。饲养员尤老大说:“你们真要进城打工,把你们自己入股那匹黑马带走吧!驮着骑着也省点力气。”
尤建公摇头说:“不啦,留下运桃子吧!我这有本书请大伯交给尤创新,告诉她,这里夹着我的辞职报告。”尤建公从背上的行李包中掏出一本《企业管理学》,双手递给了饲养员。兄妹二人迎着初升的太阳,顺着上坡的羊肠小道匆匆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