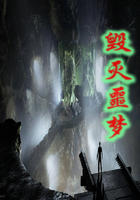其实柳正庭并不是不着慌。此刻,他心中像火一样的燃烧着。但是他并不是怕这几张大字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里,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为了人民得解放,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时,他面对着几十万美式装备的蒋匪军,头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随时都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在那种艰险环境中,他都没有皱过一下眉头,难道今天,几句攻击谩骂,他能看在眼中吗?他所担心的是当前的工作,这么一来,一切都乱了,弄不好,会给生产事业上带来损失。东溪乡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社队,一跃而成全公社的首户,这是他的心血啊。但这一心血却被人视为驴尿马粪,他能不伤心吗?在以后,他就是吐出真红血,也是小豆水了。谁能不心痛呢。
但是他没有把这一切表露在脸上。看过大字报后,他就走出人群,向大门口走去。
这时恰巧刘富贵也叼着香烟走了过来,刚好和柳正庭打了个照面。四目相对,使刘麻子刘富贵不禁打了个寒战,像窃贼一样,低下头溜进了人群。
第二天,第三天,大队院里仍然是闹哄哄的。有些平时受到柳正庭训斥的人也认为时机已到也零零星星地贴出了几张寡墨黧大字报,来教训教训这老东西。
整个大队院里,每天从早到晚,一直是人来人往,后来人们看得多了,气氛又慢慢活跃起来。
太阳落山了,人们开始散开了。三五成群像刚刚看完一出好戏,一出大门就指手画脚,说说笑笑地议论起来。有些人,趾高气扬地仰着脸,挺着胸,一边走一边哼着京调,好像大字报给他出了一口冤气;有些人却像在窄路上遇到了冤家,蛮不讲理地和他过不去,他怒气冲冲,骂骂咧咧,那架势仿佛要和谁闹个你高我低为止;有些人却像是打输了官司,摇摇头唉声叹气,沉沉闷闷地苦着脸;还有的人,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也和往常一样,心平气和不慌不忙,一甩手扬长而去。
人们走完了,大队院里寂静了。零零落落的大字报纸片,仿佛西瓜市上的西瓜皮,满地都是,随着风在院子里打转转,墙上的几张也耷拉下脑袋,有气无力地挂在那里……
随着太阳光辉的收缩,大地上的一切都慢慢地沉陷在一片茫茫的夜雾之中。
夜,寒冷而黑暗的夜来了。
大鲁枕着双膊躺在被卷上,双眼怔怔地凝视着屋顶,脑子参,里却陷入一片纷乱的思绪之中。
近几天来,村子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革命造反队,大字报,刘富贵,这究竟是一场什么呢。被人尊敬的柳支书却要被打倒,无赖恶棍却成了革命家,这……就是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他早在去年冬天就一知半解地听到了。但现在这场风暴降临到了他的村,他却感到来得突然,莫名其妙了。
“刘富贵也配得上起来革命吗?”
提起刘富贵,他就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件事:
一天,他和小翠在小翠院子里玩。小翠妈李氏在晌午时从地里回来了,她正准备着做饭,忽然刘富贵气势汹汹地闯进来,一把揪住李氏的衣领,恶狠狠地问道:“你看见什么了?”
“没,没看见什么呀。”她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一时摸不着头脑。
“老东西,我妈和你相跟着回来。你,你向别人说了没有。”刘麻子的目光直逼着李氏。这种威逼的目光,使这个善良而胆小的女人,不禁颤斟起来。
“没、没向人说呀。”当她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立即为自己辩解:“一回来我就进家来了。一路上没和谁说……”
“量你也不敢。”刘富贵松了口气,却把她推倒在地。歪着脖子,骂骂咧咧地扬长走了。过了一会,李氏才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但嘴角却跌破了,血一滴滴地流了下来。
大鲁和小翠一时被吓得怔怔地呆在一边。刘麻子走了以后,小翠才扑到妈身边哭起来。
“婶,他怎么打你呢?”大鲁不解地走过来问道。
“好孩子。”她摸摸大鲁和小翠的头,把他俩搂在身边,流着泪告诉他俩:今天我和刘麻子妈一起从地里回来,路过队里南瓜地时,她顺手摘了几个南瓜。我劝说了她几句,就……
她委屈地指着大门,一边呜呜哭,一边骂了起来:“牲口。”
大鲁看着李氏嘴角的血,心中气愤极了。他攒着拳头,望着门外,愣愣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自己快快长大吧,长大了,好好揍他一顿,给婶出气……。
但是现在,这个无恶不作的刘富贵竟是挺身而出的革命者。而且,他是向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开刀,这算什么“革命”呢……。
门忽然推开了,大鲁抬眼一看。啊!说曹操,曹操就到,进来的原来就是刘富贵。他心中一震,微微欠起身来:“坐,坐下。”
剂富贵看了他一眼,顺从地坐在炕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大鲁,我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大鲁一看见他的那张铁青的麻子脸,心中就有些腻了。他懒懒地问道:“有什么事?”
“参加我们的革命造反队吧。”
“我?”大鲁鄙视地笑了笑:“嘿,我可没有那本事。”
“不,你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刘富贵毫不掩饰地把他的目的说了出来:“你是民兵连长,你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其他人就……”
大鲁明白了。原来是把他当作招魂牌啊。他心中不禁冲起一股无名之火。“民兵连长就是军人,军人是服从上级命令的,绝不能任人摆布!”
刘富贵见大鲁发起脾气来,双眼愣愣地望着他,张口结舌地说不出来。摆在面前的这件事,并不像他考虑的那样简单。
要在以往,他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火性。但今天他却没有发脾气,只憨憨地冲他笑笑说:“这可是工作队老张的主意,你总不能不相信老张吧。”
他坐了一会,见大鲁还不发表态度,就站起来说:你考虑考虑再说。
说完,他转身走出了家门。
屋子里又陷入了一片寂静,一片空荡荡的无聊的寂静。
这天黄昏时,村子里忽然来了一支十几人的学生队伍。他们都背着背包,背包后面都挂着一面语录牌。为首的一个男学生除了背着背包,在胸前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彩色像。手中还打着一杆红旗。红旗上大大地印着三个大字:长征队。
他们都走得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了。
这里虽然没有设立红卫兵接待站,但是善良的东溪乡人们还是把他们安置在各家各户。
大鲁把那个带队的领到了他冢。那学生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一进门就热情地和刘氏打招呼:大娘,我们来打搅您老人家了。
刘氏立即迎了上来:“求还求不来呢,快上炕,你是……”
“大娘,我叫张闯。”张闯立即给她自我介绍,“我们是河南林县中学长征队,要上北京,要到延安,要到井冈山,要到祖国各地去串联串联。”
他给他们讲了五四运动时,学生的作用,并告诉她,这场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大革命,又是学生开始的,学生是主力军。
“喔,你们小小年纪……”刘氏虽不懂得“五四”、主力军。但总感到他们小小年纪就出来奔波,是了不起的。“你们真辛苦了。”
夜饭,刘氏特意给张闯做碗白面条,但张闯却执意不肯独自吃,刘氏只好把面条倒在大锅中。这一来,刘氏更喜欢这个张闯了。
以前,她招待过大鲁许多的同学,但这些人中,只是和大鲁混在一起谈啊、笑啊。可这位张闯,能和大鲁说得来,还尊敬她,还能讲出一大套一大套的话来。她的大鲁就不行啊——
真是多读一天书,肚里就多一份墨水。
饭后,她还特意地给张闯烧了一锅水,让他洗洗脚。
当张闯把鞋袜脱掉,刘氏和大鲁一看,却都惊讶地叫了起来。原来张闯一只脚上的大拇指和二拇指皮裂开了,白刷刷地露着白骨。脚掌上打起了一个个的水泡。
刘氏心痛她叫起来:“这,这是何苦呢?”
“大娘,这没什么。”张闯不以为然地对她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熬过来了,我们这算得了什么。
“是倒是,可这……”
“为了革命,就是流血牺牲,我们也在所不惜。”
张闯虽然是轻轻和刘氏说着,但句句都敲到了大鲁的心上。他被感动了,更感到这位长征队长的可爱可敬。
晚上,他俩睡在一起。张闯给他谈起了文化大革命,谈起了长征串联,也谈起了他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憧憬……
窗户上的月光慢慢地从东边移到西边,最后的一抹月光也渐渐消灭了,但大鲁和张闯还在兴致勃勃地畅谈着。
大鲁把村里所发生的事和他的见解都告诉了张闯。张闯听了,对他说:“刘富贵过去虽然不好,但能在这场大革命中站到革命造反立场上,而且能写出第一张大字报,这种精神是可贵的。革命,尤其是在革命最开始的时候更需要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来打开局面。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精神,哪能搞革命……”
他讲起了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领袖李大钊、毛主席、周总理……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冲破种种白色恐怖,为革命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献出了家族亲属的生命……他还进到了黄继光、董存瑞、杨根思、《五女投江记》中的烈女。
大鲁虽然也读过这些书,懂得这种英雄人物,但是每次都没有比得上张闯给他讲得生动、有趣、感受之深。他佩服张闯,佩服他的智慧和才能,更佩服他为革命万里奔波的革命精神。
当他又一次提起他们村的柳正庭时,对张闯说:“我实在想不通,他是共产党员啊,他反党,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
“不可能?”张闯爬起来,点起灯来,在他的挂包里取出了许多的传单,拣出两三份递给大鲁说:你看看这个,也许你也会感到意外。
大鲁把灯挪过来,展开传单,只见上面印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坚决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于是张闯又讲起了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他讲到刘少奇的招降纳叛,讲到贺龙的“二月兵变”,讲到陈毅是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可能吗?在以前,谁也不会相信的,但现在在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居然被揭了出来。他们是披着红旗反红旗。这种人具有欺骗性,迷惑性,虚伪性。你们村的柳正庭,不能不考虑他是不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的人物。因为他是当权者,执行反动路线,那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了。
已经半夜了,张闯谈着,谈着,竟慢慢地闭上了眼。他实在困乏了,不一会儿就发出了呼噜声。大鲁也没再打扰他,也合上眼,但他却没有半点睡意。一个清晰的示意图像越来越清楚地印在脑子里。
资产阶级司令部——刘邓——柳正庭。
革命闯将——张闯——刘富贵。
张闯和大鲁一起睡到吃早饭时,才让刘氏叫起来。
吃过早饭,张闯掏出粮票、钱来,刘氏却说什么也不让留:你们出门人,难处多啊,带着吧,大娘不在乎这些,你们在外不受苦,我就心安了。
张闯过意不去,把粮栗、钱偷偷丢在炕上,就匆匆忙忙集合队伍了。
当他们被村里人送出村外时,大鲁忽然赶了上来,叫住了张闯:“好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把张闯留下的粮票,钱又硬塞在他手中。但当张闯展开手中时,却发现握在手中的,不仅有他留下的粮票、钱,还有一张崭新的五元票。“啊!这是为什么?”
他激动地望着大鲁,喃喃地说道:“不,不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到路上好好医治一下脚。”
他的真挚感情,使张闯这个硬汉子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望着大鲁诚恳的脸,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鲁拍拍他的肩说:“谢谢你,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们住在这偏僻的山沟里,交通不便,消息太闭塞了——好了,赶路吧,再见!”
张闯含着泪水,向他点点头,忘情地又用旗杆点着地面,每走一步,破碎的竹竿头,嚓地响一下。
嚓——嚓——嚓——,他们转过了山看不见了,大鲁还愣愣地站在一边。一他多么懊悔自己对学校的“失约”啊,如归校,他不也像他们那样,为革命献身吗……。
这一天,在大鲁的脑子里实在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嚓嚓嚓的破竹声常常回旋在他的脑际。他想起了他谈到的一切,他记起了他脱了皮的脚指头。
傍晚,他怀着一种异常的心情来到了刘富贵的门前。但当他把腿迈进门槛时,心情却忐忑不安起来。
“怎么向刘富贵说呢?难道我大鲁还不及他刘富贵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