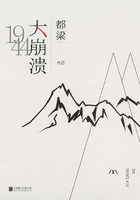这么多年来,在行政权力的指挥棒下,跑部钱进的风气污染大学的学术殿堂,全国各高校为了迎合上级口味的学术造假已经成为学术圈潜规则。偶尔被曝光一两例,往往都是被其他学校甚至国外的同行所揭发,而刚一披露,就会很快被这些学校的“运作能力”所捂住。但交大难能可贵的是,两年多来,这几位坚持举报的教授并没有“被和谐”,领导想做工作,当和事佬,居然也搞不定。
这就是我感到高兴的原因,它说明交大的传统没有丢!
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听说母校出了这档子丑闻以后,在多次校务会上,都有教授和院长系主任们,批评校长书记。
我所感受到的交大最宝贵的传统就是教授可以“骂校长”,我读大学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心目中的大学就该是这个样子。我知道经常有教授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很尖锐的意见,搞得校长书记很难堪。
交大不仅教授可以“骂校长”,我一个学生干部,也可以对学校提意见。当年我年轻气盛,一个人直接跑到行政楼,敲门就进去找校长书记提意见,现在看来我当年的那些意见水平真是不高,不过校长书记们一点儿也没怪我没大没小。
我最激烈的一次“骂校长”,是我已经毕业准备离校的那个暑期。那年交大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不好,搞了一次大规模罢餐事件,我听到这件事,也挺高兴,罢餐可能形式过激了一点儿,但至少说明母校的师弟师妹们有一种民主意识。不想这事被定性为不稳定因素,学校居然把几个带头的同学给处分了。
那天晚上,大概是10点,我给当时的校长徐通模家里打电话,我一打过去,问“是徐校长么”,那边说“是”,徐校长是认识我的,我接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说的最尖锐的话,大概是,“你们这么搞,把交大的脸都丢光了”。我之所以当时这么气愤,也是出于我对学校的感情,觉得交大搞出这样的事情,也有损我们毕业生的脸面。我当时也并没有想到我是在批评一个“副部级校长”。不过让我事后有些感动的是,徐校长在电话那头,耐心听完我一顿骂,居然承认学校处置失当,语气还有几分惭愧。
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我才感到这些细节的可贵。这些年来,中国高校的行政化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学办得如同衙门。而且很多人身在其中还并不自觉。我认识一位老师也是知名教授,在北京一所全国著名的高校任教,一次和我聊到,他有一项计划,想找分管副校长交流一下,结果约了一个月,副校长居然都还没时间,他倒是很体谅,“现在校领导实在是太忙了。”我简直不可思议,天底下就校长忙?大学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询问其他一些学校的教授,大家都觉得不奇怪,各个大学都是这个样子,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官僚气重。现在学校里,教授见了校长都是毕恭毕敬,校长有个什么指示,谁敢不遵从。
由此看来,还是母校让我觉得比较舒服,那几个给学校捅娄子的老教授值得敬佩。最好其他老师同学也要向他们学习,发扬较真儿的精神,不唯上,只唯真,如果还有什么脏事儿,再捅出几个来才好。没有激浊扬清的正气,还叫大学么?
只要这种作风还保留,交大就依然还是一所无愧于其使命的学术殿堂。
让我怎能不爱她?
(2010年)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吗?
如今有一些学者都在写文章怀念民国时期,讲那时候做一个知识分子收入有多高,能住洋楼,能请几个老妈子,出门有车夫,颇有世风不古之感。实事求是地讲,民国时知识分子地位确实是高。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经济活动,让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略窥一二。虽然很多人都在争论鲁迅是不是巨富,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工资水平比今天的普通大学教授高了不知多少倍。鲁迅当年买下北京的三进大院,只花了十几个月的工资,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认为,如今中国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也就符合市场规律,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在民国时期,知识是稀缺资源,供给不足,而且获得知识的成本也很高,工资水平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比如胡适,一回国就当了北大的教授,工资也发得很多,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当时“海归”很少,出国很困难。且不说别的,去美国光坐船就要一个月左右。其实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知识阶层也还是稀缺的。那时候就是从国外读个硕士回来,评个教授也不是很困难。
而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每年都有大批海归归来,带着博士学位的也不在少数。再加上中国本土每年还产几十万博士,大家都争着往大学里挤,而大学就这么多,自然是供大于求。且不说教授了,要当个助教都很困难,队伍排得老长。如果把胡适放到今天的大学,要评个讲师估计也很困难。所以说教授工资水平的下降,跟市场规律是相吻合的。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是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在中国,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西方社会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去经商,其次是做学问,再次才去当公务员;而中国是完全颠倒的,最优秀的学生去考公务员,其次往学校里挤,最差的只好去经商。大学市场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高福利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许多大学教授享受着跟实际贡献不相称的福利,还怨声载道;而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要进学校却很困难。这些教授其实是跟中石油和中石化一样,成了垄断的受益者。
所以说,如今有人在酸溜溜地怀念民国教授的高收入,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现象。甚至我觉得大学教授的工资应该再低一点,能保证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足够了。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英国女王在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时,发现任天文台台长的天文学家詹姆·布拉德莱的工资很低,表示要提高他的工资。布拉德莱得悉此事后,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人,将不会是天文学家了。由此看来,低一点的工资,反而可以促进学术的进步。而在中国,有些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年收入都达到上百万了,学术反而乏善可陈。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横向对比来看,知识分子的工资也不应该太高。比如在美国,很多人就认为,淘大粪的工人应该比大学教授工资高。因为淘大粪是一种辛苦的工作,没人愿意干,而知识分子则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很多乐趣,很多人都愿意干。既然大家都愿意当教授而不愿意淘大粪,那为什么还要给教授更高的工资呢?今天很多学者只知道叨念民国教授工资有多高,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淘粪工人比美国的淘粪工人工资低多少。
在美国,一个开垃圾车的,一个开大货车的,或者一个修下水道的,年薪十几万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享受很好的职业保障,依靠工会组织的保障,工作非常稳定,相当于我们说的终身教授,他们个个都是终身司机,终身管子工。
所以,如果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工资不是低了,反而是高了。我经常在说,社会转型会让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空间,但如果你理解的未来是会让知识分子有收入意义上更好的待遇,那我敢掏空我的钱包和你打赌,这种期望绝对错了。
(2012年)
兄弟我当年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的出国经历,却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别人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平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