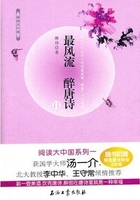海明威
潘普洛纳,是纳瓦拉山区的一个镇,常年受太阳的炙烤,镇上建筑的墙都是白色的。每年7月的最初两个星期,这里便要举办世界性的系列斗牛赛。
长长的双排木栅栏,形成了镇主街至斗牛场的一段长长的入口。这样,公牛通道约有二百五十码长。人们严实地挤在通道两侧,目光顺着通道朝主街看去。接着,远处传来一声单调的传话。
“它们出发了。”所有的人叫喊起来。
“是什么?”我向身旁的一个人问道。那人正俯在混凝土栏杆上,远远地把身体探在外面。
“公牛!有人把它们从镇那一头的牛棚里放了出来。它们正在镇上飞跑着。”
“唷,”赫塞尔芙说,“他们干吗要那么做?”
接着,从围有栅栏的狭长通道另一端,跑来一群男人和男孩。拼命奔跑。通往斗牛场的大门打开,他们便一窝蜂地跑到入口层下面,涌进斗牛场。然后,又是一群。奔跑得更是拼命。径直从镇的另一头,沿长长的栅栏疾奔而来。
“公牛呢?”赫塞尔芙问了一句。
随即,公牛出现了。八头健壮、凶悍、光亮的黑牛,上下甩动着头,飞速疾驰过来。牛角是光秃秃的。随这八头公牛一起奔跑的,是三头小公牛,颈脖上穿着铃铛。它们紧紧相随,跑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在它们前面横冲直撞地狂奔的,是潘普洛纳镇上殿后的一群男人和男孩,整个上午,他们在公牛的追逐下,疯狂窜逃一条条大街,以取一时之痛快。
其中一个男孩——穿蓝衬衣、白帆布鞋,系红腰带,肩挂真皮酒囊——沿通道飞跑时,绊了一跤。跑在最前面的一头牛垂下头,又往边上猛地一甩。男孩砰地撞在栅栏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牛群紧紧相随着从他身边跑了过去。
观众一阵喧嚣。
所有人一齐冲入斗牛场内,我们走进一个包厢,恰好见到公牛奔进斗牛场,场上都是男人。他们惊恐地往斗牛场的周边窜逃。公牛还是紧紧地跑在一起,随同受训的小公牛,径直冲过斗牛场,奔进通往牲畜圈的入口。
那便是进场。潘普洛纳举行圣费尔明斗牛节期间,每天早晨六点,参加下午斗牛的公牛便被人放出牛棚,沿镇大街疾跑一英里半,直奔牲畜圈。跑在公牛前面的那些男人,为的是取乐。斗牛节每年举行,足有两百年的历史,那还是在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在格拉纳达附近的营地进行历史性会晤以前。
不测事件的避免发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斗牛在一起疾跑时,不受刺激,因而无凶悍之举;其二,利用小公牛,使斗牛始终跑不停蹄。
每当公牛撞倒一人,人群便高声欢叫。无非是当地人给勇士的喝彩。斗牛者越勇猛,或是他在斗牛撞来前,用披风作的躲闪动作越漂亮,观众便会大声叫喊。没人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用任何方式伤害或激恼公牛。凡有人抓住公牛尾巴,想紧握不放,观众便嘘声不断,向他喝倒彩。第二次他再这样,另一个人就把他击倒在斗牛场。公牛讨厌有人抓它的尾巴,观众亦同样不喜欢。
一旦公牛露出疲于冲撞的迹象,那两头聪敏的小公牛,一头棕色,一头极似霍斯坦牛,快步跑到公牛仔身旁。公牛像一条狗似的,跟在它们身后,温顺地绕场跑了一圈后,便出去了。
另一头公牛立刻进场,冲撞,用角挑甩,毫不起作用的舞动披风,伴以美妙的音乐,这一切又从头来一遍。但一次与一次不同。参加这次早晨业余斗牛赛的,有一些是小公牛。斗牛的价格一般都很昂贵,每头二千至三千美元不等。即便是品种优良的斗牛,若体格有什么不足,就永远达不了这么高的身价。但它们的斗志却是不减的。
斗牛表演是每天上午进行的。全镇的人五点半出家门,此时,数支军乐队通过一条条街道。许多人彻夜不睡。我们没有错过一场比赛。这是一项体育比赛,连续六个上午,我们五点半便起床。
大烟火升向高空。当我们在固定座席就座时,斗牛场差不多坐满了观众。太阳热辣辣地炙人。另一侧,我们能见到斗牛士们正作好入场的准备。他们穿的都是最破旧的衣服,因为斗牛场地泥泞不堪。我们用望远镜注视当日下午的三名掌剑手。只有一名是新的。奥尔莫斯,圆胖的脸蛋,看上去总是乐呵呵的,极似特里斯·斯皮克尔。其他两位是我们先前常见到的。马埃拉,皮肤浅黑,个子瘦削,长相极死板,却始终是最优秀的斗牛士之一。第三位是年轻的阿尔加贝诺,安达卢西亚人,身材细长,一张印度人的脸极是迷人。他父亲是个颇有名气的斗牛士。他们三人穿的衣服,太紧,早就过时,很土,或许是他们刚开始从事斗牛这一行时穿的。
接着是列队入场,演奏狂热的斗牛音乐,入场仪式很快结束。长矛手与马退至红色栅栏一边。掌礼官吹响号角,牛圈门开启。公牛急冲而出,见一人正站在栅栏附近,便猛撞前去。那人翻身过栅栏,公牛扑向栅栏。它猛冲直撞围栏,哗啦一声响,一块两英尺宽八英尺长的木板全成了碎片。公牛却因此而断了一角,观众要求重换一头公牛。受训的小公牛快跑进场,那公牛温顺地紧随它们身后,三头牛便又快步跑出斗牛场。
第二头公牛同是急冲入场的。由马埃拉负责,完美无缺的披风舞动表演过后,马埃拉便往牛身上扎短标枪。马埃拉是赫塞尔芙最喜爱的斗牛士。假如你想让自己在妻子心目中始终保持勇敢勤劳、稳健沉着、能力非凡这一形象,那么千万别带她去看斗牛赛。我曾参加过早晨的业余斗牛赛,想尝试一下,结果是,从她那里赢回了些许的敬重。然而,我发现,斗牛需要的是大量与众不同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在我身上几乎找不到一丁点。一个事实由此而愈发明显:较之她对马埃拉和维拉尔塔发自内心的倾慕,她对我可能重新产生的任何钦佩,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陪衬而已。你怎么也竞争不过斗牛行家。无论在什么地方。大多数丈夫若影响自己的妻子,惟一的途径是,首先,只有限量的斗牛士;其次,只有限量的妻子曾观看过斗牛比赛。
斗牛场的围墙四周,有一圈小台阶。马埃拉坐在台阶边缘,投扎头两柄短标枪。他对着公牛吼叫,公牛猛扑上来,他后仰身体,紧贴住围墙。就在公牛用角在他两侧撞击时,马埃拉纵身跃至牛头一侧,把两柄短标枪扎进公牛背部隆肉。他又用相同的方法,投扎了另两柄短标枪。他跟我们相距很近,我完全可以俯身碰到他。后来,他便准备置牛于死地。他手持小小的红色穆莱塔,作罢一系列完美无缺的躲闪动作。之后,他拔出剑,就在公牛猛冲上前的当儿,马埃拉握剑刺了过去。剑飞出他的手,公牛逮住了他。公牛用角挑起他托入空中,然后,他又跌落下来。年轻的阿尔加贝诺用披风罩住公牛的脸,公牛朝他猛冲过去。马埃拉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他的手腕扭伤了。
马埃拉扭了手腕,每次抬手瞄准刺剑,脸上总是汗珠直冒。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想一剑刺死公牛,但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手中跌落。他用左手从泥泞的斗牛场地上捡起剑,再把剑递至右手,刺了过去。最终,他成功了,公牛倒了下去。足有二十次,公牛差些撞倒他。马埃拉走到栅栏边,站在我们下面时,他的手腕肿得比原来粗了一倍。我想起自己曾见过职业拳击手因伤了手而退出赛场。
差不多没留下什么间歇。几头骡疾跑进场,套住第一头公牛,把它托出场。第二头公牛旋即冲进场来。长矛手手持长予,迎接它的首次冲击。随后便是公牛喷出一阵阵呼哧呼哧的鼻息,冲撞,扑击,仰头望弥撒,长矛手手持长矛抵挡公牛,作精彩的防守表演,接着,罗萨利奥·奥尔莫斯手持披风出场。
他握住披风,立即朝公牛扔过去,又来回舞弄,动作洒脱自如。然后,他重又舞动披风,作典范的引逗公牛表演。表演完,公牛便撞上了他。结束时,公牛没有停下,却是又冲了上去。公牛直接用角挑起奥尔莫斯,把他高高地抛到窗中。奥尔莫斯重重地跌落了下来,公牛完全控制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用角抵触他。奥尔莫斯躺在沙地上,头枕双臂,其中一个队友正拼命对着公牛的脸挥动披风。公牛抬起头,片刻后,便猛冲上去,把他逮住。又是用角挑起,抛向空中。过后,公牛转身,追逐就在它身后的一人,直至栅栏边。那人飞速奔跑,手搭上栅栏,正欲翻身过去,公牛追到,用角把他勾住,极利索地把他抛到人群里。公牛又冲向刚才被它抛入空中后跌落到地上的那人,他正想站起身,独自一人在那里。阿尔加贝诺抓住公牛的尾巴,他紧紧握住,我想,除非他或是公牛倒下,他是不会放手的。那名受伤的队友站了起来,躲到了一边去。
公牛猫一般转过身,冲向阿尔加贝诺。阿尔加贝诺手持披风,与它较量。一次,两次,三次,他站稳脚跟,后仰身体,缓慢地挥展披风,动作娴熟优雅,洒脱自如。公牛已是晕头转向。阿尔加贝诺控制住了局势。以往任何一场世界系列斗牛赛,从未有过这样精彩的一幕。
替补掌剑手是不允许的。马埃拉完了。几个星期之内,他的手腕是抬不起剑的。奥尔莫斯身被牛角抵伤得很厉害。公牛归阿尔加贝诺了。这一头和接下来的五头。
他全都制服了。获得了成功。舞弄披风的表演,优雅,洒脱,自信。穆莱塔(西班牙语,即斗牛时为吸引牛的注意而挂在棒上的红布)的挥舞,又是漂亮之举。极认真地把公牛置于死地。他宰杀了五头牛,一头接一头,不过,对付每一头公牛,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均以死了结。到了最后,那份优雅洒脱,在他身上,已荡然无存。放在面前的,只有一个疑问:他是否能支撑过去,或者公牛是否置他于死地。
“他实在是个很了不起的孩子,”赫塞尔芙说,“他才二十岁。”
“我们要是认识他就好了。”我说。
“也许将来有一天会的,”她说罢,便考虑了片刻,“到时,他很可能早被宠坏了呢。”
他们一年赚二万。
那只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此刻,在办公室办公,似乎是进了一个不同的世纪。早晨,从常年日晒的潘普洛纳镇——每天上午,男人们飞速跑在公牛前面,穿过一条条街道,坐小汽车上班,实在是一段很远的路程,但走水路在西班牙,只需十四天的时间。住一幢巨宅,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埃斯拉瓦街五号的那间房,一直是在的。一个人,如想以斗牛这一行重振家威,必须得及早加入到斗牛士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