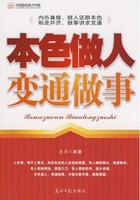二人相视而笑。马召娣(停了停)纪兰,说正经的,我问你,听说你回来马上要分地?申纪兰你听谁说的?马召娣甭管谁说的,有这事没有?申纪兰暂时还没定哩。马召娣没定就好。我们受苦受累创下的家业,就这样白白分给他们啦?申纪兰你说的谁们?马召娣我说的有的年轻人,平时不安心在村里好好劳动,提起分地,倒挺积极,还说什么要按人头平分,一分也不能少。凭啥?当年垒坝造地,他们扛过一块石头,挑过一担土?那阵,还没他们呢,凭啥跟我们平起平坐!申纪兰这些都有政策规定。马召娣我不管政策不政策,反正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闹平均主义!周占军召娣姐,你这,该不是得了红眼病吧!马召娣什么红眼病?我就得了红眼病又咋啦?对那些坐享其成的眼红不应该?
谁敢把地瞎胡分了,我跟他没完!(欲走)牛春旺火气还不小哩!
马召娣(又返回)咱可有话在先,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气冲冲离去)周占军这倒好,找上门来了!
张秋生老汉气冲冲走来,与马召娣撞了个满怀。张秋生(瞪了马召娣一眼)没长眼!马召娣你有眼?(双关地)有眼——看好你那牲口!(离去)张秋生(似懂非懂)有眼——看好我那牲口?!(好像感悟到什么,急忙进屋)纪兰,听说咱们村也要分地分牲口?申纪兰咋哩?张秋生我们盼你从省里回来,就为的给我们分地分牲口?申纪兰秋生叔,那是中央精神。张秋生咋?过去号召组织起来,就不是中央精神?申纪兰那是两吗事。张秋生我还不知道那是两码事?申纪兰(急了,越说越说不清)那是一回事!张秋生什么一回事!一会儿两码事,一会儿又一回事,别来回捉哄我老汉啦!申纪兰我是说,无论过去号召“组织起来”,还是现在提倡分田到户,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尽快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情况变了,形式不同了……张秋生不是情况变了,是你忘了本了!为了垒那拦洪坝,垫那河滩地,寒冬腊月,冒着风雪,大伙受的什么苦,遭的什么罪,累病了多少人,难道你都忘了?就这样,说分就分了,你就不心疼?
申纪兰秋生叔,我哪能忘了,哪能不心疼?
张秋生那为啥还分?我问你,当年要不是组织起来,一家一户,咱西沟能垒起这几里长的拦洪坝,垫成这上百亩的河滩地,种上这几千棵苹果树吗?这集体经济有啥不好……申纪兰秋生叔,你是多年的老劳模,老党员,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央精神,党的号召……张秋生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别的村咱不管,反正咱西沟不能分,谁要从我那里拉走一头牲口,我豁出老命跟他拼了!村委会秘书小赵匆匆赶来。
小赵纪兰婶,县里又来电话,问西沟的地几时能包下去,要再包不下去,县上要来咱西沟开现场会啦!
牛春旺他妈的,这不是存心出咱西沟的洋相吗?小赵他们还问:你还想不想当这劳模?你不当劳模,也不能拖了全县的后腿呀?
张秋生(一下蹦了起来,大声吼叫)太欺负人!当年砍合作社那功夫,不是也来了工作组,开了现场会,不都挨了毛主席的批评灰溜溜地走啦!来吧!让他们来吧!看最后谁斗过谁!
申纪兰(没好气地朝着小赵)你回他们话:就说承包的事,我们自己会安排。要来西沟开现场会,请便!(又更正)我们欢迎。至于个人当不当劳模,无所谓!
小赵应声欲走。
申纪兰(已稍冷静。又叫住)等等!(转念)算了,回头我跟他们说。小赵离去。哑巴怒气冲冲进屋,朝着申纪兰“哇哇”乱吼乱叫。
申纪兰哑巴哥,别急,有话慢慢说。哑巴依然乱吼乱叫比划。周占军(揣摸着问道)你是不是想问要不要分牛羊?哑巴连连点头。牛春旺(试探地)真要分了牛羊呢?哑巴听了,愣了一阵,突然朝申纪兰“哇”地大吼了一声,将收录机往桌上“啪”猛然一甩,嚎啕大哭狂奔而去。张秋生哑巴!哑巴!(喊着追出门去)周占军(感慨地)秋生叔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申纪兰大伙儿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这事看来还挺复杂的,是得慎重对待。什么时候承包?怎么个包法?村民们,特别这些老人们的思想工作怎么做,得考虑个稳妥的办法,别出了事儿。张秋生(返回。教训地)你们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呀!分了牲口分了地,这些人咋办?谁管?申纪兰我管。张秋生集体财产都分了,你管?管个屁!(气急败坏,指着申纪兰鼻子)败家子!
(又指着周占军)一伙败家子!
牛春旺(不满地)有理也不能骂人呀!张秋生骂人?(不屑地)你小子想挨骂还不够格哩!牛春旺(气极)你——倚老卖老!张秋生我——倚老卖老?!老又咋啦?我这老劳模是大伙选的!咱西沟这老先进(指桌上的奖匾)是大伙血汗换来的,毛主席亲手批的!(忽然发现牌匾上“组织起来”字样,双手捧起奖匾,嘴里不住嘟囔:“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突然神经质地吼叫起来)组织起来!完了,全完了!(“啪!”的一下奖牌匾猛摔于地)众人皆震惊。张秋生抱头痛苦地蹲在地上……申纪兰抱着破匾在暗暗流泪……周占军、牛春旺在一旁伤心,发愣……申纪兰秋生叔,你打我骂我都行,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摔这匾呀,这是咱村的心血,是毛主席奖给咱顺达哥,奖给咱西沟的荣誉呀!
张秋生(痛心疾首)“顺达,我对不住你,对不住西沟!对不住毛主席呀!我该死,我真该死呀!”挥拳痛打脑袋踉跄而下。
众人(急追下)“秋生叔!秋生叔!”急剧音乐声骤起。远处隐隐传来歌声,更加增添了人们烦燥不安的情绪。住惯的山坡不嫌陡,走惯的老路不担忧,吃惯了地瓜和子饭,安乐祥和度春秋。如今一切都在变,山在转来水在流;虽说前景似锦绣,山高林遮令人忧。
(三十九)夜色朦胧。西沟群山中处处苍松翠柏。申纪兰站在山坡上沉浸在植树造林往事的回忆中。
闪回。光秃秃的小花背石头山上。申纪兰领着十几个年轻姑娘在山坡上种树,有的用镢头刨坑,有的撒树种,有的用锨复土……“轰隆隆!”申纪兰随着巨石滚动声滑下陡坡……十几个姑娘一齐向倒地的申纪兰围去,有的问候,有的安慰,有的掏出手绢,有的解下头巾,七手八脚地为她包扎伤口……申纪兰抬抬脚,甩甩手,向众人示意平安无事:“没事,没事!大伙儿坐下休息一会儿吧!”众姑娘围着申纪兰坐下,有的拍肩,有的捶腰,有的揉胳膊捏腿……“哎哟,哎哟!”之声此起彼伏。
申纪兰见状,想调剂一下众人情绪:“我编了首山歌,唱给大家听听,看行不行?”众人齐声:“好啊!好久都没听你唱了,大伙儿正想的慌呐!”申纪兰轻声哼唱,众姑娘随着歌声渐渐振奋,并随声和唱起来。歌声字幕:
爬一道山来又一道岭,千年的荒坡上把树种。
山坡坡撒下松柏籽,汗水水浇出万年青。
满山青,绿葱葱,咱们妇女要立大功,立大功。
蓝天中一队人字雁行由南向北飞来。申纪兰指着雁行向姑娘们说:“等到她们飞回南方老家的时候,咱们种的树苗也就长出来了!”
(四十)数月以后。
姑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坐在自家的炕头,搬着指头相互算计着上山植树的时日……蓝天里,一队队人字雁行鸣叫着由北向南飞去……歌声伴唱:
行行大雁北来又南归,姐妹们屈指数来回,日夜盼满山树苗早吐翠,松柏成荫令人醉。
(四十一)村道上。
申纪兰正朝前走。雪花(从后边赶来)纪兰姐!等等!申纪兰(站住)啥事?风风火火的,看把你急的!雪花咱们在小花背辛辛苦苦种了三百亩树籽,一棵也没长出来!申纪兰(惊奇地)真的,三百亩树籽,一棵树苗也没长出来,谁说的?雪花满村人都这么说!众姑娘(也闻风而至)我们也都听说了!一姑娘发旺大叔也这么说。腊秀肯定是他造谣!他本来就对我嫂当社长有看法!申纪兰你亲耳听他说的?姑娘(想了想)好像他也是听旁人说的。
申纪兰不一定是他造谣。发旺大叔倔是倔,但不是个好挑三祸四的人。我看咱们还是亲自上山看看再说吧!众人对!上山!众人在申纪兰带领下一齐向小花背山上奔去。
小花背山顶。
申纪兰和姑娘们四处寻找树苗……雪花哎,咋就不见树苗呢?张腊秀(蹲下刨土)嫂,你来看,咱们撒的树籽都不在了,准是让鸟兽山害给刨吃了!
申纪兰也默默蹲下刨土……女青年甲纪兰姐,快来,这儿长出一棵!申纪兰在那儿?女青年甲在这荒草窝里。
众人上前围观。雪花绿油油的,真好看呀!女青年乙唉,可惜就这么一棵,要是再多几棵该多好呀!
申纪兰这儿能长出一棵,说不定其它地还有哩,大家再分头找找看。
众人四处寻找后,陆续返回。雪花纪兰姐,北坡没有。张腊秀嫂,东坡也没有。另一姑娘我们那边也找遍了,还是一棵也没有!
申纪兰泄气地“咳!”,跌坐在石坡上。众女青年议论纷纷:
姑娘甲爬山越岭,日晒雨淋,整整忙了一年,只活了一棵,咱们再也不干这傻事了!姑娘乙男人们早就说了,小花背山上要能长树,老一辈早种上了,还用你们!姑娘丙这下可让男人们看笑话了!女青年甲我说石头山上不长树,你们偏不听,要不是你们动员,谁上山来受这份洋罪,听这份闲话!女青年乙反正现在后悔也晚了!申纪兰这事不能怪大家,是我领的头,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腊秀不能全怪我嫂。当初上山植树,虽说也动员了,可最后还是大伙儿点了头,自愿参加的。
召娣(生气地大吼一声)都别说了!(伤心地)纪兰为替咱们争取同工同酬,里里外外受了多少气?为了植树造林,她受的苦不比谁多?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她为了谁?为了大伙儿!你们说这些话,也不嫌脸红!你们的良心都到那儿去了!说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女青年甲(内疚万分)纪兰姐,都是我们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我对不起你,你批评我,骂我吧!说着抽泣起来。
申纪兰小妹,别难过,别哭!(边安慰边自己也哭了起来。)众人(一起安慰)“纪兰姐,纪兰组!”似有传染病似的,女青年们你抱着我,我搂着你,霎时哭成一团。
申纪兰别哭,别哭,大家都别哭!“哈哈哈”(画外)远处传来李顺达洪亮的笑声……画外音(李顺达大声地):“活了一棵,好啊!好啊!”李顺达走来,见状:“哎,你们这是哭的哪门儿的丧呀?”
雪花“社长,我们栽了三百亩树种,才长出一棵苗!”李顺达(欣喜地)“噢,长出一棵,在哪儿?快领我看看!”一女青年(指着)“那不是!”
李顺达上前颇有兴趣地蹲下仔细观看。李顺达嗬,小家伙长得又粗又壮,还蛮精神的哩!申纪兰顺达哥,我的工作没做好,请社里处分我吧!
李顺达(站起)唔,刚才你们就是为这一棵树苗,哭的鼻子是不是?
一女青年社长,你就甭取笑我们了,不该哭,难道该笑不成?
李顺达对。你们不但应该笑,而且应该唱,应该跳才是啊!
雪花社长,你甭给我们宽心了。就只当在家歇了半年,我们不要社里的工分就是了。
李顺达唔,那是为甚?依我看,社里不但应该给你们按劳计酬,还应该再给你们每人记上一功哩!
众人社长,别说笑话了!
李顺达我可不是说笑话。你们还记得不?当初你们妇女队上山的时候,人们都说些甚来着?
雪花那还能记不得?有人说,要是山上能种树,咱们的祖祖辈辈先人都傻了,还能搁到现在?
张腊秀还有人说,叫她们妇女去瞎折腾吧,要是能在石板山上种活一棵树,他就圪脑朝下,脚朝上倒着走!众人发出压抑的笑声,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李顺达(也笑了)这不就对了。眼下,虽说只长出一棵树苗,和你们付出的艰苦劳动相比,的确是少了点。但是,它实实在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西沟山上能长树。有一棵,就不愁有一坡;有一棵,就不愁有一百棵,一千棵,一万棵,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申纪兰顺达哥说的对,有一棵就不愁一坡,咱们接着干!
众姑娘对,接着干!
申纪兰还要大干!
众人对,还要大干!
李顺达好,我支持你们。不过,你们也不能光顾蛮干呀,要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赶明儿我到市农校去请几位教师,来给你们进行现场指导。
众人(欢呼雀跃)那太好啦,我们接着干!歌声中众姑娘植树起舞。歌声(字幕):秃岭荒山一座座,姐妹们上山把树种播;日晒雨淋志不移,风儿歌儿相伴和;大雁南来北往岁月过,一棵树引来绿满坡;东山松柏西山果,绿色银行金银窝;功夫不负有心人,社会主义幸福多。
大雁成行一回回南来北往。荒山秃岭一年年绿树添荫。
(四十二)闪出。
申纪兰来到饲养场外,木桩上挂着一盏马灯,引起了她一段趣事的追忆。
闪回。西沟村道上。申纪兰、老农赵相奇迎面相遇。
申纪兰相奇叔,我正找你。最近跟顺达哥商量,咱村是农林牧合作社,不能光有一群小毛驴,连头大牲口也没有。你对牲口最内行,想让你趁今天龙镇庙会,赶上几头毛驴卖了,买回两头小母牛,慢慢繁殖,行不”
赵相奇行。你现在是副社长,你说了算,还有哪个社干部一块去?
申纪兰我。
赵相奇你?
申纪兰咋?不行?
赵相奇(不好意思)这是男人们做的生意,要袖格筒里捏指头悄悄定价,你一个妇女家……申纪兰(笑了)咱又不封建,和那些经纪人碰碰手指头有啥关系?赵相奇摸手定价你会?申纪兰不会咱不会学?赵相奇(也笑了)行吧。那,咱就边走边学。申纪兰大叔,你说大伙为啥都把牲口贩子叫“牙行”?赵相奇牲口贩子挑牲口,全凭看牙口。申纪兰啥叫“牙口”赵相奇就是牲口嘴里长的牙。申纪兰那咋看?赵相奇牲口牙口没长齐的,说明牲口还小,正长个儿,骨架小点不碍事;牙口齐全的,牲口长成了,正是使唤的时候,多出点钱,值!牙口不全的,老了,眼下看着壮实,使唤不了几年就得送屠宰场。牲口贩子功夫深浅,全在看牙口上,所以,大伙都叫他们“牙行”。
申纪兰这里边道道还不少。(玩笑地)这回,我也当一回女“牙行”。大叔,天不早了,咱们走吧。二人边说边走。
龙镇庙会。牲口市场。
传来阵阵毛驴鸣叫声。经纪人(过来掰开毛驴的嘴看了看牙口)来,摸个价怎样?赵相奇好啊!经纪人(装作漫不经心的神气)是社里的,还是自个儿的?赵相奇社里的?经纪人(看看赵相奇和申纪兰)谁是掌柜的?我和你们掌柜的讲价。赵相奇(指指身旁的申纪兰)她。经纪人(瞪着多疑的眼睛,斜视申纪兰一眼,不屑的语气脱口而出)她?一个女人,她懂牲口行?申纪兰(大方地)大叔,你先和这位老叔摸摸价,拿不准的咱再商量。赵相奇行。经纪人(自言自语)看不出,这女人还挺有派儿!
赵相奇走过去,经纪人把手掩藏在衣襟里,两个人摸起价来。
经纪人这价怎样?
赵相奇不行。
经纪人这个价总可以了吧?
赵相奇差远着哩。
经纪人(装作有点不耐烦,把手抽出来)你做不了主,还是你们掌柜的来定个价吧!
申纪兰行啊。
经纪人(朝申纪兰)那你就说个价吧!
申纪兰咱还是按老规矩办事!(说着从头上取下毛巾,走了过去,大大方方把手放在毛巾下面)经纪人(被申纪兰的气势吓住了,慌乱地)啊!啊!
申纪兰(走到经纪人跟前,邀他摸价)来呀!
经纪人好,好!(只顾答应,却不往毛巾下面伸手)申纪兰(玩笑地)哈!还封建呐,没进过城还没看过电影?人家外边人,无论男女,见面先握手,年轻人搞对象还当众亲嘴哩!
经纪人(假装正经地)我是怕你……申纪兰我咋啦,我又不封建,又不是没出嫁的小姑娘挨不得,来吧!(主动伸出手去)经纪人(尴尬地)行!行!两人在毛巾下面掐指头议价。
经纪人这个数?
申纪兰(笑了笑)差得远哩!
经纪人这个咋样?
申纪兰不行!
经纪人这个总可以了吧!
申纪兰(不由笑了)我说老叔,别捉弄我了,你别乱压价,不给这个数不卖!
经纪人太高了吧!
申纪兰不高,一点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