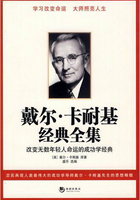老太说完,大家都静着,等村长说话。村长咳了一声,慢慢抬起眼睛,说道,真是对不起首长和领导,事情兴许有些误会了。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先瞪村长,又转过去瞪王副乡长、老杨和小韩。那三个通红了脸,不约而同要张嘴说话,却被樊老头的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示意人们继续听村长说。村长说,昨天夜晚,听说首长要来,就特地把夏家窑七十岁上的老人会齐来问情况,老人们有的说记不清了,有的倒还记得,说孙来家草窝里的小女兵其实不是兵,是不晓得哪个地界上的砍柴的女子,失了脚,掉了崖,挂在树枝上,才留住一条命,然后顺着古时的挑炭的旧道,爬到了夏家窑来了;因为正是胡宗南进兵的当口,人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传了;还有,那小女子头几天还能说话,见大爷叫大爷,见大娘叫大娘,好像是山西那边的口音,这就对不上了;因为是烈士的事,政府的事,不能有半点差错的,要不咱们也对不起烈士李书玉啊!老头的脸板着,十分僵硬,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村长发现,至此,老头还只字未语。老太显然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向陪同前来的副县长发难了,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老樊知道找到了李书玉同志的下落,激动得几夜没睡,血压都高了。副县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只能对老杨和小韩责问,老杨小韩再向王副乡长责问,最后是王副乡长望着村长,虽然一言不发,可那眼睛是把村长十八代祖宗都骂到了。村长不接他的茬,把眼睛挪开,看外头。外头地上站着乡亲,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村长将人头看了一遍,没看到孙惠和他家的。
老太又说,老樊也知道你们搞了迷信,结什么阴亲,但老樊并不计较,农民嘛,是需要长期教育的,老樊只是想把李书玉同志的遗骨,送进烈士陵园安葬,也了了几十年的心愿,对后代也是教育,真不知道你们基层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村长心里静得很,老太说什么他并没听进去,只是看着她的嘴,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词这样不间断地从这嘴里吐出来,就像炒锅崩豆子似的。忽然间,那老头又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老太戛然而止。老头站起身,说道,看看那女子的地方吧。他声不高,言语也不多,可村长却震了一下,他不由跟着站起身来。他又在老头那双垂着囊肉的小眼里,看见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就是这些熟悉的东西,透着一种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了解,厉害着呢!村长又有些不安了。他乖乖地引着人们走出村委会,门前的人群默默地让出一条道来,看他们走过去。
村长带着他们沿了沟坎走,阳光从屋檐上漏下来,一条条的,照着半张脸,都沉默着。离他们一段距离,是夏家窑的乡亲们。屋檐后边是光光的山崖,崖顶是雪亮的太阳,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崖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人们来到了孙来家院子,孙来和他媳妇还有他爹妈,站在院子里,比画给来人看当年那一堆草垛的地点,又比画给来人看,当年的院子是如何,现今改掉了哪些。南墙朝外推了几步,山墙也撑了出去,所以地形就有些两样了。一边说,一边往四处撵鸡,不让它们到中间那块地面来,鸡就喳喳着。人们围了院中间的空地一圈,想象是当年窝小女兵的草堆的地方。老头沉着脸,听孙来他爹说话,说那小女兵在草堆里度过的七天七夜。孙来也是听他娘说的,他是小女兵来到后的第二年生人。村长蹲在人圈外头,不再说话。孙来爹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处传来,漏出好些破绽,他口口声声称她为“小女兵”。老头并没有置疑,村长也不去纠正。他知道没什么能哄住这老头的,他钝钝的,却看得清底细。这老头身上有一种东西,确实打中了他,这也是钝钝的,是钝钝的悲哀。
然后,队伍就由老头带领了。他领头出了孙来家院子,村长不由得随在身后,向村口坟地走去。老头将手背在身后,抬起头四下里打量。看门里的院子,圈里的猪,场地上晒的粮食。有小孩子挤了他的腿,他还摸摸小孩子的头。老头的脸色松开了些,不像方才绷得那么紧了。那种钝钝的东西,似乎变得柔软了,可以流动的了。近午的阳光照着他花白的头顶,村长想,多少日月过去了啊!从这老头的头顶上过去,也从夏家窑过去,可是小女兵还是小女兵。他们来到了高岗上的坟地,站在孙喜喜和凤凤的合坟前头。清明添的土还湿润着,坟头的土坨坨也是新的,土坨坨下压着一张粉红纸,炫目得很。老头对着坟站了一会儿,转过身,看一眼身后围着的乡亲,低下头从兜里摸出一个小钱夹,夹子里摸出张相片,递给人群中一个老汉,说道,您老看着,是这个女子吗?
老汉拿了相片看了半晌,没吭声,传给了另一个比他还老的老老汉。老老汉看了一会儿,也没吭声,再传给一个老婆儿。老婆儿又传给老汉。相片在人群里传了一遭,最后传到了村长手里。这是一张比手指盖略大一点的旧相片,泛黄了,却还是清晰的。照的是半身正面,学生头,齐额的刘海儿,旧式便褂的竖领,嘴抿着,不笑,眼是黑漆漆的。从未谋面的小女兵一下子跳到了眼前,村长觉得已经认识了她几十年似的。几十年,他在娘肚子里从无到有,再从光腚猴长成这么个半老汉,可小女兵却一直是这副面容。就和相片上一样,不笑,不吭声,眼睛黑漆漆的。这个受了伤的小雀儿啊!村长眼睛湿了。他将相片还到老头手里,见几个老婆老汉都在擦泪。停了停,村长使劲将喉咙里哽着的一块东西咽下去,哑着声说,这多年来,夏家窑把她当自家闺女看。老头也哑着声说,她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老头说过后,就看着地面,一动不动了。这时,村长知道,他到底是输给了这老头,他到底是犟不过这老头的。
这天晚上,村长迈过了孙惠家的门槛。他晓得,今晚他要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一宿不得安泰。他要一直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就一直不得安泰。老两口子见他来,立刻明白了,掉起了眼泪。孙惠家的一把一把地擦泪,眼睛擦得通红,都烂了,那是叫眼泪腌的。哭了一会儿,孙惠家的便起身要去烧茶,被村长拦下了。村长说,这几天,早想来同你老说,可是一直没得闲工夫,说实话,也怕你老哭,就挨着,可不说呢,又老堵在心里,是块病。孙惠就说,村长,大家都知道你也不好办。村长拦住他的话,等等,你老先听我说;有半个月了,还是清明前,我就做了个梦,现在想来,是喜喜那媳妇托给我的;她对我说什么呢?她说,她和喜喜小日子过得不错,和和美美的,可是不期然的,玉皇大帝点了她去投胎;你老知道,她上一世没活够人呢,吃苦比享乐多,尤其是最后那七天七夜,真是煎熬啊,她想活人呢!我就说,那就去呗,你先去,二年把喜喜拉扯去,再做夫妻。她就说,大叔啊,你不知道,夏家窑太背了,挤在山折折里,路又不好走,还没有水,玉皇大帝的船撑不进来接我呢!她说,大叔,你能不能送我出去呢?梦做到此就断了,开始我倒并没有上心,不就是个梦?可是过了一段,这不,来了个首长,专为了认这女子,要把她带到省城的烈士陵园。我心里就不由一惊,这不是应了那日的梦了?是玉皇大帝托人来引路了不成?
第二日,村长就专派人到乡里,给王副乡长捎了信。说是一切都妥帖了,三天后可来人领遗骨,事情由他来操办,请领导和首长放心。
这一天,吉普车先后三辆连成一队,开来了夏家窑。近村口时,就看见高岗上许多人忙碌着,有白烟腾起,被风吹开,夹着些焦黑的纸屑。有指令从最后一辆车传到了第一辆,吉普车停了,停在距村口二百米的地方。没有人下车,就这么等着。高岗上坟地里的人们没注意到吉普车,兀自干着。他们由村长带领,在孙喜喜和他媳妇的坟头四角烧了四堆纸,一边烧,一边念叨,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走了,感谢这三年的处处照应,和睦相处,我走了,撇下喜喜和孩子,还请多多相帮。念罢,便开始起坟。铁锨试探着插进土里,辨别着方向,然后才下力一掘。再烧纸,这回是烧给喜喜的,说着劝慰宽心的话,还有大丈夫要自立自强的话,烟裹着烧不尽的焦纸,飞扬着,就像一群黑蝴蝶。经这几番折腾,几十年前的薄板子早已散了,村长将遗骨拾在一口坛子里,又在喜喜的棺木跟前抓了几把土。等他直起身,便看见了村口路上的吉普车。他将坛子捧在手里,想这坛子只装了这些遗骨和土,怎么就突然变沉了。他小声地说了句,凤凤,这就送你出山呢。他下了岗子,走上路。最后一辆吉普车里走下一个人,是那樊老头,手里拿一块红布,等他走过去,便用红布蒙在了坛子上,然后接过了坛子。车上的人纷纷下来了,没有那老太,村长心里感到少许的安慰。而就在这老头接过坛子的那一刻,村长觉得小女兵突然间变老了,也变得像樊老头那样的年纪,头发花白,垂着大眼囊。几十年的日月一下子走了过来,闪忽之间,没有了。
老头上了车,随行的人,王副乡长、老杨、小韩,都纷纷上了车。然后,车就开走了。村长站在路上,望着车沿了山路,慢慢远去。在他身后,人们继续干着活,将孙喜喜的坟重新垒圆,垒高,四周添了新土,又烧了一圈纸。石碑上,凤凤的名字油了红漆,表示人在阳间,留着个寿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