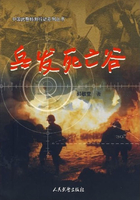伟人毛泽东常有不同凡俗之识见,为曹操翻案是其中之一。因而有郭沫若闻风而动,创作《蔡文姬》积极响应。郭老一向随风转舵或有苦衷不遑多论,他的《蔡文姬》单从选材来讲也未见高明。匈奴左贤王掳掠大文豪蔡邕之女而去,沦落异邦的蔡文姬诉其悲苦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传入中土,曹操怜其处境向左贤王索而救之。这实在是太小的一点好人好事,何足用来鼓吹歌颂曹操?除去戏剧化的考虑,若是要我举例说明曹操办过好事,那我则会选取他政令天下戒除寒食陋习的事迹。
晋文公火焚绵山烧死功臣介子推,因而特设了县治“介休”,因而自此还有了一个介子推的忌日不许天下百姓举火的“寒食”节。寒食节在农历清明节前两日,老百姓后来就将两个节混为一谈。现时山乡野里还把清明叫做“寒节”。因政令而渐成风俗,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晋文公烧死他的功臣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为消除心中愧疚而搞得举国人民不能举火烧炕,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更加霸道无理。但百姓无权无势,只好恭恭敬敬认认真真当一个盛大节日来过。不许举火,如何烧饭?大家唯有提前预备若干熟食,于节前蒸许多面点花样。这习俗至今在我国北方仍大为流行,花样繁多的面点还作为民俗文化的特别节目上过电视呢!而从春秋到三国,荏苒千载,这一所谓“民俗”曾发展到极其荒唐的地步:竟是在一个月之内不许举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死人而让成千上万的人民大受苦寒,是何道理?但习惯如此,风俗如此,传统如此,弊政陋习,愈演愈烈,陈陈相因,欲罢不能。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予更改革除呢?有权者,念不及此;有心者,力不至此。乃有曹公孟德,在其位而谋其政,忧天下之所忧,念北地苦寒,妇幼老弱多所不堪,断然下令戒除恶俗,减寒食一月而为三日。一道命令,救拔苍生无数。如此功德,无数获救苍生的子孙后裔们却随波逐流诅咒“白脸曹操”千载以下不绝于口。真令人不禁悲从中来!
若说曹操文采,“东临碣石有遗篇”,和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共创“三曹”
大名,煌然巨着彪炳千秋。似乎直到宋朝才有“三苏”出世,堪可比附。作为文学家,曹操还只是玩儿了一点业余爱好。他的专业之一应是打仗。评价他的军事才能,便是孔明周郎之辈尽管有赤壁大胜,也不能不由衷钦服。伟大的军事学着作《孙子兵法》得以流传当代,也须归功于孟德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天才予以增修疏注。文才武略,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人可与比肩!更何况文学家军事家之外,曹操更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外交家和策略家,革新家和冒险家。“绝代风流”,应非过誉。
当然,历史上的曹操和世俗文化中艺术化甚至脸谱化了的曹操已非同一个人。《三国演义》和三国故事以及三国戏剧的极大流行普及使得两个曹操水乳交融,难以廓清。甚至脸谱化的“白脸曹操”已全然湮没了真实的曹操。由此,我们又不能不慨叹文学艺术的功能之巨大、之深刻、之可赞、之可怕!
历史发展到今天,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受到一代具备了全新观念的今人的审视和反省。而大赞清官包公之类的旧戏新戏仍在锣鼓喧天粉墨登场,有新编历史剧《曹操和杨修》也在凑热闹。只会耍点子小聪明的杨修,出现在现代音响化灯光布景化的舞台上,来做大英雄曹操的对抗角色,实在不成比例。组织了评论家来大肆吹擂,首长接见、献花颁奖什么的,更教人哭笑不得。不说这些了吧。
写作本篇短文的中午,我告诉女儿说正在开写《今古奇谈》之二,是讲曹操好话的。当时正读高中二年级的女儿反诘道:曹操本来就是超级大英雄,你说他好,还算什么“今古奇谈”?
于是,这个中午成为一个乐观的中午。
和番哪怕不昭君
昭君出塞故事,以戏剧形式广为传播,是在元明杂剧传奇时代才可能开始的。骚人文士辞章咏叹这一题材,则要早得多,而且几乎从来没有被冷落过。从诗圣杜甫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皆有佳作流传。特别是在昭君出塞两千年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艺界隆重推出大型史剧《王昭君》,将王嫱女士描写成主动和亲、促进民族团结的明晓大义的奇女子,则更可称作空前之盛事。什么“一个伟大的剧作家”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之类,肉麻吹捧、放肆阿谀,烈火烹油、繁花着锦,鼓噪欢呼、甚嚣尘上。昭君有灵,怕是要幸福得从墓穴内歌舞而出,怀抱琵琶弹奏一支普天同庆的“欢乐颂”呢!
古为今用,何尝不好。但这个“用”不应当堕落为实用主义之“用”。传统戏《铡美案》,借青天大老爷之手铡掉驸马爷的脑袋,本来也就解恨得很了。但戏剧改革家心血来潮,觉得需要借助官府才能获救雪冤,我们被压迫的妇女地位仍很可悲。因而便有新戏《秦香莲挂帅》出台上演,胡编乱造了秦香莲立军功、挂帅印的情节,然后让当了大官掌握了刀把子的秦女士亲自来审判处决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如此,妇女自我解放,主题多么进步!亲自手刃仇雠,心情何等痛快!然而,如此的戏剧改革,破掉的也许算不得金城汤池,立起的却绝不是玉柱华表。那只是浅薄的激进和无聊的胡闹,甚至是低级的卖弄和愚蠢的迎合。
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属于中原汉族政权怀柔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和亲”,后来的传奇剧目名曰《和戎记》。和亲也罢,和戎也罢,事件本身或者果然有政权间达成和议、暂时消弭边境战祸的功用。当事者王嫱却无疑做了这项政策的可怜的牺牲品。对她个人而言,实在是大悲剧中最悲惨的一幕里最令人酸楚的角色。
将她描写为乐颠颠而傻呵呵心甘情愿去和亲,其觉悟性开放性比如今在各国大使馆门前卖色相而当黄牛的超级新潮女性还高,王昭君还像是两千年前的汉家女子、还像是锁禁深宫中的帝王嫔妃吗?
汉元帝,堪堪是在一代雄主汉武帝之后。汉武在位,遣大将卫青霍去病驱匈奴于大漠之北七百余里,数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匈奴民族水草不得逐、六畜不繁息、妇女无颜色,一何可悲!匈奴人就不是人吗?就应该赶尽杀绝吗?就无权以战斗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吗?而“六月债,还得快”,匈奴人终于从血泊中爬起,铁骑潮涌势不可挡,逼迫堂堂汉家天子不得不屈辱“和亲”。选送后宫佳丽,以媚强寇;天朝大国,蒙羞至此。匈奴人的大喜事,便也正是汉朝人的大悲剧。
和亲,实出无奈尔。
无奈之中最是无奈、不幸之中尤为不幸者,是汉元帝后宫嫔妃何止千百,偏偏选中了王昭君去和亲。昭君王嫱,忝列皇上后宫,数年里竟无缘得睹天颜,已够可悲。那皇帝若不荒淫,何必设后宫三千;若是荒淫,偏又不曾遍洒甘霖。到和番之议已成,元帝皇上这名义上的丈夫才第一次见到属于他的女人。皇帝龙颜天面,王嫱闭月羞花,四目相视,情何以堪!史料或许有些许真实点滴,传奇则对此大加铺陈演义。说那宫廷画师毛延寿着实可恶,由于王嫱自视甚高,不肯像别人一样请客送礼,毛贼竟是将一个沉鱼落雁的美女成心画丑了。因而,皇上览画之后不曾中意,未能降幸于她;因而才着她去和番,似乎拿了一个残次品去糊弄洋毛子。以变法而知名的王安石惯做翻案文章,曾有诗曰:“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是啊,女人之美岂止是五官轮廓而已,而神情意态风韵婀娜摇曳绰约之美是画不出的。后世读诗评诗者因而津津乐道,赞扬王荆公之识见。
然而,我却要问:假如王昭君真个不那么美呢?假如她真个很美而汉元帝另选一位刘昭君李昭君去和番呢?那终被选中而被迫远涉大漠去陪洋毛子睡觉的不太美的女人们就格外幸福了吗?这样的和番对民族就不是屈辱、对作为牺牲品的女人就不是悲剧了吗?中国一干鸟男人什么时候把女人当过人!一个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倒被他们把玩咏叹了两千年,多么同情妇女、多么保障女性权益似的,叫人好不恶心!
中国历史上战争之多,怕是罄竹难书。杀将出去倒还罢了,被杀进来总不是愉快事。而大凡国势倾颓,衰弱至极,文臣爱钱、武将怕死,长城不能保国、大军望风披靡。此刻,惯于打骂老婆欺压妇女的凶霸蛮横的男人们干什么去了?老幼遭杀戮、妇女被奸淫,男子汉们何辞其咎?反而要苛责女子不能自尽全节,诅咒唾骂妇女不贞不烈;或有女子不堪受辱果然跳井上吊,做了败军之将阶下囚亡国奴的七尺须眉们则又大树贞节牌坊,书之竹帛,旌表天下。这时,女人死了最好,总算没有被外人占用,满足了一种极其阴暗卑的占有心理。试问还有比这更其无耻的吗?昭君出塞一例,偏偏又不是敌国掳掠而去,倒是自家皇上把老婆洗刷得白白净净,打扮得鲜鲜亮亮,笑容可掬、开门揖盗、温良恭俭、让不胜犬马悸怖之情、诚惶诚恐敬献强敌。打敌人,打不赢;骂女人,没借口。假高兴,笑不出;装糊涂,心里痛。这是一种典型的受了伤害的“乌龟”心态。这样一种微妙复杂卑可耻的心态,实在是两千余载难以忘怀、代代文人描摹不尽的啊!
历史上确有实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加以创编大演特演的另一折戏《文成公主》,正好能与《王昭君》做个对照。文成本非公主,因和亲而敕赐封号,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同样是和亲,同样是美女远嫁番邦,文人学者因何便没有那种言说不清的晦涩心理呢?这个女人就不是我们华夏女儿吗?说来却是简单不过:大唐李世民时代,中华大帝国好不强盛,文成公主不过是我们赏赐那番邦王子的一点恩宠。是下赐而非上缴,是主动支援发扬国际主义而不是签订城下之盟被迫割地赔款。于是,欣欣然而陶陶然,美滋滋而笑嘻嘻。然而我则不禁又要发问:拿女人作礼品送人,无论姿态多么居高临下,外交方略多么巧妙成功,那女人就不悲哀吗?
前几年乃至近几年,在所谓的新时期,“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
的呐喊声中,常见一些小说电影以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来结构谋篇、设立矛盾,其解决矛盾的高明招术往往是两个男人你推我让、五讲四美三热爱,简直就是整一个君子国,不争不抢,互谅互让,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人格多么崇高、精神多么伟大、风格多么高尚、灵魂多么圣洁!那么,这个女人本身的意志呢?像一件物品似的把她推来让去,将这一个女性当成什么东西了?这样的貌似崇高,实质多么卑劣!如此的拔高境界,恰恰暴露了境界的低俗。这样的当代君子们,见他娘的鬼去!多篇多部这样的作品出版播映,甚至纷纷获奖,却不见谁来横加干预定其名曰“精神污染”,国人从上到下的文明水准叫人说什么好!
历史上的苦女子王嫱却到底是自杀了。与其冷落后宫枉自白了少年头,嫁一个体肤相接的实实在在的男人也罢。远涉瀚海,吞腥食膻,语言不通,气候不适,终究生男育女,位举王妃福晋之类,也算苦中作乐,终可以在蕃邦立脚。然而匈奴制度风俗,老王故去,新主登位,却是要连母后皇娘一并继承。昭君曾与儿子商量,问其遵照汉制还是依循匈奴习俗?儿子匈奴称王断然答复不能改制。
作为母亲的王昭君到底不能放弃汉家女儿最后的文化与心理的防卫屏障,同样是断然的选择,她选择了死亡。呜呼哀哉!人固有一死,被迫牺牲自己而换取了民族间数十年和平的华夏女儿王嫱最终是这样的一种结局下场。凡有人心,能不为之哀伤。悲哉痛哉,夫复何言。硬要把惨绝古今的一个女人写成欣欣然、美滋滋、兴冲冲、乐颠颠,放肆糟蹋恣意污辱这样一位女性,实在猜不透编剧人和鼓吹者出于什么心术。不是有成语曰“人心叵测”吗?
历史大书翻到宋朝以降,成熟的中央封建大帝国开始烂熟而朽败。异族入侵彻底占领易服改制始有元朝继有清朝。我们不能因奉行民族多元论而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这种入侵的残酷性与非正义。一个民族臣服于另一民族,绝不是“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高歌。强权,并不就是公理。曾经发生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假如没有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建成了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我们能够承认这样的民族融合吗?
近代以来,红毛国而不列颠,鬼子而毛子,欺侮侵略我中华变本加厉,殖民瓜分肆无忌惮。始有孙中山先生割划时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了数百年来之异族统治,同时倡导三民主义实行共和,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丰功伟业,横扫千古。复有壮烈的抗日战争,我中华焦土抗战加入同盟终于打败狂妄的日本帝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未尝有此大胜!日帝战败,前有波茨旦公告、后有日内瓦公约,赔偿战争损失无可逃绾。战争赔款之计定,是以人民财产鲜血性命换得。赔且不足以抚人心民意,何况不赔。毛泽东一代伟人,认为日本侵华牵制了蒋介石救助了陕北红军,可谓坦率;出于重新交好不索赔款,可见气度。而在韩国朝鲜追查“慰安妇”事实,向日本政府逼索赔偿之后,中国也有志士仁人首倡发起民间索赔之签名请愿运动。杀我人民,辱我妇女,小鬼子焉能不赔!此事结局远未明朗,但中国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不在甘心受辱、不再以德报怨之崭新面孔已傲然展现于全球。
为现今中日邦交友好,突出宣传鉴真东渡之类,以及为了现今的民族团结,新编上演史剧《王昭君》之类,是闻风而动的遵命文学,是实际操作的“古为今用”。从积极意义来理解,也不妨美其名曰:参与意识。为百年屈辱,为“九·一八事变”,为“南京大屠杀”,民间自发掀起索赔运动,无疑更是一种参与。相形之下,我在这儿喋喋不休数千言翻捡故纸堆中一页,可算乏味。
所自信者,在千部一腔的大合唱中敢发一两声不和谐的怪叫,志在身体力行倡导某种程度的说话自由,则也可说是一种参与。借题发挥,以古论今,也不妨说是古为今用。而关于“昭君出塞”的一套说法,或许言之成理,或许可算一家之言。
歌舞帐下犹美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无疑是人类史上开天辟地的壮举。欧洲勃兴的资本主义向海外大肆扩张,盖由此发轫。在欧洲而言,这是朝气蓬勃的开拓,这是活力旺盛的冒险,这是节日的庆典,这是胜利的凯旋。在美洲、澳洲而言,这却是亘古未有的灾难,这却是种族灭绝的末日,是死亡的恐怖,是臣服的屈辱。角度不同,功过利害之评判也必然悖谬。没有欧洲文明的拓展,能有今日美洲、澳洲的繁荣吗?若不是欧洲殖民者的血腥屠杀和野蛮占领,印第安和毛利土着安知不是在他们既成的传统生活中其乐融融呢?部落吞并,民族倾轧,自古以来多半遵循了优胜劣汰的规律。规律之下,道德评判便显得苍白而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