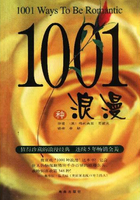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郑伯奇在《鲁迅先生的演讲》里也说道:鲁迅的演讲,“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哄堂的笑声。”许广平也曾经谈到她们在女师大听鲁迅讲课时的一个细节。
她说,有一天,新的讲义还没有发下来,同学们就想和先生“闹一闹”。
于是就有人说,树枝吐芽啦;外面的空气好啊;书听不下去了;要去参观!
鲁迅在弄清是全体都要去的情况下,就带他们去了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鲁迅的课本来是讲得很好的,他的演讲常常人满为患。
同学们不想听课虽然也有没有讲义的原因,但绝不是因为鲁迅讲得不好。更多的成分,我以为还是由于鲁迅可亲可近。这一点,从学生们与鲁迅的“闹”中也可以感到。
许广平还曾谈到,鲁迅常爱买些小玩具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一天被他的学生们发现了,大家竟一抢而光,还有人因为没有抢到几乎要哭起来。
鲁迅在搬出八道湾后,曾在砖塔胡同借住。与当时还年幼的俞芳姐妹住在一个院子里。俞芳回忆说,那时她们在太师母房里,最感兴趣的是听大先生讲故事。比如鲁迅曾给她们讲过绍兴人怎么读书,怎么吵架,等等。有时鲁迅竟连说带比划,笑得大家前仰后合。
那时,俞芳姐妹最感兴趣的另一件事就是敲大先生的“竹杠”,要鲁迅为她们买街上卖的零食。“事情总是大姐带头,我和三妹帮腔……遇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他是同意的。为什么他不拒绝呢?原因之一是他的好心肠,他看着我们‘垂涎三尺’的顽皮样子,就同意了。”
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曾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其实,这只是说了鲁迅性格中的一面。
关于鲁迅的温情,鲁迅的幽默,鲁迅的风趣和善良、软弱他还没有谈到。事实上,许多人觉得鲁迅不好接近,仅仅是凭了一时的印象。一旦和鲁迅有了来往,而且又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鲁迅其实是一位最为慈祥的长者和一位最为真诚的朋友。比如冯雪峰在没有与鲁迅来往前,感到鲁迅是一个非常矛盾,冷得可怕的人,觉得他“藐视一切,对一切人都有疑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我主观上所以这样地理解鲁迅先生的性格,除了根据片面的印象之外,也还由于读了他陆续发表的散文诗(就是后来收到《野草》中的)的缘故”。然而,一旦他们有了来往,冯雪峰的印象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一九二八年底,柔石把冯带到了鲁迅的家后,冯雪峰便与鲁迅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们是战友,更是朋友,除在一起编刊物,写文章之外,还常常在一起聊天。鲁迅去世的前几天,冯雪峰天天去探望。
他也是最早得到鲁迅去世消息的人之一,并且还代表中共中央在幕后参与了鲁迅先生的后事。当年凭印象而来的种种误解和偏见早已在共同的战斗中烟消云散。但是,在鲁迅的性格当中,实在是蕴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一种是体现在文章中的,表现出的是毫不妥协、锋芒毕露的战士形象。
而另一种则是日常生活中的,是一个善良的、风趣的、没有任何名人架子的兄长。
我们说他是战士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指的是他的文字,而忽略了或者说不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普通的一面。我们常常错误地把他的为人当成他的做人,以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不苟言笑,没有人情,甚至不近情理的人。其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充其量也只是了解了他的一些作品,对他的生活起居,待人接物还缺少更具体、更真实的了解。
我们只看到了他人格中的一面,而非常地不了解其中的另一面。因而,事实上我们也就难以准确地走近这个对我们来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而这,对我们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诸如像鲁迅这样的人的为人,就难以走入他们的内心,就难以接近他们的精神天地。当然,我们对历史,对文化,对今天的选择,也就缺少了重要的参照。
而凭空的“神化”、“魔化”就会取代实事求是的对“人”的还原。
6、鲁迅精神是与权力阶级对抗?
罗兴萍先生正在做一个“鲁迅与九十年代文学论纲”的课题。这自然是很好的。不过他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上关于这一课题的前言《鲁迅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中关于鲁迅精神的论断却是不能让人苟同的。他说,在九十年代之前的近四十年中间,“鲁迅虽然被某种权力抬举到了神化的位置,但真正的代表着自始至终与权力阶级划清界限,并与之保持紧张的潜在的对抗性的鲁迅精神是被阉割和忽视了。”
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个论题,即鲁迅精神就是与权力阶级划清界限,并与之保持紧张的潜在的对抗性。概括地说,鲁迅精神就是与权力阶级的对抗。我以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偏颇的、简单的,是抓住了事情的某种表面现象,而回避或忽略了鲁迅精神的本真。
从某种意义而言,鲁迅是与权力阶级对抗的。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终身遭受通缉,常常处于被监视的地位,作品的出版和发表受到了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保障等等。可以说,鲁迅是在“权力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之中生活工作的。
他的许多作品也是对当时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批判而作的。从这一点来说,鲁迅是与权力阶级充满了对抗的。
但鲁迅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他作为战士,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最突出的贡献乃是表现在他对旧的僵化的思想、观念的批判上。诸如他对中国封建礼教的批判,认为那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对国民性中“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对国民中精神麻木、思想僵化的批判等等,都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代文化大师在思想领域的敏感和独特。或者可以换句话说,鲁迅的伟大和不容忽视,乃是因为他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贡献。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那些与鲁迅发生过激烈论战的人,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一些“学者”,而不是某一“权力”的化身。
比如与陈西滢、梁实秋、“第三种人”,以及与高长虹、创造社、太阳社等的论争,哪一次是因为“权力”或为了对“权力”表示“对抗”呢?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鲁迅的作品表现了他对“权力”的某种对抗性。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是因为“权力”成为黑暗、落后、僵化的文化形态的代表。比如女师大事件后“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控诉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动理解为与“权力”的对抗。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鲁迅这一“对抗”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谁都知道,陈西滢是反对女师大的学生运动的,并且写了文章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受到了鲁迅的痛斥。表面上看,陈西滢是在为军阀政府“帮忙”,实际上是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回避了陈本人也是反对军阀统治和殖民主义的。
他和鲁迅的分歧,乃是由于接受的教育不同,因而文化价值观不同所致。
说鲁迅是否与权力阶级对抗,主要得看是什么样的权力。当权力代表了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时,鲁迅与权力是合作的。比如辛亥革命后,他就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在国民政府中任职。而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反动军阀窃取,并大肆屠杀进步青年的时候,他便辞职南下,表现出不再合作的姿态。鲁迅也是善于运用权力的。比如他在教育部任职时,曾负责社会文化工作,对当时图书古籍的整理做出了开路先锋式的贡献。所以,笼统地把鲁迅精神概括为与“权力阶级的对抗”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其副作用也非常之大。第一,它只揭示了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从而容易使人们忽视或者认识不到鲁迅在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中做出的伟大贡献;第二,它会使人们误以为鲁迅是一个因不满“现政权”而出名的人,从而诱发一种对抗现实的精神状态或无政府主义思想,使鲁迅蜕化为现实秩序的批判者,而不再是文化精神的塑造者。总之,它不仅没有揭示出鲁迅精神,反而会使真正的鲁迅精神受到贬损。
7、鲁迅与人力车夫
说到鲁迅与人力车夫,人们不免要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对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大多读过先生的这篇不长的小说。那寒风中的人力车夫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写到的,“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的反省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这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据《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小说可能写于当年的十一月。因为是小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鲁迅与小说中的“我”等同起来,更不能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即是鲁迅先生本人。因而,鲁迅是不是真的遇到过这样一件和人力车夫有关的事,我们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小说表达了鲁迅的思考,特别是他对下层劳动民众的深切的肯定。当然,仅就这一点来说,是那一时代的一种思潮。比如蔡元培先生就认为劳工神圣,并且身体力行,从事平民教育。而胡适也对社会下层民众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如他在自己的诗中也曾经描写过人力车夫,对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当然,像鲁迅那样,用人力车夫来做自己精神上的镜子,以期从中照出自己灵魂深处不光彩的东西,还没有更多的人。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鲁迅的回忆,发现了一个鲁迅和人力车夫的真实的故事。鲁迅的侄女周晔在她的《伯父鲁迅的二三事》一文中曾写到,她的伯父鲁迅先生在世时,由于年幼,她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和伯父的接触中,却有一些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晔写到,大概是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因为鲁迅生病,她常和父母一起去看望伯父。一天的黄昏,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周晔和她的父亲周建人、母亲王蕴如一起往鲁迅先生家走去。在离鲁迅家后门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呻吟。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嵌进了脚底,鲜血淋漓,疼痛难忍。没有人理睬他,他也回不了家。她的父亲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了鲁迅家,“不一会,和伯父两人拿了药品和纱布出来,那个车夫被扶上了车子的坐垫上,伯父和爸爸,一个蹲、一个半跪在车夫的面前,伯父原学过医学,爸爸也懂得一些解剖,这时,便由爸爸把车夫脚底嵌在肉里的玻璃碎片,用钳子钳出,伯父把他的脚用硼酸水洗净,二人分工合作,替他敷药扎绷带,不多一会,包扎完毕,车夫说他可以支持着回去了,他的家也离此不远。于是伯父又掏出钱来,叫他在家里多多休养几天,又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周氏兄弟与那位不幸的人力车夫是毫不相识的。但是由于拥有了一颗博大的爱心,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图回报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良知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些所谓的“事情”,有大有小。大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小到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包脚。他们的行为,源于内心的大爱。所以周晔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的确,伯父严肃的容貌仪态中,却有一颗天下至仁至爱的心,他的心,他的血,他的情,是如此的热切,如此的真诚。”
周晔在她的文章中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在哪天哪月,什么时间。但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九三六年。我们知道这一年是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是在那年的十月去世的。这样的话,这件事就只能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年初了。那时,鲁迅的身体十分虚弱,可以说弱不禁风。他最后发病就是因为出门和友人说事受风引起的。这样看来,在天寒风大的冬日里,鲁迅竟然不顾自己的病情,去为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包扎脚,就有了另外的内涵。由此,我们也可以见鲁迅先生人格伟大之一斑。
8、鲁迅是怎样去演讲的
鲁迅先生一生做了很多的演讲。他的演讲总是吸引了众多的听众,有时甚至要改换演讲地点,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而热情的听众总是把他围了起来,以至于水泄不通。有时甚至把他抛到了半空中。其演讲的热烈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企及的。现在研究鲁迅演讲的人似乎多了起来,有人编辑了鲁迅的演讲集,有人对他的演讲内容进行分析比较,等等。但好像还没有人研究鲁迅是怎么去演讲的。最近读了几本书,多少涉及了这类问题。我以为从这样的细节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为人和做事来。
马来西亚的温梓川先生在他的《文人的另一面》一书中有很多对三十年代文人的回忆和描写。其中提到了他在暨南大学期间曾和同仁共同创办了文艺社团“槟榔社”,出版《槟榔月刊》。此外还组织邀请名人演讲。那时他们经过讨论并表决,决定第一位请鲁迅先生,依次是胡适、张竞生二位。温梓川说,“那次邀请鲁迅演讲,我记得最为省事。”因为他们既不认识鲁迅,又不知道鲁迅住在什么地方,便贸然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寄到北新书局转交。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果然收到了鲁迅的回信。鲁迅答应去暨南大学演讲,并且不用温梓川等去家里接,说他自己会乘坐火车到达。那时的暨南大学在真茹。温梓川常说他们到上海市区路途遥远。我现在也还不知道这真茹距市中心有多远,距离鲁迅住的北四川路有多远。但既然要坐火车才能去,可见距离一定不短,行走起来也很麻烦。温梓川在他的文章中说,“到了那天下午三时前,他果然如约从火车三等座走下车来。我们七八个同学,便把他一窝蜂地拥到大饭堂去。”既不认识,又没有熟人牵线搭桥予以介绍引见;既不知道住处,更没有亲到府上拜谒面请;当然也很难说要支付巨额的稿酬劳务,只是凭一种热情就贸然发出了邀请,也只是因一点责任就同样贸然地答应前往。不知鲁迅是否感到了他们的唐突不周,或者自己花钱坐三等座独身前去有失身份?总之,他只是觉得该去而且能去,他就去了;能不麻烦别人的地方就尽量给人以方便,更谈不上什么名利之虑。一切就是那么自然,毫无伪饰,毫不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