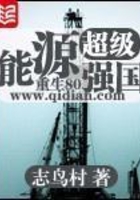光阴似箭,几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林徽因对儿子梁从诫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拨开迷雾,她读到了自己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感受,拒绝并不是她的懦弱和胆怯,不过是当时的情感来得太过突然,让她有些手足无措。当她冷静下来,深埋在心中的理智告诉她,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他爱她,却爱得不真切。她不爱他,则是最坦诚的回答。
世间女子能有几人如林徽因这般,懂得繁华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道理。爱情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某一人一时的突发奇想。
爱情容易让人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唯有时间,才会给一切疑问应有的答案。
爱冲动的姑娘们,理智点吧。
在感情中受伤在所难免,可理智能帮助我们将它的杀伤力降到最小,这是我们全身而退的法宝。
独立是长矛和盔甲
有生之年,只能依附于别人的女人,注定少了些气场。
女人拥有独立的人格,才不会在别人的议论中亦步亦趋,才不会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也唯有精神独立,才不会受他人的思想摆布,自由自在地活出自己的人生,拥有令别人拜倒的魅力。
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在与林徽因接触后,这样评价"情敌":"徐志摩的女朋友是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从肉体到灵魂的独立,让林徽因有机会划出不受他人束缚的人生轨迹。她驰骋在自己广阔的天地里,有时如鹰击长空,有时如浮云缱绻。
女人绝对可以选择自己最得意、舒适的姿态活着,让自己变成独一无二的存在。
关于林徽因的童年,她很少提及,甚至不愿意说起,不过在她的一篇散文中留下了些许文字记载。她6岁时得过水痘,在她的家乡,这被称为"水珠"。
林徽因的特别,在6岁时便显露出来了。一般的孩子得了病总是哭闹不止,而她竟然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她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
就是这种小小的荣耀与骄傲,确定了她不同凡响的一生。她有一对不轻信旁人的耳朵,一颗不盲目从众的心,一个独立而坚挺的灵魂。
父亲林长民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在外,6岁的林徽因留在祖父身边充当起小通信员的角色,早早就端起大人的口吻,代笔为祖父给父亲写家信。
大部分信件已经遗失,留下的是家人保存的一些父亲写给她的回信,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她7岁那年。
徽儿:
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趾趾闻甚可爱,尚有闹癖(脾"气否?望告我。
祖父日来安好否?汝要好好讨老人欢喜。兹寄甜真酥糕一筒赏汝。我本期不及作长书,汝可禀告祖父母,我都安好。
父长民三月廿日
6岁的林徽因已经开始慢慢承担大人们的事。林家有女初长成,12岁的林徽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倾听父亲心事的姑娘了。
当其他孩子在尽情玩耍,享受快乐的童年时,林徽因却一边玩耍,一边悄悄构建着她的内心世界。也许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些残忍,直接缩短了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时光,却也在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她的成长,在今后的许多年里,她靠着从小培养起来的担当和独立,不急不缓地描绘着自己的人生。
祖父病故之后,父亲仍留在北京勤于政务,全家人则住在天津。林徽因以长姐的身份平衡支撑着一家人,伺候着两位母亲的日常生活,照顾着几个弟弟妹妹的饮食起居,乃至搬家打理行李这样的活计,也落在她的肩膀上。
成年后,她在父亲写给她的一封信上批注道:"二娘病不居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嘱吾日以快信报病情。时天苦热,桓病新愈,燕玉及桓则啼哭无常。尝至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桓始熟睡。乳媪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
愈是被别人依靠着,她就愈是独立。
她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年纪虽小,阅历虽浅,却一个人默默承担着本该由家长来担起的责任和压力。
在父亲远游日本的时候,她将家藏的全部字画翻了出来,一件件分类,编成收藏目录,以便日后供父亲赏阅。在给父亲的家信上反思道:"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
没有人指引她该如何去做,没有人帮她分辨好坏,完全靠她自己去慢慢经历、感悟。也许会感到辛苦,也许会觉得委屈,然而,正是这样的磨炼洗涤了女人的优柔寡断。
当她以崭新的姿态站在历史舞台上,无人不会为她的精神面貌所倾倒,这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更是一位主宰自己人生的女王。
出身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她原本可以凭着优渥的条件养尊处优,甚至依附于丈夫,在家中舒适地做着梁太太,享受着他人提供的一切优待。
不问世事、逍遥自在地过生活是女人幻想过无数次的美景,丈夫在外奔波赚钱,作为妻子,只要打理好家务就可以了,不用风吹日晒,更不用历经辛苦,一切的"不舒服"都抛给别人。
这样无所事事的生活真的好吗?用不了多久,便会与社会脱轨,直至完全丧失存在感。
林徽因勇敢地脱离了丈夫的庇护,她以独立的个体与他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里,她依旧勇往直前,自食其力。
在"太太客厅"里,一场又一场的聚会中,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由她主导着来客的情绪。在这里,她无拘无束地释放着光芒,即使外界的流言蜚语从未停止,她只是莞尔一笑,继续着她的传奇。
她的存在不是为了卖弄自己,去取悦别人,所以她的世界无关他人。
唯有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独立的人格,才不至于在众说纷纭的世界里迷失自我。那些善意的评论或非善意的指指点点,都不足以让一位独立的女性惧怕。
在混沌的社会中,她自有一套标杆和准则。在自己确认无疑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收获成功,收获喜悦,体味辛酸,体味痛楚。
独立是她的长矛和盔甲,是她行走在世间的武器和防护。好的、坏的,都是沿途的风景,不骄不躁,宠辱不惊。
她是梁太太,可她更是林徽因。
事业上,她与丈夫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即便如此,她不只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还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
学术上的成就不逊色于丈夫,甚至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与他同处于一个平台,不是上级与下属、主导与跟从的关系,相反,是平等的、合作的。
卞之琳在《窗子内外:忆林徽因》中直言不讳:"(林徽因"实际上却是他(梁思成"灵感的源泉。"
梁思成也曾对朋友们提起:"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这个专业。"
当林徽因与丈夫及同仁们结伴外出考察时,她虽然穿着窄身旗袍,又体弱多病,可她爬起古建筑的穹顶来,却行动敏捷,根本不成问题。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到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习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是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做摆设似的!"
换作他人,能被冠以"美人"的头衔,嘴上也许会做谦虚状,心里早该暗自开心了,可她却排斥这个美名,倒不是因为这个词有欠妥当,而是她不甘心只做被别人观赏的摆设。
平日里,林徽因和梁思成常常就一个问题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她有她的学识见解,甚至不会轻易屈从于权威。她的努力付出不比任何人少,自然,她的成就也不会低于任何人。
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林徽因向来是与丈夫梁思成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两个人互相补充,两个独立的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起创造着辉煌。外界经常低估林徽因的专业成就,这对她是不公平的。
陈学勇在《莲灯诗梦:林徽因》中提到:"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国妇女先觉者"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成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女人极其容易演变成男人的附属品,失去自我,沦为没有思想、没有主见的家庭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