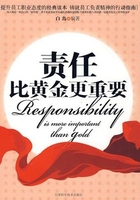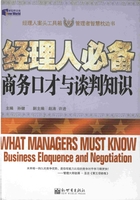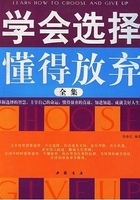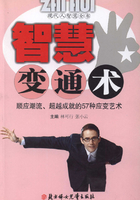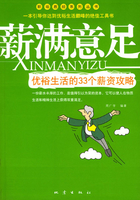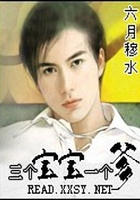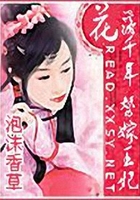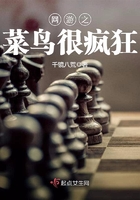吴荔明女士说过,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确实相处不谐,只与她的母亲梁思庄没有芥蒂。她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李健吾曾用她的"高傲"来解释,其实未必如此,更多的应该是缘于她的率性和不世故。
周遭的女性与林徽因相比,不论在知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有所差距,她们之间没有可以建立起友谊的共同话题,林徽因的高谈阔论,她们不懂,她们的家长里短,林徽因却不愿参与,她又从不会敷衍、周旋,产生误解和生分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这虽怪不得林徽因,却也正可以劝诫其他女人,要适当地融入周围的女性朋友圈,多交些女性朋友,总是好的。
梁从诫曾回忆说:"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母亲喜欢交朋友,她的热心和健谈是有名的,而又从不以才学傲视于年轻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许多忘年之交。"
率性还是刻薄,女人们切记把握好分寸。
有些话是不是该说,该在怎样的场合说,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说,是有很多讲究的。一句无意间的话,也有可能会伤了别人的自尊心。
人人都有不可触碰的雷区,有敏感的心理地带,也许藏着一些难以言说的小秘密,即使并无恶意,也应该注意分寸和时机。
与人交往中,不要吝惜发现美的眼睛,赞美别人的闪光点,让他人感到一股暖意,这才是贴心的朋友。
有一种宝藏叫作朋友
朋友是一座能说会道、能跑会跳的宝藏。
正是在岁岁年年的相处中,经过点点滴滴的融合,才得以积累起牢不可破的信任和心有灵犀的默契。
朋友之间的真心,是岁月的积淀,看穿了许多事、很多人,最初的愤愤不平慢慢转变为接受和释然,看清了,也就看轻了,无所谓遗憾或后悔,只是留不住的感情,实在没有硬生生扯着不放的必要。
而在了解了彼此的缺点之后,依旧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这是被时间证明了的友情,也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事情,相对无言,会心一笑,一切的一切,都懂。
那些过去的记忆,有的已经消失,无处可寻,但更多的被我们牢记,每一次回想起那些往事,纵有千言和万语都说不完。
文章也许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感情是真心实意的累积。
比爱情更长久的便是友情,金岳霖是这一论断最有力的践行者。
幽默风趣又温文尔雅的金岳霖,朋友们亲切地叫他老金,林徽因也不例外。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自从徐志摩将他作为挚友引荐给林徽因夫妇后,他始终是"太太客厅"的常客,逐渐成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他们之间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多了份惺惺相惜,加上志趣相投,性情也颇合得来,彼此的感情也就格外深厚。老金赞羡林徽因的人品才华,推崇至极,对她十分呵护,林徽因对老金更是敬爱有加,钦佩他的智慧和为人。
金氏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海光,1949年赴台湾在台大任教多年"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7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老金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林徽因的至交,也能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林徽因的品质。
林徽因和老金之间,心心相印,甚至一度将友情上升到了爱情的地步。林徽因亲口将一切实情告诉了丈夫,他没有勃然大怒,没有声嘶力竭,有的只是难以割舍却又不得不割舍的退让与包容。
梁思成甘愿让位,忍痛成全林徽因和老金,而老金感动之余,爱屋及乌,强忍下满腔爱意,真心祝福林徽因和梁思成。能同时被两个如此优秀的男人深爱着,林徽因是幸福的,她看到了丈夫对她的爱,也明白了老金的苦心,最终,她决定将浓厚的爱情给梁思成,将纯粹的友情给老金。
故事讲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不是男女主人公随后散落天涯、各自安好的桥段。没能拥有爱情,还可以拥有友情。
"你说再热闹也终需离散,我便做了这一辈子与你看。"此句极为应景。
老金从此绝口不提爱意,她需要的是友情,那么,他就将挚友的角色扮演好。他是逻辑学家,他用抽象的思维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自己长期不成家的寂寞。
他后来认真地分析了自己与林徽因、梁思成之间的亲密关系,按他的逻辑推理:"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爱而不得,也许在某一点上被描绘成悲剧,可退一步来说,不曾拥有就意味着永远不会失去,友情就是最好的回报了吧,在有生之年,还能够以朋友的身份纯粹地互相"喜欢",便也足够了,未尝不是幸福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来到李庄避难,困顿的生活使她的身体病弱不堪,金岳霖拿出微薄的薪水,跑到大老远的集市上,买回来几只老母鸡,悉心照料着,为的是等老母鸡下蛋给林徽因好好补一补身体。
一生能得此挚友,被这般关心着,该当无憾了。
朋友的最高境界是相互信赖,那些难以启齿的窘事或秘密,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吐露,不必担心他会嘲笑挖苦。
林徽因就是沈从文最值得信赖的朋友,那个压抑在心中许久的秘密,也唯有一五一十地告诉她,才能缓解胸口的憋闷。
1936年,刚过完春节不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热闹还没有退散,沈从文与高韵秀的地下恋情给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安。
憨厚木讷的沈从文将自己恋上他人的感受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原本希望得到理解和原谅,可是他想得过于简单与美好,任何一位妻子听到丈夫移情别恋的事情,都不会轻易原谅,张兆和盛怒之下,连夜回到苏州的娘家。
痛苦和无助狠狠地掐住了沈从文的喉咙,无处诉说的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林徽因。
当绝望中的沈从文来到梁思成家,向林徽因倾诉他的烦恼时,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林徽因首先说:
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虽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都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澜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沈从文说:"我不能想象我这种感觉同我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与事,我就是这样的人。"
明明惦念着两个女人,却不知道妻子为什么会生气恼怒,也算是有些过分了。
作为朋友,也作为女人,林徽因用超越普通男女的视角来看待感情这件事,她说:"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
林徽因对自己的朋友这样形容当时的沈从文:
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个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的苦痛与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林徽因在1936年2月27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进入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的心里使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林徽因在朋友圈里,素来是感悟、理解能力最好的一个,她能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感觉,她不会偏激地去否定,也不会极力地去赞扬,她站在事物的更高层次上去理解。
比如沈从文和高韵秀之间的感情,她也经历过相仿的纠葛,她明白这转瞬即逝的明媚心情多么难得。许多人此生都没能遇到一次怦然心动,该是何种遗憾。
然而在感情之上,还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这是对自我感情的维护,所以孰是孰非,心里要有数。
女人们总会有一箩筐的悄悄话想要和好朋友分享,这是连最亲近的丈夫也不能知晓的小心事、小情绪,闺密的位置,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当然,感情是相互的,一头热地付出不仅可叹,也总归不会长久,在享受朋友的关怀备至时,别忘了报以诚挚的微笑,告诉她,她的好,其实你都知道。
不必日日月月、时时刻刻都能在一起度过酸甜苦辣,知道彼此生活安好,便会由衷地开心,这样的人就叫作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