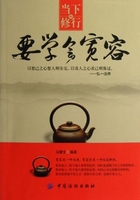【心上】
伤口已经包扎。血止住。但疼痛的感觉始终停留在手臂初初断裂的那个时刻。一直痛,痛进心里去。痛成了无穷无尽的怨恨。
白涵香闭着门,不肯接受阮清阁的歉意。
尽管这歉意根本无法弥补什么,但它如此盛大,如此浓烈,生生的压得阮清阁周身的血脉都坏死。他宁可断去的,是自己这双无法兑现承诺的手。
阮清阁决定亲自将白涵香的母亲接到镇上来,好生的照顾她。白老夫人极瘦小,干枯的,像一棵缺水的树,连行动也很迟缓。她听说自己的女儿出了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在半路上,就咳出一滩血来。一声声的哭喊着,是我连累了她,都怪我,都怪我。
阮清阁越发难受。
伤人的屠夫已经受到制裁。他因为之前痛失爱女,思想变得偏激,他认定了白涵香就是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所以,他要报仇。虽然他伤人的手法极残忍,但却因为他的悲惨遭遇得到众人的同情。他不过是依照苏和镇的某些条例,受了轻微的皮肉苦。
白涵香得知此事,欲哭无泪。
没几天,白老夫人在阮家的客房落了气。张着嘴,似有话要说。白涵香几次哭倒在灵堂。整个人迅速的瘦了一圈。
那场丧事,由阮清阁一手操办。也算是办得体面。纵然白涵香对他有千般的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到底生了一副柔软的心肠。况且,她已举目无亲,她住在阮家,受上宾的礼遇,她想阮家的人不计较她的出身来历,对她也算仁慈,她惜恩,那肿块一样的怨毒之意,便逐寸逐寸的化去了。
有时候,阮夫人会亲自看望白涵香,给她送去补身的汤药,或者是好看的衣裳。阮夫人出身贫寒,对白涵香的遭遇极为同情,又见阮清阁为了这女子忙进忙出,愁眉深锁,她隐约觉得两个人之间也许是有什么的,况且,白涵香生得清秀,是颇为标致的一种贤良的模样,能讨她的喜,她对她,自然又多了几分热情。
阮夫人在私下询问阮清阁,你是不是对白姑娘有意思?
阮清阁吓了一跳,急忙摇着手说,不,不,不,娘您说到哪里去了?
阮夫人却笑,道,若是普通的女子,有什么理由你对她那么好,你可有认真的想过,是不是,连你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你真正的心意呢?
阮清阁顿住。在那一瞬间,他想起的是白涵香楚楚可怜的模样,想起她缺失的手臂,她苍白的脸,深锁的眉,还有水晶一样剔透的眼泪。在那一瞬间,他也想起了立瑶在纯真中带着妩媚的笑脸,她纤弱的身子,俏皮的话语,还有骨瓷一样细滑的皮肤。
此后。
风波似平息了。苏和镇回复了往常的安宁。阮家也静了。他们又一次论及酒场的营运问题,阮清阁不甘心,再次提出,到南京开酒铺。但阮振国对此始终有保留,听则听矣,却不做答。
阮心期出言反对。
他是阮振国的养子。在阮家已经十八年。阮清阁六岁那年离开苏和镇,那时候,阮家还没有阮心期。他是回到这里,才被以长兄的身份介绍在阮心期的面前。他的心里有芥蒂,他觉得阮心期对他亦是,他们表面看来相处融洽得当,但他们之间缺少了兄弟间的手足情,彼此都有点生疏。
阮心期说,南京那样混杂的地方,什么酒没有,若竞争起来,苏和清酿未必有取胜的把握。开酒铺是需要周密的调查和详细策划的,不是说开就开。酒场的资本有限,无论是哪一种用途,都应当谨慎。
在座的人,无一不点头称是。
阮清阁黯淡下去。
这时候,门外有人说话了。说的是,你们这些人,也太闭塞太保守了些,我倒觉得,大哥的想法,未尝不可一试。
说罢,却迟迟不见露面。
阮心期虽然被对方毫无礼貌的顶撞了一回,可他不但不生气,脸上竟倏地堆满了愉快的表情。他对着门口发笑。阮振国则沉了脸,手握着拳头放在嘴边,干咳几声,道,清雪,不得胡闹。
语罢,门口的人儿施施然走了出来。
【掌上明珠】
这女子,阮清雪。短发齐肩,乌黑。顶上绑着月牙形状的乳白色丝带。蓝底碎花的斜襟上衣,白色的长裙上有整齐的褶皱,黑色的皮鞋配着雪白的棉袜子,整个人,利落又不失端庄。在眉眼间还有些许的桀骜,以及女子的妩媚和俏皮。阮清阁看她的第一眼,想起了立瑶,只是她的身上透着一股不可驯服的锋利之气,笑容间还有藏不住的清高。
阮清阁想,原来她就是清雪,阮清雪,是自己的妹妹。他六岁离家,她还是襁褓中不足月的婴儿,如今,这般亭亭玉立。
果真是,年华易逝,韶光催人老。
阮清雪是阮家最得宠的后辈。她生就一颗玲珑心,左右皆逢源。一张灵巧的嘴,更是就像抹了蜜糖。就算偶尔任性,偶尔撒娇,也只让人觉得那是她可爱的小姐脾气,无伤大雅,甚至犹如餐后的甜点一样,是一种情趣。
这样一颗掌上明珠,在阮家,受尽恩宠。尤其是阮振国。因为阮清阁早年流落在外,阮心期又是养子,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所以阮振国一门心思都倾注在小女儿的身上。早些时候,还特地聘了教书的先生,教她读书识字,如今又将她送往南京的女塾,巴巴的望着她能成为人中龙凤,天之骄子。她对家中的生意向来关注,此次,趁女塾放假回乡探望,一进们便听见这样的话题,她意兴昂然,早已经跃跃欲试,而她既然开了口,阮振国便饶有兴致的,问她,你也赞成你大哥的提议?
轻轻的一句话,惹了堂下两人,心生惆怅。
阮清阁想自己多番苦口婆心,却抵不过妹妹的三言两语,受挫与失落的感觉油然而生。阮心期则嫉妒。嫉妒清雪没有跟自己站在同一条阵线。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她的兄长,但阮心期和清雪却没有血缘的关系,他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他对她的爱护,已经超出了兄妹的界定。
他喜欢清雪。
这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无第二人知晓的秘密。
时过正午。蝉噪。鸟鸣。人的声音却极贫乏。
阮清阁以为,他只是想要在镇上的任何地方随便走一走。但他走去了蓝家。映阙在院子里晒棉被,看见阮清阁远远的走过来,笑道,大少爷是来找立瑶的吧?
而彼时,立瑶正抱着一床棉被,从屋里出来,看见阮清阁,竟有一种隔世般的惊错。自从白涵香一事,她已经许久不见他了。她也听过外间的传言,说阮清阁对白涵香如何的鞠躬尽瘁,她听得憋闷,吃饭睡觉都不安稳。
于是,一刹那的欣喜,草草的,都被流言覆盖过去。
他们并肩走着,白花花的路面,很刺眼。阮清阁说,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和你说。
立瑶抿着嘴,不做声。
那是难得的,素来爱说爱笑的女子,噤了声,只是如同旁观客,如同局外人,低眉顺眼的听着,偶尔附和三两句。
末了,阮清阁说,谢谢你。
可是,谢什么呢?立瑶想。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你待我是如何,我待你又是如何,我竟迷糊了,捉不到此刻自己心中的悲喜,你走吧走吧,不过是一个转身而已,不过是如此而已。
暖风熏人。
吹了满地唏嘘。
【南京】
阮清阁回到家,看见清雪。清雪站在后院的樱桃树下,笑眯眯的望着他。他掷出一个相对勉强的笑容,欲往侧门走。
清雪唤他,哥。她说,我刚才看见你了。
哦。阮清阁不以为意。
清雪走上前来,仍是笑,她说,那样的女子,大哥应该离她远一点才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她的名声可不好呢。说着,也不管阮清阁的脸色如何难看,便将立瑶从前在女塾的事情都讲了出来,譬如,她逃学,课程差,她偶尔会跟学友争执,惹老师厌烦,她总能认识一些风月场中的男子,往往衣着香艳,彻夜不归,最后,她索性连学也退了。清雪和她就读于同一所女塾,又是同乡,因而多了些关注,但她对她,是全然没有好印象的。
清雪说,这样的女子,就像一只狐狸,你永远猜不透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想些什么,她下一刻又会去做什么,我怕你太靠近她,会伤了自己。
阮清阁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他宁可相信自己亲眼看见的,一个健康活泼的蓝立瑶,她应该单纯,她应该美好,而不是活在谣言下。阮清阁只是轻轻的应了一声,说,我知道了。
但其实,在暗地里,却无法不将清雪的话放在心上。
辗转思量。
阮振国终于同意在南京开酒铺,小试牛刀。尽管他出于保守估计,投入的资金有限,但对阮清阁来讲,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最难解是阮心期。他问清雪,你为何一定要说服爹采纳大哥的意见,做生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清雪扬了扬眉,说道,我们的生意就是太小气了,好比从前的清政府,盲目,闭塞,妄自尊大,才落了个亡国的下场,你若到外面去看看,你也许会觉得,在这贫穷的小镇上终老,是你一生最大的遗憾。
阮心期弓着背,头微微低下去,问,清雪,你不喜欢这里?清雪笑言,是的,不喜欢,非常不喜欢。她的神态坚定,连牙关也几乎咬紧了,于是阮心期满腹的话都被她一个眼神镇压了回去。他想问她,难道苏和镇就没有一条吸引她的理由,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她留恋。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被遗弃在荒原的孤雁。晴空万里,她和他,隔着天,隔着地。
蓝家很冷清。简陋的旧式小庭院,瓦片上长满青苔。角落里惟一的一棵桂花树,低矮,又瘦小,也不到开花的季节,看上去萎靡得很。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只有映阙一个人,在堂屋里坐着发呆。她开始想念南京,想念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旅馆,吃过的饭菜,以及,她遇见过的人。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
是阮清阁。
映阙自然以为他又是来找立瑶的,她说,立瑶走了。是昨天的事情。她坚持要去南京,触怒了爹娘,他们锁着她,要她反省,谁知道,半夜里她竟然爬窗户走了。
阮清阁愕然,问,她为什么要去南京?
映阙苦笑,道,为了她的理想吧。也许旁人是很难理解的。
阮清阁沉默了一阵。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沉默,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片空白,好像空空的,又好像满满的,总之,千头万绪,理不出一个思路来。映阙接连唤了他几声,他才缓过神,道,我这次,是来找你的。
后来。
山水都清亮了。河风暖融融的。从眼睛里,嘴巴里,耳洞里,皮肤上,钻进身体的五脏六腑,如一场洗礼,润物细无声。
映阙想,未来会不会是一场梦呢?
尽管她是获得爹娘的同意,才离开苏和镇的,因为阮家在南京开酒铺,需要人手,阮清阁觉得映阙温良又聪颖,模样亦是出众,遂希望她能够去南京帮忙打理酒铺的生意。但南京是什么样的地方。南京就像天上的月亮。美得很,也玄得很。她这样平庸的小女子,去了,也不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但她想去。
她巴巴的望着爹娘乞求他们的同意,那个时候她的身体里已经充满了南京。爹娘直感叹孩子长大了,心野了,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她的魂。他们终于还是点头。他们说,你去了,好好的看着立瑶,别让她再出什么乱子。
她说会的,我会的。
但她此刻看见了南京的岸,听见了南京的风,却开始忐忑起来。她想起阮清阁说,我相信你可以应付得来,她才稍稍拾回了一点信心。然后又想起曾经在那片陆地上逗留的短暂时光,想起一张熟悉却也陌生的脸,她抬起头,望着江岸垂杨绿柳,如梦呓般的,轻轻的念了一声,南京。
【擦身】
苏和酒行。
新铺。新开张。红色的绸缎还挂在匾额上。但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店里的伙计都和映阙一样,是从镇上出来的,有人为了养家糊口,也有人真的踌躇满志,期望能有一番作为。
无奈这惨淡的光景,似倾盆的雨,兜头而下。
阮清阁一直在门口站着,负着手,眉头不见舒展。映阙走上前,试探着说道,大少爷,我有一个法子,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阮清阁的眼睛里终于有了光。
映阙的法子,是在店门口放几大缸酒,一来让酒的香气随意扩散,二来,若是对酒有兴趣的人,还能够免费品尝。
如此,店铺门口倒真是热闹了起来。
阮清阁忍俊不禁,但不是因为招徕了生意,而是笑自己,这样简单的法子,竟没有想到。映阙看阮清阁笑了,自己也跟着笑。旁边有顾客不留神撞了她一下,她一个趔趄,鼻子撞在阮清阁的肩膀上,这一撞,两个人笑得更厉害了。
有黑色的轿车从门前经过。
映阙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