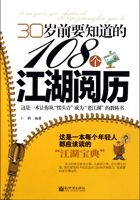还是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仗势欺人,破口大骂,你妈那个起码子,哪个霸啦,哪个抢啦。格老子把嘴巴子放干净点,小心老子扇你杂毛的耳刮子。你他妈简直是狗坐鸳兜不识抬举。
少给老子耍歪。不霸不抢,就拿钱来。货郎毫不示弱,硬生生地把说话的人顶了回去。
拿,拿你妈那个起码子,不松松你那张猪皮子,就不晓得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老子这就给你龟儿子拿来。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说着,就往前扑。传话人刚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货郎的脸胀成了猪肝色,霍地站了起来,转身从货架上抽出一把杀猪刀,毛发直立,怒目相视,严阵以待。
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只是一愣,并没有放慢脚步,径直向货郎扑了过去。
货郎已经横下了一条心,挺直了尖刀,直接朝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腹部捅了过去。
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来势凶猛,不避不闪,刀虽穿背,但仍伸手牢牢地抓住了对方的衣襟。
货郎身手也算敏捷,左手格挡的同时,右手用力拔出尖刀,又连捅了两刀。
那个毛毛躁躁的年轻人毕竟已受重伤,再也经不住对方的用力推挡,身子摇晃,訇然倒地。
见血眼红。货郎飞身跃过年轻人,直向那帮人扑去。手起刀落,又重伤了一人。
传话人见状,转身便逃。
货郎一个跨步跃起,奋力把杀猪刀向传话人背心插去。不曾防,一直躲在门外的一个家伙,已经高高地举起了顶门杠。
货郎头部重伤被缚。一个未曾负伤的家伙,提着那把还在滴血的杀猪刀冲出来,连连在货郎身上戳了几十刀,直到血液流尽才住手。残忍的家伙们还剖开货郎的腹腔,挖出了他的心肝,扬言要拿回去下酒。
唐老先生不忍货郎横尸街头,当晚就雇人用店铺门板做成一个火匣子,也就是一种简易的棺材,将他装殓埋在了乱葬坟。出事前寄在老先生这儿的东西,他也都找熟人先后带给了货郎的妻儿。老先生最后不无惋惜地告诉两个年轻人,货郎当时如能稍微忍一忍,不与那些恶人去一争高低,也不至于没了店铺,还要白搭一条命。想来,他的儿子和女儿也该十六七岁了,该成人了,如果子承父业,也能够做货郎了。
天祥对爹爹已无多少记忆,但多次听妈妈讲过爹爹的事。老先生故事里的货郎就是爹爹。天祥当时不到四岁,对父亲的记忆相当模糊。只记得父亲个子高高的,眉毛浓浓的,胡子特硬,往脸蛋上一挨,就很痛。父亲劲儿大,开心的时候,总把他往空中抛,他是又惊又怕又喜欢。生意关张空闲下来了,父亲就把他架到脖子上,到外面去遛遛,他觉得自己好高好高。吃饭的时候,他就坐在父亲的大腿上,舒服极了。父亲对秀秀也特别好,也经常抛她,亲她,秀秀的笑声特别清亮,特别好听。
妈妈一直没告诉天祥事情的真相,就是担心他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去找仇家寻仇,她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主要的是出于对他安全的顾忌。十多年过去了,恶人不但没有遭到天愆,至今还招摇过市。
8
在进货返回的船上,天祥遇到了一个同船的木匠师傅。木活背篼里有大小不一的刨子,宽窄各异的凿子,长长短短的锯子,还有墨斗、直尺、刻刀等东西,看来是一个打家什,做细活儿的师傅。木匠师傅说他在巴中一带做了好几年活路了,这次到两河口去办点私事。天祥听说是从巴中来的,就有些好奇地问他见没见过霉老二,到底有好凶,为啥子专门整有钱有势的人,还闹了啥子红,闹红到底是咋回事儿。
船行江中,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木匠师傅说话也少了许多禁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船上的人,巴中过队伍不假,来的不是霉老二,是红军,人很和善的,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凶。闹红也不可怕,对广大穷苦人来说还是好事儿。闹红,闹的是革命。闹革命靠的是红军。红军不是霉老二,他们专门收拾恶人,把财主老爷们的钱物分给穷苦人用,粮食分给穷苦人吃,田地分给穷苦人种。在红军的天底下,穷苦人不再怕有钱人。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的遭镇压了,敲了沙罐,打了脑壳。有的时候红军还帮穷苦人种地耙田,侍候庄稼,平常就操练,学打枪,还有女红军教他们识字念书哩。
天祥特地问了红军咋个镇压恶人的事儿。木匠师傅说,简单得很。只要有人检举,告诉红军那个恶人有血债。红军就派人核查,如果是真的,就派队伍去抓来,再开公审大会,上面批准了,就敲沙罐儿,打脑壳。
木匠师傅还说了,在红军的天底下,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男人不敢随便打婆娘了。如果哪个男人不讲理,打了婆娘,婆娘就可以找女红军给评理。那些女红军可不得了,凶得很,说话一套一套的,直到把那个男人收拾巴适了才松手。还有哪个不怕的。但是,那些女红军对人特别好,听说哇,一些男红军负了伤,没法吃东西了,带了娃儿的女红军就给挤奶吃。这可是真的哟。
天祥问红军整不整认不倒的生人,木匠师傅说那哪儿会呢。他帮人做家什,就没得哪个过问过他。他还帮过红军哩。红军找他去钉木箱子,做床,还给伤员做拐耙子,给工钱还管饭。女红军特别夸他做的拐耙子轻巧,好使得很,伤员都喜欢。
天祥问还有啥新鲜的事儿,木匠师傅说有哇,多得很,胆子放大点,过去亲眼看看最好,眼见为实嘛。木匠师傅还告诉天祥,红军要大家都要有觉悟,都起来闹革命,组织苏维埃,把坏人、恶人都给敲了沙罐儿,把有钱人财主老爷的命都给革了,天下就是穷苦人自己的了。
木匠师傅能说话,从上船一直说到下船。临别时,还特地招呼船上的人,千万不要对人说红军就要过来了。对红军的事儿,一船人有的好奇,有的怀疑,有的漠不关心,也有人很向往。天祥心中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憧憬,但他又将信将疑。
9
货不经卖,没多久就要再次进货了,妈妈好像对天祥已经有了信心,没再阻拦他,只是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小心,不要让妈不放心。天祥这次出去很想把秀秀也带上,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好说话儿,出了门没一个熟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做他们的游戏了,免得偷偷摸摸的,但这次出去不仅仅只是为了进货,他还要做买卖,如果带上秀秀就很不方便了。于是决定还是一个人去算了。临走前,他给妈妈和秀秀告别,说这次进了货,得转一转卖些东西,可能要过些日子才回得来。
秀秀没争着跟天祥去。他出门后的一天晚上,她独个儿来到天祥家,见幼兰也一个人烤火就着小油灯纳鞋底子,就挨着坐下。不时拿眼睛看一看幼兰,欲言又止。
平时,秀秀见幼兰,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儿。幼兰觉得有点奇怪,就鼓励她有啥事儿直说就是了,莫啥子好为难的,真有啥事了,大姐会帮你的。
秀秀还未开口,就先成了一个泪人儿。她跪在幼兰面前,两只手扶着她的一双膝盖,使劲儿摇了又摇,泪眼哀哀地望着她,直喊姐,姐哩。
幼兰不知是咋回事儿,就一个劲儿地安慰秀秀,并催她有啥事儿尽管说出来,姐一定会想法子帮忙的。
秀秀只顾掉泪,憋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我和天祥几个字就又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幼兰以为天祥欺负了她,就一个劲儿地骂天祥,死砍脑壳的,敢欺负妹儿呐,等回来了,看姐不好好收拾他。
秀秀生怕幼兰错怪了天祥,极力为天祥辩解。不是,姐。天祥好好儿的,都是我的事儿,你一定得帮帮我。
幼兰对秀秀从来都是依着顺着,生怕哪儿做得不好,为难了这个小妹儿。她一边使劲拉秀秀起来,一边安慰着她,妹儿,你有啥事儿,起来坐,好好给姐说说。
以前,秀秀的任何问题,用柔语软话,再加撒娇,在幼兰这儿都能得到彻底解决。她这次还打算使用同样的方法,不,你答应了,才敢起来。
幼兰真是拿她没办法,但就是发不起火来,只能耐着性子催她说出事情的原委,说嘛,哪回姐没帮你呢。
秀秀见幼兰语气很温和,知道她不会发火的,更是得寸进尺,又撒起了娇,就不,你得先答应了。
幼兰奈何不了秀秀的缠劲儿,只得满口答应下来。好吧,姐帮,帮。不管妹儿有多大的事儿,姐都帮,还要一帮到底。这下行了啵,还不给我起来呀。
秀秀慢腾腾地站起身来,拿过一条小板凳在幼兰面前坐下,趴在她的大腿上,拿眼睛望着她,眼里尽是无助和期盼。
幼兰似乎觉得真有事儿了,就停下手中的活儿,用手抚摸着秀秀的后脑瓜子,轻轻地催她,妹儿,有啥事儿尽管说出来吧,姐在这儿听着哩。
秀秀得到幼兰的承诺,有了指望,就大着胆子告诉幼兰,姐,我喜欢天祥,天祥也喜欢我。
幼兰有点儿奇怪了,两个娃娃喜欢是自然的,还用说吗。是不是有了别的啥事儿了,她还不明白。咋个喜欢法,给姐说说明白,慢慢儿说噢。
秀秀望着幼兰的眼睛,认真地说,姐,我和天祥都是吃你一个人的奶奶一块儿长大的,自幼在一起,长大了也一样,我们没分开过。最后仍然强调,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
秀秀自小没妈,幼兰一对奶奶喂两个娃娃,把秀秀当女儿,这个家任她自由出入,两个娃娃也形影不离,这在大天井是家喻户晓的事儿。她看着秀秀的眼睛承认道,还用说吗,姐都晓得啊。你们两个就像一根藤藤上的两个瓜瓜。
按辈分儿秀秀和天祥是长辈和小辈的关系。她以前承认,现在却不能承认了。她就直拗拗地告诉幼兰,姐,我不做天祥的姑了,他也不是我侄儿。
长辈和小辈的关系哪能说变就变呢。幼兰认为秀秀在说傻话,对她笑了笑,仍然坚持道,那咋行呢,傻不傻啊,你本来就是他姑,他就是你侄儿呀。
看到幼兰是这样的立场,秀秀再次着急了,喊了一声姐,又哭出了声,哭着说,姐啊,你答应帮我的啊,姐。
幼兰见秀秀无助的样子,怕她有话憋在肚子里,就再次鼓励她,看看,又来了,不是答应过了嘛。说,姐一定帮你。
秀秀见幼兰那样友善,是真的关心自己,就把在古城产生的想法说了出来。姐,我想回爹老家王家坪去住。你去跟爹说说嘛,他肯定听你的。好吗。
这下,该幼兰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她是真不知道秀秀会有这样的想法,就问她,这儿不好好儿的,为啥要回去。
秀秀见幼兰心生疑惑,怕她不帮自己了,心一酸,又禁不住泪水直流。她摇了摇幼兰的双膝,望着她的眼睛,哀求她,姐,你答应要帮人家的。
幼兰还是那样温温和和的,微笑着,拿手拍了拍秀秀的后脑瓜子,耐心地答应道,帮,要帮。要咋个帮法嘛,妹儿,你总得多少给说出个道道来嘛。
秀秀再次鼓起勇气,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人家都是大人了,就没得哪个关心关心,我想成家。
幼兰脸上顿见阳光灿烂。她抚摸着秀秀,既欣赏,又高兴。夸赞她,成家啊,好事儿嘛。妹儿长大了,妹儿有出息了,晓得考虑自个儿终身大事啦。是哪家的儿娃子,真是有福气,有眼力哩,摊上你这么好个妹儿。
秀秀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对美好生活更是充满憧憬,再次要求,姐,你可要帮我啊。
幼兰被秀秀的情绪所感染,做母亲的幸福感让她一时感到很满足。她拿定主意要把事情完全弄明白,这才好帮这个自小没妈的娃娃,肯定地答应她,要帮,当然要帮的,你总得把话说清楚了,姐才好说咋个帮法。这儿不好好的吗,又没得哪个撵你们,咋个硬要回老家去呢。
秀秀明白,她和天祥在古城的做法虽然是情之所至,但不管是按族规,还是按礼法的要求都是说不过去的。尽管大姐对她真心好,还是担心她一时接受不了。那,大姐,可说啦,你要答应我,绝对不怄气噢。
妹儿的人生大事,姐高兴都来不及哩,怄哪门子气哟。说,姐不怄气,决不怄气的。幼兰的手在秀秀的头上轻轻地拍了拍,鼓励她把话说完。
秀秀受到鼓舞,打算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那,真说了。
真说。卖啥关子。真说,说。幼兰慈爱地再次轻轻地拍了拍秀秀的后脑瓜子。
大姐,我都说,不管哪样,中间你都别打岔。等到我说完了,你愿意咋样就咋样,我都愿一个人领受。秀秀望着幼兰,眼睛里透出坚定和决断。
说吧,姐不打岔就是了,妹儿说噢。幼兰表现出极大的耐心。
秀秀还未吭声儿,就又泪流满面了。她泪眼汪汪,望着幼兰的眼睛,掏根掏底地说出了她和天祥在古城的事情和她的全部想法。最后哭诉道,姐呀,我和天祥自幼在一起,吃你一个人的奶奶,睡你一个人的被窝窝。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虽为姑侄俩,实为一对儿。长大了,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妹儿早想好了,发誓这辈子谁也不嫁,就只嫁天祥。前次去古城进货,像是老天爷有意安排要成全我们。我们就在客栈里私定了终身,成了亲,完全是情之所至啊。
姐呀,你本不该是我姐呀,今生今世你就是我的妈。妈呀,女儿虽然不是你亲生的,但女儿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是你把我养大了,也是你教我如何做女人的。妈呀,忘不了哇,那些年里,女儿穿薄了,你最先晓得女儿冷,女儿吃少了,你最先晓得女儿饿。女儿脚丫儿踢烂了,你背我上茅房,女儿发高烧,你抱着我三天都没睡,没你的胸口暖着,女儿早已枯骨一堆了。
妈呀,你一直都那么疼女儿,爱女儿,一直都在帮女儿呀。没了你帮,女儿就成了没得藤藤的瓜儿,没得苗苗的花儿,就无依无靠,就长不大了呀。妈呀,你以前帮了我多少,女儿都记得清清楚楚,都记在心窝子里呀。但是,女儿还没长大呀,没成人呀,你还得帮我才行呀。就让天祥娶了我吧,噢。我是女儿,也是儿媳妇,噢。我孝敬你一辈子,供养你一辈子。我为你养老送终,为你披麻戴孝,妈噢。
秀秀一把鼻涕,一把泪,似长歌当哭,任何人听了都会动容,都会揪心。秀秀的哀怨,秀秀的期盼,秀秀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幼兰。她用手抚摸着秀秀的脑壳,哽咽无声,泪流似珠。她虽然待秀秀如同己出,但并不完全了解她的心思,认为她还是一个娃娃,并不懂得她的感情,一直看她说话叽叽喳喳,毫无城府,并不晓得她竟有如此的胆量胸怀。
妈呀,女儿想呀只有你去给爹说,回老王家去住。回去住了,我就是王家的人了。天祥本该姓丁,给王家当了胞儿子,也就没得哪个说闲话了。等过几年了,或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把你也接了去,住在一起了,我们供养你,孝敬你。你就带孙子,享清福。妈,好吧。你的孙子你说姓洪就姓洪,你说姓丁就姓丁,你说姓王就姓王。
妈呀,女儿晓得你也为难,你也不容易。在这人生关头,你得帮女儿呀,帮女儿完成终身大愿。找爹说说噢,妈。说到后面,秀秀不再哭泣,只是克制不住像开了闸的泪水,任由它恣意流淌。说完了,就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她摇了摇幼兰的大腿,泪眼矇眬地望着也正泪流不止的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