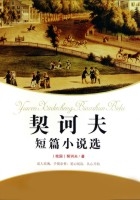大热的天气,正是太阳西晒的时候,在高大的柿子树荫里,桃桃蹬在坎上,天祥站在坎下,他们就那样相互望着看着。只不过才十几天,她觉得他似乎又变了许多,脸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更黑了些,透出一个成熟男人特有的气质。额头和脸上挂着汗珠子,鬓角也被汗水打湿了。过了好一会儿,桃桃好像忽然清醒过来了一样,忙喊天祥进屋喝水。
这天,桃桃好像特意打扮了一番似的,上身穿了一件阴丹布汗衫,下着一条青色的长裤。衣服也好像是特意量身定做的一样,很是合体。看得出来,她比秀秀高挑,身段显得更加丰满,曲线柔美,全身发散出浓浓的青春气息。
桃桃让天祥就在外面坐,屋子里太凉了,恐怕阴了汗,容易热伤风。家里备有黄酒,凉冰冰的,非常爽口。天祥也不用客气,一连灌下了两大碗,望着伸手接碗的桃桃,连声赞美到真是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桃桃心里甜甜的,笑容更加灿烂。她拿根小板凳挨着天祥坐下,总拿眼睛瞟着看着他,问他来去一路遇到的新鲜事儿。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真是太精彩了。除跟爷爷到过两河口外,她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她太想到外面去看看,哪怕是感受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也是值得兴奋的事。
桃桃问天祥坐船晕不晕,船上好不好耍。古城有多大,有几条街,像不像两河口镇,是石头街还是泥巴街,街上有多少人家,馆子里除了卖面,还卖些啥子。
桃桃只在两河口镇上吃过面。馆子里的面油多,面里加了肉丁丁,豆腐颗颗,还有葱蒜香菜。面只有一点点,数得过的几根儿,吃得快,几大口就吃完了,饱不了肚子,但是吃在嘴里软溜溜的,滑滋滋的,香喷喷的,舍不得往下咽,味道真是好得不得了。回家自己尝试着做了几次,同样放了肉丁丁,豆腐颗颗,放了葱蒜香菜,总也做不出那种味儿来。爷爷夸她长了心眼儿,有出息,见啥会啥,她却高兴不起来。
桃桃早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外面去看看别人是咋个做的,是咋个吃的,又是咋个耍的。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世道不太平,爷爷不让她一个人出门。天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从他嘴里讲出来的,都是新鲜事儿,都使人长记性,长见识。
眼看着太阳渐渐西斜,天祥见时间不早了,准备启程再赶一段路。他站起身,就要告辞。
桃桃哪里肯放他就走,她不顾女儿的羞涩,一把拽住天祥的左手,拉他坐下,干脆拥着他的胳膊,把下巴枕在他的肩上,几乎是对着他的耳朵说,不许走,不许走,就是不许走。
天祥只和秀秀像这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他脸颊上感受到了桃桃说话时喷出的热气。他不敢侧过脸去,他知道只要稍稍侧过去一点点,他们的脸就会叠加在一起。他的胳膊深陷于她的乳沟,他不敢动一动,他也知道只要稍稍一动,对一个纯情的女子就是一种侵犯。
大热的天气,他们都穿得很单薄,彼此感受着对方的体温。天祥感到特别地压抑,从未有过的那种压抑,犹如火山爆发前,岩浆奔突,又一时找不到喷发的口子,它那无穷的力量可以冲破任何一处岩石,行将毁灭大片的森林和树木,毁灭一切绿色。
就在这时,他的眼前有一个影子在不停地晃动着,一个正在给娃娃喂奶的年轻女子的身影,那是秀秀的影子。他抬眼望去,院坝坎下的那棵柿子树枝繁叶茂,它身后山山岭岭的青杠树,水橡子树,白杨树,桦子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不知名的树木,它们拥在一起,各显风姿,更是绿意盎然。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爱意。它给人以安详,看见绿色就让人感到宁静。天祥尽量把声音放得缓和一些,告诉她,我实在是忙,今天哩确实还打算赶一段路的,等下次时间宽余了,有得空了再来看你,好不好,桃桃。
不好,不好,一点也不好。她又把他往怀里拉了拉,身子贴得更紧了些。反正不准走,就不准走。她仍然撒着娇。
他不再感到燥热,显得很是平静,有意把桃桃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桃桃,你听,你听,你们家的鸡咯咯在叫,去看看是不是下蛋了。
鸡下蛋有啥子好看的,爱下就多下几个。桃桃仍不愿松开他那只拥在她怀里的手臂。
你看,黑蛮子看我们挨得这么近,它是不是不高兴啦。天祥呶了呶嘴,向桃桃示意。
黑蛮子确实正好奇地望着他们。
咯咯咯,她的笑声很清脆,也很甜美,她说黑蛮子乖得很,比人强,最听话了,晓得人的心,不像有些人,才十几天就把人给忘了,没良心。
桃桃,你听,有脚步声响,正在往你们家走,要来客人了。天祥进一步转移桃桃的注意力。
桃桃凭她的生活经验判断,黑蛮子的耳朵比你强十倍,它不咬不叫,就没得人会来。
天祥想用爷爷的权威让她松开手,真的,快去看看,是不是爷爷回来了,爷爷看到会骂我们的。
回来更好了。爷爷才不会管哩。爷爷也喜欢你的,是真的。就要叫爷爷晓得是我们在一起。就不许你走,就要你陪着我。桃桃仍然不肯松一松手。
他的脸颊被桃桃呼吸喷出的热气撩得痒酥酥的。他不能侧一侧脸,只能平视着前方。为了使气氛更加轻松一些,他有意说笑,那好吧,就陪着你,就不走了,给你们家当长工,当你们家的嗯嗯那个。本来,他要说当胞儿子的,一时又感到说漏了嘴,就来了个脑筋急转弯,用那个代替了胞儿子。
桃桃已经听出了他的意思,就紧追不放,你说清楚点,到底当我们家的啥子嘛,说嘛,说嘛,你说嘛。她使劲又把他往怀里拉了拉,似乎是动作太大了一点儿,鼻尖和嘴唇好像已经无意间碰着了他已经火辣辣的脸。
触动只是轻轻的,好像轻风拂面,只要用心去感受,同样会留下深深的印迹,如同导线的两极,只将它们轻轻一碰,同样会产生耀眼的火花。
天祥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尽量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对她说,桃桃,松开手嘛,松开手,我有正经话跟你说噢。同时拿右手去拂她紧抱胳膊的手。不料,一伸手触摸到的却是她右侧高高突起的那只玉乳。尽管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他显得很是尴尬,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放在膝盖上,但对一个真情萌动的青春少女而言,产生的却是惊心动魄的震撼。
桃桃从记事起,除偶尔在爷爷面前撒撒娇以外,在别的男性面前总显得特别的局促,未曾开口,脸就烫得火辣辣的,更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有过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如金似玉的双乳,她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着,哪怕是自己脱衣解扣时,偶尔不小心碰着了,她都要自责,拍打自己的手,才原谅自己的粗疏。就他这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好像电流对一个可控硅元件的一激,它唤醒了一个成熟女性还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下的一种情愫,它成为一种召唤,促成了一个怀春少女的一次觉醒,它又像黑夜里一盏明明亮亮的灯,引领着她走向了人生最神圣的殿堂,走向幸福,使她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
21
滔滔清水河,凭借自然的伟力,切开一山又一山,割断一岭又一岭,形成了一道接一道的深沟峡谷。清水河一路向东,而到了两河口,则来了一个大转弯,陡然折向东北流去,十多公里后,回还东南,继续东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河曲。河水对迎水面不断冲刷侵蚀,背水面则不断沉积堆砌,再加上两条河的自然作用,阻滞了大量泥沙。天长日久,就在河曲的背水面,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形成了一大片平整开阔的冲积台地。
两河口场镇正处于两条河的交汇点上。镇子何年形成,已无从考证。从街道上,人踩马踏在青石板上留下的印迹判断,至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古有景谷道与金牛道相接,是蜀地通往大西北的一条重要通道。应该说两河口镇与景谷道相伴而生,景谷道已成历史的回忆,两河口镇则生生不息,繁荣至今。自古以来,扼水陆要道的两河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胡宗南就派丁德隆部的一个加强连驻守在这里。
两河口地处要津,但自古至今只是一个集镇,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官府并未在此设置过府州县治。没有高高的城墙,更没有坚固的城池。主街临河,俗称外河街。外河街修建在河岸的岩石上,街面作铺面,铺面后的房子多是临空的吊脚楼。多数人家的生活废水直接排放,生活垃圾直接倾倒。吊脚楼下污水长流,垃圾成堆。每到夏天,蚊蝇猖獗,臭气熏天。
集镇还有几条支街,街道较窄,街房高的高,矮的矮,多是全木结构。集镇不大,戏园则不小,一次可容数百人听戏看戏。戏园为商家集资修建,如不演戏,平时一般都是闲着。与戏园相对的就高升饭店。高升饭店是全镇最好的建筑,门高面阔,街房整齐。这里成为全镇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有药铺,有饭店,也有烟馆,补锅的,修鞋的,磨刀的,理发的,长年累月占据各自的地盘,经营自己的手艺。
两河口的居民有本地人,多数则是外地的客商。有的今年来,明年走,有的租赁铺面三年五载坐地经营。一些小商小贩来去更加自由。大户人家可在街上置产兴业,但一般不住街上,都情愿在地坝里圈地造屋,一套接一套的天井,都修有高大的围墙,设置了威严的门楼。
张啸虎从一个小混混经过几十年的搜刮,巧取豪夺,建了几套天井。这些天井各自独立,通过上下走廊相衔接,高大的围墙又将几套天井围成了一座独立于其它建筑的庄园,自成体系,门楼高大气派。
丁德隆的部队虽属正规的国防军,服装统一,装备也比较新式,但部队素质比田颂尧的川军实在也好不了多少。照样抽大烟,照样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镇上店铺家家都有赊账,乡下人家户户都遭到过强拿抢掠,搞得民怨沸腾。人们见了这些当兵的,就像见到了瘟神,唯恐躲避不及。
张啸虎让丁德隆的部队驻在他的两套院子里,经常同那些军官在一起喝酒赌博,得到了不少的好处,捞到了不少的油水,特别重要的是弄到了一批新式的长枪短枪,重新装备了他的保安队,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三姨太被驻军连长霸占,戴了绿帽子,他得好处在先,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摸清敌情,详细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教导员和木匠排长分别带着一组人到两河口进行实地侦察。教导员一袭长衫,皮鞋,打扮成一个商人模样,天祥还是老本行,背着背篮,带上拨浪鼓,继续做他的货郎。
仲春时节,山里气候还不见明显的变化。越向下,海拔越低,气温越高。山上,樱桃花蕾还包裹得严严实实,半山腰以下,就已经完全绽放,桃花红,梨花白,清水河边,柳絮纷飞,新芽已经满满地挂上了枝头。
时近中午,他们一行人先先后后来到了两河口。按事先的分工,分头扮演各自的角色,前往丁德隆部队的驻地。
张啸虎的庄园坐落在两河口坝子靠里边的一块平地上,距离两河口镇约有两三里路程。这里地势相对比两河口镇高一些,右后面是一条半环的小山梁。山梁坡度平缓,都是耕地,麦苗长势正旺,油菜则已经繁花似锦。前面就是两河口大坝子,一直延伸到河岸边。大块大块的麦田里镶嵌着一块块黄澄澄的油菜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
按照教导员的安排,天祥还是干他原来的老本行,穿货郎衣,干货郎事,背着背篮送货上门。庄园大门有卫兵把守,端着枪厉声呵斥他站住。两个卫兵黄色衣裤,穿戴整齐,帽子上的青天白日星特别扎人眼睛。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说明兵是不讲道理的。兵对秀才不讲理,对老百姓更不用讲道理,只拿枪杆子说话。这些兵在两军对垒时向敌人猛烈开火理所当然,拿枪杆子吓唬老百姓,对老百姓开枪也是常有的事。老百姓晓得这些兵不认人,会干出不是人的事情,那些枪杆子更没长眼睛,他们怕兵,也怕枪杆子。天祥才不怕这些兵,恨恨地想,你龟儿子莫神气,不出明天,就会成为老子的俘虏,到时候看老子咋收拾你。
天祥赶紧停住脚步,做出一副惊慌的样子,舌头似乎变得又大又笨,说不清楚话,还有些结巴,战战惊惊地上前给两个卫兵说,兵大爷,乡下人没见过枪,怪吓人的,害怕得很,能不能收一收哇。卫兵晃了晃手中的枪,还是用枪管指着他,样子凶巴巴的,不准他再往前走一步。
天祥对卫兵说,三姨太上次要的花线给带来了,这就送过去,可不可以,要不就麻烦两位兵大爷给通报通报。卫兵很不友好地回敬他,老子才懒爱得管你妈那些起码子事,要去就自个儿去。
天祥漫不经意地笑着告诉卫兵,三姨太对人可好啦,人也长得特别标致,是不是啊。
其中一个卫兵把枪管放得低了些,凑过头来,声音放得低了些跟他开玩笑,对他说,标致的是条老母狗,骚你妈得很,你杂种有胆子就日嗒里面莫出来,活脱脱你妈个瓜娃子。
天祥也不生气,嘻嘻笑着,好像是在抱怨那个卫兵不该骂人,你兵大爷骂人,我去给三姨太日个白,扯个谎,叫她晚上把你收拾安逸。边说边就进了大门。
庄园的大门处于五套天井的正中,通过高大宽敞的门廊,直达中间最大的那套天井。
庄园是几个天井构成的,五套天井一字儿排开,上房走廊和下房走廊贯穿五套天井,将五套天井结为一体。五套天井中,中间一套的上房下房分别多两间耳房,呈长方形,一共是二十间房,除了门楼,有十九道明门。
一般一套天井都有四间堂屋,正房的堂屋叫中堂屋,或大堂屋,下房和厢房的堂屋通称小堂屋。不管是大堂屋,还是小堂屋,与其它房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门上,堂屋的门都是对开的双扇门,中堂屋还是四扇门。堂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都没有楼,一眼望上去,就直接看到檩子椽子和青瓦。一套天井里,除中堂屋外,其余房间都可以安床住人,小堂屋一般作客房,只允许男性客人住宿,女人是不能在堂屋里住宿的。
紧挨堂屋的是耳房,称小耳间,一般都设有通向堂屋的侧门,叫幺门子。大堂屋右侧边的小耳间一般都由一家之主居住。如果男主人有几房妻室,大房也叫正房,就是最先娶的那个妻子就应该居住在这间房里,后面陆续娶进门的姨太太就安排到其它小耳间里居住。
张啸虎庄园大天井以外的四套天井都呈正方形。第一套天井上下左右都是三间房,加上四间转角有十六间房,有十四道明门,还有两道门被中间厢房挡住了。第二套天井则只能算有上房下房,共三二六间房。
天祥顺着走廊到了左边天井。这里就是丁德隆部队的驻地。两套天井共计二十二间房住得满满的,到处都是军人。张啸虎的三姨太和敌军官住在最左边天井里的小耳间里。每天吃了饭不消化,就和一群男人们混在一起搓麻将。
那些长时间尝不到荤腥的男人们,馋得像小猫,只要连长没有在桌子旁,总要找机会趁摸麻将时,顺便摸一下三姨太肉嘟嘟的胖手背,或用脚勾一下她肥嘟嘟的小腿。谁摸了手,三姨太就顺势在那人的手背上狠狠地拍一巴掌,谁勾了腿,她就顺势狠狠地踹那人一脚,嘴里还要带骂一连串的脏话。桌子上的人谁都乐意挨打受骂,把钱输给了三姨太当然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