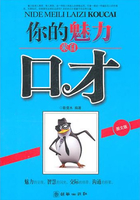“没有啦,‘你在我心中是最美’。”典范说着小声清唱了一句,问:“对了,你说翻这个收在我的新专辑里怎么样?”
“不要!你红的时候他们还在酒吧驻唱!”吴菲调侃。
“对哦,我红的时候还不知道‘刀螂’原来不止是一种昆虫的名字呢——嗌?你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不红了吗?”
典范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趣,追问了一下午,不依不饶的。
没多久,“观邸99”交屋,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吴菲选了一个周末搬家。
临出社区门的时候,吴菲又看见杨小宁在草坪上逗孩子,跟她搬进来时看到的情景别无二致,只是这一次杨小宁身边没有孩子他妈,而他则奇怪地戴了个方型的墨镜。
吴菲看着那情景不禁微笑,她想了想,让吴宪跟着搬家公司的车先走,她把自己的车在草坪边停好,向着她的初恋走过去。
她在跟他距离大约七米的地方停下来,歪着头看他。她脑海中又出现她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向她走来,带着他的“招牌微笑”,就像他此刻对着他的小孩微笑的一样。
吴菲在那儿站了将近十分钟之后,杨小宁才终于发现了她的存在。他就在原地站起来,搓了搓手,也冲她微笑。
吴菲确定这一次他们两个人都互相清楚地看到了对方。没等杨小宁有别的反应,吴菲就冲他笑着大声说:“我搬家,刚好路过这儿看见你,就想着,总该跟你打个招呼!对了,你戴这个墨镜挺好看的,猛然一看,我还以为王家卫跟咱院儿里逗孩子呢!”
说完轻快地转身走了,留下杨小宁五官抽搐着伫立在艳阳下,无言地手里牵着他的孩子……
也像王家卫电影一样,此时无声胜有声,所以悲欢着各自的悲欢,结局了各自的结局。
吴菲知道,这一次,终于是她和他的永诀,她等这一刻的来临,等了十年。
她心里唯一纳罕的是,为什么是在莫喜伦的事情彻底了结之后,杨小宁才也能跟着一起消失在内心的尽头了。从此,她不再为他留给的记忆而颠沛,也不会继续受控于他留给她的,他们谁都说不出名目的挫折与忧伤。
吴菲在那天之后跟那个叫龙与成的销售果真来往频密起来,她也说不上到底当他是什么人,也许,像那个摇滚乐手Bon Jovi说的:“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
龙与成不做销售的时候,是个业余诗人——没有任何作品发表仍坚持创作的那种诗人。
“你知道,我觉得人的本性里面,天生下来就会四件事:游泳,吟诗,喝酒和跳舞。这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事情,后来大多人不会,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教育的束缚。”
与成不是说说而已,这四件事是他的最强项,很明显做起来比当销售更得心应手。吴菲因此跟他见面都是听他的安排,与成似乎也很乐意当吴菲的领袖,他教她游泳,她听他吟诗,他们喝酒,跳舞。
跟龙与成在一起,吴菲觉得自己简直不算年轻过。他每次都会给她新鲜的感觉,他带她跟不同的陌生人一起狂欢,不问姓氏,不管出处,也不受任何利益的支使,玩儿的无拘无束。
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次见面都喝酒,每喝必醉,趁着醉意再解决别的饥荒,没有了自控的枷锁,很原真超自然的体验。
“人生最快乐的事是喝酒和做爱。”诗人龙与成如是说。
“是啊,可惜多数时候你们男的只能同时选其中一件!”
“怎么说?”
“不是说很多男人喝酒之后就不能做爱了吗?”吴菲笑道。
“也有像我这样的天才啊!”龙与成说。
他有时确是个天才,他让吴菲觉得,世界原来还有这样的一隅,在里面,有纯粹的快乐。她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种全新的力量:年轻、单纯。这些力量出现在吴菲生命的此时此刻,令她无比感激,却又没有任何多余的负累。
等到熟悉一些的时候,龙与成也会跟吴菲讲他自己的身世,讲刚到北京那两年的一段颠沛,也讲家庭不睦。
“我妈除了对连续剧热情之外,对其他的一切都特冷漠,我爸正好相反,他是对一切都很热情,除了对我和我妈特冷漠!”
这话令吴菲想到她和吴宪,她因此对与成顿生怜爱之心,不禁叹道:“唉,有时候想想看,我比你大将近八岁,你比我弟还小呢。”
“怎么忽然想起说这个?”龙与成笑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嗨,这年头,谁容易啊!”
“哎,这么着吧!”吴菲凑近与成说:“以后,甭管你需要什么帮助,记着,你都有我呢!”
“我什么都不需要。真的。”龙与成说,收起笑容看着吴菲。
“可是我需要啊!”吴菲笑,眯起眼睛,一边把头歪在与成肩膀上,柔声道:“你知道吗,现在啊,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高兴,你就是我命里的天魔星,你要不让我对你好点儿啊,我还真觉得有点儿欠你的!”
龙与成把手环在吴菲背上轻轻揉着,玩笑道:“您这么客气干吗?我也没对您做什么!”
吴菲挣脱了笑道:“这还叫‘没做什么’?那什么叫‘做了什么’!”
“不过,说真的,我是挺怕别人说要对我好的。”与成咳了一下,点了一支烟递给吴菲。
“为什么?”吴菲接过烟吸了一口,问。
“大概,呵呵,我不想爱上谁吧。”龙与成若有所思道。
“为什么?”吴菲又问。
“就是不想,没有为什么。”龙与成想了想又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会以爱之名要挟你,这样那样的。前阵子我认识一女孩,也没怎么着,有一天她忽然特哀怨地跟我说,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碰见比她对我更好的人。我一听,头皮立刻就麻了!”
“呵呵,”吴菲笑笑,问:“那她对你是怎么个好法”。
“怎么个好法,嗯……”与成给自己也点上烟,抽了一口,在面前挥了挥把烟赶开,说:“好像也没怎么,就是……她每天都给我发短信,嘘寒问暖,逢年过节还送我礼物,让快递送到我上班的地方,弄得项目的人都嘲笑我,呵呵。而且,每次我们见面,她都特哀怨,回回欲言又止,老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就跟我快死了似的。”
“那她肯定是爱上你啦,多可怜啊!你还这么说人家!”吴菲笑道。
“可她非要爱上我,这也不能赖我呀!”
“那你呢?你爱她吗?”
“嗯……我,还不讨厌她。”与成说。
“那就是不爱喽!那你为什么还要见她?”吴菲问。
“我不知道,有时候觉得她也挺可怜的,她说只要见着我就高兴。我一想,让她见见我,我也没什么损失,如果这点都做不到,那我也太不是人了。”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最有用的‘长久之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估计过一阵子她自己就好了。现在这年头,哪还有什么长久!”龙与成继续道:“我就是觉得吧,有时候女的都挺自以为是的,以各种方式自以为是。比如这女孩,她总在说她自己如何如何喜欢我,可是她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别说了解,其实我们俩连认识也算不上。”
“那是你的问题啊,你根本没给人家机会了解你。”
“了解不需要‘机会’,只需要‘智慧’。”与成说:“嗨,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就是特见不得女孩哀怨,也很怕别人说喜欢我啦,要对我好啊之类的这种话。我……可能我在那种家庭里长大,已经习惯没人对我好了,所以,我有点抗拒别人对我好,尤其是陌生女人。在我人生的经验中,‘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让自己觉得自己负心,时间长了,觉得自己挺混蛋的;另一种呢,我其实觉得,好多女人老爱打着对你好的幌子,说白了,也就是想霸占你,霸占就霸占呗,弄得还跟献身了似的!你说,什么叫好?咱凭良心说,一男的跟一女的睡了,到底谁吃亏谁占便宜?唉,当男的未免他妈的太倒霉了!”
吴菲听完,把烟掐灭,低头很仔细地把落在衣角上的一粒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烟灰仔细地掸掉,然后笑说:“呦,那你可得把自己看好了,你这么才貌双全,当心被我占了便宜!”
“嗨!咱俩谁跟谁呀!再说,你跟别人不一样!”龙与成看着吴菲笑。
“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为了扎堆儿吃然后一起睡!”
“这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龙与成注视着吴菲的眼睛说:“你会承认,你什么时候都不伪装,有什么说什么。”
吴菲也回看他,两个人又奇怪地一起大笑了两声。笑完,吴菲忽然凑近了搂住与成的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你带我走吧,咱喝酒去,然后,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想干吗咱就干吗。”
“你想还是我想?”龙与成也小声的回问。
“都这日子口了,还分什么你我?还不都一样?”吴菲笑,然后她放开他,他们又很深地对视了十三秒,在那十三秒里,他们仿佛彼此看穿,只这么一眼,只在那一刻,让他们意外地拥有足够的了解,了解到足够他们在一处厮继续混个一年半载,不用再有任何多余的迂回或解说。
等“观邸99”卖完之后,吴菲休年假,就和龙与成去了东南亚的一个岛上休假。
那天下午,之后,龙与成起身,先只穿上牛仔裤,走过去拉开对着海景的阳台门,饭店外的沙滩和海浪声赫然冲进来。
吴菲蜷在床单里,伸出手按了一下遥控,空气里顿时飘出与成带来唱片,是张国荣不朽的沙哑嗓音唱出来的“怪你过分美丽”。吴菲满足地伸了个懒腰,叹了口气说“这首歌真是性感啊!”
“性感?比我呢?”与成走过来在吴菲脸上轻轻掐了一下,边走到梳妆台的镜子边上,边感叹:“你这样好多了!”
“什么?”
“你现在的样子……很女人。”
“怎么讲?”
“没什么……”
“讨厌,就烦人说话说一半儿!”吴菲笑着说,然后伸手点了一支烟,斜靠在床边看与成梳头。
“我就喜欢看男孩子梳个小马尾!”吴菲由衷地叹道,“我弟就是头发太少,我要是将来有个儿子,也给他搞成这样。”
“你觉得你儿子会像我吗?”龙与成梳完辫子,回过头问吴菲,一边使劲举着手臂看自己的二头肌。
“我儿子要是像你这样,早被我打扁了!哈哈哈。”吴菲笑着弹了弹烟蒂。
“那你会打我吗?”与成走过来,坐在床沿,伸手摸了摸吴菲的发际。
“滚!”吴菲娇嗔地把与成的手挡开“我最受不了别人摸我头发,我前夫当时就是靠这一招骗了我,我觉得这他妈比摸哪儿都性感!”
“那,你会不会很容易爱上发型师啊!”
“这倒没有,我觉得发型师跟大夫似的,自带绝缘体。而且我一般都找‘同志’给我弄头发。”吴菲边说边侧着身伸手从沙发上的一堆衣服底下抽出一个纸袋,对与成说:“哎,你试试这件。”
与成接过那件纸袋,从里面掏出一件黑色的衬衫,他举着衬衫看了看,问:“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吃午饭之前啊,你非要健身,我闲着无聊,就去购物喽!”
“我服了!这么点儿功夫你都能购物啊?你不是说去SPA吗?”
“我才不要自己SPA呢,要去就一起去!”
“好啊,那一会就去。”与成挨着吴菲坐下,想了想又说,“不过,以后别买衣服给我了,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
“那你早不说!”吴菲笑道。
“以前跟你不熟啊。”与成也笑。
“都上床一百次了,还说不熟?”
“熟不熟跟上多少回床没关系吧——有一百?太夸张了吧。”
“你们男的不都好(四声)个夸张吗?”
“我无所谓,呵呵,对自己这点信心还是有的!”与成道“反正以后别买了。”
“你就当我有心理问题吧,呵呵——我可能真的有心理问题,我只要一上街就想给‘我的’男人买东西。以前给我弟买,给老公买。现在,老公让我给甩了,我弟穿别的女的买的衣服了,我就只能给你买喽!”
“那,像我这样,要是在老上海,是不是就叫‘拆白党’啊?”
“哈哈,你呀,你是该拆没拆成的那种!”吴菲被龙与成的话逗笑了,“别废话了,快穿给我看看。”
“不穿了,省得一会儿又脱,你给我买的衣服都挺合适的,不试都知道。你老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我要是习惯了,离不开你了怎么办?”
龙与成说完站起来把衬衫挂进衣柜。
“那就将计就计呗”吴菲仍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微笑。
“怎么个就计法?这样?”与成走过来把吴菲抱起来,两个人循序渐进,来了一个长久的湿吻。
“我不行了。”吴菲吻完把头埋在与成胸前笑说:“我上年纪的人,每次之间得间隔俩小时养精蓄锐。”
“你好色啊你!想什么呢?我就打算抱抱你而已,没打算干别的!”与成说着把吴菲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用床单把她裹了裹,从床上抱起来,放在阳台上的躺椅里。他自己走回房间,从冰箱里拿了两个椰青回来,其中一个帮吴菲插好吸管递给她,自己坐在旁边的另一张躺椅上。
两个人都面对着远处的海岸线发呆。
龙与成喝了两口忽然问:“你相信有上帝吗?”
“好好的怎么想起上帝来了?”吴菲反问。
“你说,我这么帅,你这么美,这儿的海这么蓝,椰青这么甜,跟假的一样!”
“哎呦,您这是,又作诗呢?”
“没,我认真的,你说,如果没上帝,这都怎么来的啊?”
“呵呵,是啊!”吴菲很受用,一边吸椰青一边闲闲地说:“不过,如果真有上帝,上帝肯定也挺郁闷的。”
“怎么说?”
“你想啊,上帝给人制造了这么美的条件,结果人跟这儿,都不干好事!”
“怎么没干好事?”
“比如你我,咱俩在一起的这点儿事儿,这要在《圣经》里,那它就是个‘罪’。”
“上帝不会这么计较吧,如果这都叫‘罪’,那怎么才不叫‘罪’呢?”
“可能,如果有了‘爱’,了,它就不应该是‘罪’了。”
龙与成不语,看吴菲眯着眼睛,就起身从茶几上拿起个墨镜递给她。
吴菲戴上墨镜继续笑道:“不过说真的,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爱’的。只有爱才有那种让人想要认清自己的折磨。很久没有那么被折磨了,感觉还挺‘饥渴’的!”
“‘饥渴’?我除了对性和酒,对其他的怎么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龙与成笑道。
吴菲没理会与成的笑话,继续自己的话题道:“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愿意相信爱,大概,至少说明我的心还没有全死吧。”
“到底是女人啊!呵呵。”龙与成回头看吴菲,笑笑。
“讨厌,期待爱很可笑吗?干吗笑?”
“不知道,就是想笑。”
“那说说你吧,你呢?你就完全不想爱?”
“不知道,也懒得想,我倒没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再说,今年是我本命年,过了再说吧,人家说了,本命年的时候不宜改变自己。”
“靠,你还敢在我面前提什么本命年!我再过个本命年就奔四喽!太可怕了!不过从今天起我要忘记年龄,省得你小子提前嫌弃我,呵呵。”
“哎,”与成又转脸看着吴菲,认真地说:“不过,有一点我确信,你甭管到什么时候,都还是会让自己保持美丽的。”
“谢谢,借您吉言!”吴菲笑,又说:“那除了爱呢?还有什么是你打算过了本命年才考虑的?”
“你指什么?”
“比如,嗯……理想啊什么的,对呀!你说,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也没个理想啊?”
“有啊,怎么没有。”
“那你说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嘛……”龙与成站起来把喝完的两个椰青丢进垃圾袋,转身对着那海天一色大声道:“我宣布,我龙与成的理想就是,等吴菲老了,我每星期都去敬老院看她一回,她吃饭我给她夹菜,她喝酒我给她拎着瓶子!”
说完转回身坐下,扭头问吴菲:“您看这理想靠谱吗?”。
“放屁!”吴菲听了大笑。
不远处海浪的声音一卷一卷拨过来,屋里的CD兀自响着,隐约,在唱“如果我还有哀伤,让风吹散它,如果我还有快乐,也许吧……”。
吴菲惬意地翻了个身,背对着与成倦成一团,不知不觉在海浪声中昏睡过去,似梦非梦之间,吴菲恍惚听见与成的声音在背后叫她的名字,那声音似乎有些异样,但吴菲还没顾上听个真切,那声音就忽然遥远了。
吴菲梦见自己随着海水飞起来之前,似乎有一滴眼泪从她的墨镜后面的眼眶中摇摇欲坠,但,还没来得及滚落,也很快就被海水冲散,跟着其它无数来路不明的眼泪汇集在一起,被带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吴菲看着水中的自己,微笑起来,虽然有些些纳闷,但很塌实,她听到有一个声音在云端隆隆的响着: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