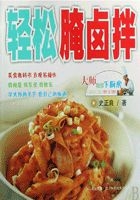“妈!我们下不下种呢?”
“不下种?吃什么东西?吃泥土吗?”
“我是说的谷种钱啦!”宝宗显出非常困难的样子。
“我总得想办法的!”
丁娘,从床底下,打开着一口破旧的衣箱,很郑重地取出一个纸包子来,打开给宝宗看:
“这是我的一只银手镯,那是你小时候带的颈圈,两样,到城里去总该可以换三四元钱吧!……当心些!妈收的真苦啊!要不是自己种田买种谷……。”
“唔!”
宝宗的喉咙象哽了一块石子。将纸包插在怀中,飞步地向城中赶了去。
下午,在宝宗还没有回来的当儿,团防局的团丁拖了一大串人犯光临到丁娘的茅棚子里来了:
“这里是姓丁吗?”
“是的!……”丁娘定神一看,险些儿没有吓倒。“什,什么?老,老总爷爷!”
“丁桂生名下,预征四十七年田赋一两,正税附加共六十一元九角,除正税六元须即日缴纳外,附加概限在四月底缴齐!”
“怎,怎么的?”
“粮饷?!”一个晦气色的团丁,将眼瞪得酒杯那么大。
“饭,饭都没有吃的啦!”
“没有吗?赶快叫出你的儿子来!……”
“他,他不在家了!……”
“混账?!”
团丁们,刚刚要亲自动手,搜查这小茅棚子的时候,宝宗恰巧从外面赶回来了。
妈,什么事情啦!……
话没有说完,团丁们便一把将他拖着。结果:人没有被带到县城去,而辛辛苦苦用银器换来的五元钱,却被当做四十七年的饷银征去了。临走,还被捉去了一只大雄鸡,算是补充正税的不足。
“天啦!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呀!……”
“有什么办法呢?妈!只要有人在……。”
噙着眼泪,惨痛地凝视着心爱的儿子,丁娘,只得勉强地装起笑脸来,重新地来计划着如何才能够在一两天内捞到两三石种谷。不下种,母子们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啊!
“那么,你就把田契拿到黄爹爹家里去看看吧!只要能够捞到两三担种谷钱!……”
“好的!”
当宝宗怀着田契走出去的时候,丁娘又过细地打算了一番:无论怎么样,种子是不能不泡的。假如黄爹爹不肯的话,她还得想其他的办法呢!
入夜,宝宗回来了,哭丧脸地摇了一摇头。
“怎么?黄爹爹不肯吗?”
“答是答应的,他要到五天以后。”
“还来得及吗?”
“迟谷!‘红毛须’,还可以。他,他答应了替我们送来。”
“那我们就种‘红毛须’吧。”
虽然谷子还没到手,丁娘的心总算是已经安定了许多,至少,已经有了着落。
一天、两天……第四天是谷雨。因为种谷仍旧还在人家手里,丁娘的心中总不免感觉到有些焦灼。一焦灼,便什么事情都糟了糕,团防局里又派了一大排团丁下乡来了,这回的名目可不再是什么征田赋,而是干脆地要捐给他们自己。
在无可奈何之中,宝宗也只得和其他的人一样,被团丁用绳子牵了去,等丁娘将黄爹爹处借来的种谷卖掉时,宝宗已经足足地关了七天了。
“妈!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啊。谷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全村的人,除黄家以外,没有一家曾下过种谷的,我们种什么呢?”
“命苦!什么都是不能种的,听天由命吧!……”
丁娘望着门外那一遍荒芜的田野,心中一酸,眼泪象雨一般地滚着。目前美满的梦幻,已经给事实打得稀烂了。未来的生活全是那样渺茫的,甚至于毫无着落,她的心房,象给什么人挖去了一块。要不是怕儿子过份的悲哀哟!她简直就想这么放声地大哭一阵。
“天,天哪!你为什么专寻我们寡妇孤儿来作对呢?”
三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沧水铺,大渡口,许多地方,没有谷下种的田,通通改种了鸦片烟了。邓石桥,有很多在发起种,恐马上就会要实行起来。
“鸦片烟?那是害人的东西呀!不犯法吗?”
“犯法?还是团防局里吩咐种的啊!”
“为什么呢!”
“种鸦片烟赚钱啦。”
丁娘,她是一个恨鸦片烟的人,她虽然没有见过那个捞什子东西,但她听见人家讲过。那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吃着会有瘾,会令人瘦得同骷髅一样的,而且,吃了这东西,便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她不懂,为什么人家都欢喜吃它,为什么团防局里还要叫大家都种。
“你也打算种吗?三胡髭。”
“怎么不种啊!至少一块钱一两,赚钱呀!你呢?”
“罪过哟!我是不种的。”
“不种?没那样傻的人哟!”
三胡髭便眯着那双老鼠眼睛,朝丁娘手舞足蹈地乱说起来。
“至少,一亩田,得收六十两,一块钱一两,就有六十块呀!……”
“六十块!”
“对啦!六十块,一亩六十,十亩六百,你家里十六亩,六六三百六,就有一千来块啦!”
“啊唷!”
丁娘险些儿吓了一跳。一千块她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数目儿。她不相信鸦片烟能有这样好。
三胡髭的话有些儿象是真的;但,又有些儿象是说谎,她可没有方法能决定。
“好吧!等大家都种了再说吧。”三胡髭常常来游说的时候,她总是拿这么一句话儿来回答他。
宝宗,那孩子,的确有些使丁娘着急。不知道是怎么的,自从在县城里关了那回以后,就象有些变了模样儿似的。丁娘,她是时时刻刻地在关心着。她什么都得靠儿子,什么事情都得和儿子商量,她看儿子有什么不安时,她总得问个明明白白:
“你在想些什么呢?”
“妈!我想去年陈老三他们那些人啊!”
“想他们?做什么呢?”
“妈,去年,他们不缴租,他们是有些儿道理啊。要是我们今年同他们一样,不缴捐款,我们不是都已经泡了种吗?”
“狗屁!陈老三,枪毙了呀!不许你乱想!”
“还有柳麻子他们,还正在罗罗山呢。”
“狗屁!……”
丁娘的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她想不到这孩子竟会变到这样糊里糊涂起来了。她怕他真的要弄出来什么乱子,她总是寸步不离在他的左右跟随着。一直到全村子里的人,都开始播种烟苗以后。
烟苗,是团防局里散发下来的,将来收下来时,每亩田,应当归还团防局十两,算是苗费。丁娘,她本是不打算种的,后来是看见大家都种了,又禁不住三胡髭那么说得天花乱坠地左劝右劝,她才下着那最后的决心。
种下来,就象蔬菜萌芽一样,很快地便蓬勃了,随着南风而逐渐地高长起来。不到几天,满村全是一片翠绿,正象禾苗张着苞的全盛时代,怪好看的。
人们的心中,又都随着烟苗的高长,而掀起着各种不同的变化。象三胡髭那样的人他的计划是非常周到的。他差不多逢人就说:他这回一定要发财了。他有七亩田,他的烟比别人家的都种得好,一亩田,至少有七十多两东西好收。七七四百九,五百块钱稳拿。他发财了啦,他可以做几身好的衣服。他今年四十岁,他得那个,那个,他从来没有讨过老婆,他要吃得好一点……。
“是吗?我说,丁家嫂!我总得快活一下子啦。四十岁了,四十岁了,难得今年天照应……。”
“好啊!”
一次又一次的熏陶,将毫不把烟苗放在心上的丁娘,也说得有些儿摇摇欲动了。
“真有那样的事情吗?”她想。“三胡髭说得那么认真的,要是真能够收七十两东西,我,我也得发财啦!……”
她真有点儿不相信。事实却又明明白白地摆在她的面前。那田野,那绿绿的东西!只要开花,结桃子……不就是三胡髭所说的那样的世界到了吗?这,实在不能说三胡髭的是鬼话。真的呀……
于是,丁娘,也便暗暗地在她自己的心中盘算起来了:还债,修房子,讨个媳妇儿,一家人过着安闲的日脚!……因此,她每天都在向人家学习!什么时候能划桃子,什么时候收浆,收了浆,怎样地去晒土!……
一切都学好了,都准备好了,丁娘的希望也一天天的坚实起来了。只有宝宗,他一个人不同,他总觉得这事情不大那个,不大象有希望似的。他常常劝他的妈不要妄想,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恐怕还有什么花样跟在后面呢。……可是,丁娘不相信,她总觉得宝宗是吃了什么人的迷魂汤,说疯话,她得看守他,不许他跟任何人跑出去。
日子过得真快,全村的罂粟花,都露出了水红色的面孔。一朵一朵的,象人们怒放着的心花一样。衬在绿叶儿的上面,是多么鲜艳啊!这令人可爱的家伙。
人们又都加倍地忙碌着。虽然,他们都是吃着蕃薯,杂粮,玉蜀黍来工作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一点儿疲劳的样子,因为他们的眼睛前,已经开展了新的巨大的希望。
一切都是快乐的,欢喜的,快乐得象走上天堂一样。浆刮子,小刀儿,盆,钵,都准备好了,只等罂花一谢,马上就得开始划桃子的。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别扭,突然地——在乡公会大门前,闹出了一个象青天霹雳似的消息。
“什么,又来了委员?”
“委员!还有告示呢。一大张一大张地贴在乡公会的门首。”
“我操他的妈!他把我们,把我们一个什么名目?”
“名目:杂粮捐!”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有稻不种,种烟苗。我们都犯了‘穷法’,所以都要捐,每亩田,正附是四十三块,还有团防的烟苗费。……”
“‘有稻不种’!我操他归了包堆的祖宗!他不是不肯借谷我们吗?‘烟苗’,不也是他们自己发下来的吗……”
“是的!三胡髭。什么全是圈套啦,他们不发种谷,借烟苗,我告诉你,全是圈套。他要我们给他种了,他得现成。我们,我们得操他的八百代祖宗啊!……”
三胡髭闷足了一口气,脸上已经涨得通红的了。他尽量地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可是,他说不出。他只是气,气……
因为他的巨大的希望,眼见得又将成为泡影了。终于,他拚性命似地进了十来个字出来。
“去!我们都和这些狗入的委员算账去!”
下午,千百个人团集在乡公会的门前,由团丁和卫队们开了三四十响朝天枪,算是代替了委员老爷们的回话。
“怎么办呢?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
“怎么办?”宝宗从人丛中跳了出来,“说来说去,反正都是种的这鬼鸦片烟。现在,我们已经捞不到这鬼东西的好处了,我们不如大家齐心,把它拔了起来,一股脑儿全给它毁掉,大家都弄不成,看他还能派我们的什么鬼捐鬼税。”
“好,拔下来!反正大家都捞不到手了。”
“不给那班忘八入的得现成!”
只有三胡髭没有作声,“拔起来”,真是可惜!但是大家都跑到田中去拔的时候,他却又没法能够阻止他们。
“真可惜啊!”
夜晚,全邓石桥的烟苗便统统倒在田土上。
四
拔去了祸根之后,全邓石桥的农民,都象是非常安心了似的。都各别的去寻找着他们自家的出路。乡公会里的委员老爷们也偷偷地溜去了,光景总该再没有什么花样出了吧。
丁娘的心绪,又同那借不到种谷时的情形一样了。焦灼而烦乱地,想不出来丝毫办法。生活差不多又已经走到了绝境了,而未来的出路仍旧是那么迷茫的。仅仅是有田,有蛮牛似的孩子,又能得到什么裨益呢?
在各种不同的刺激交集中,丁娘终于病倒下来了。然而,她还是不馁气。她还是一样地督促着儿子,指挥着儿子,做各种日常的工作。
在一个母子们闲谈的午夜。突然地,外面跑进来了一个行色仓皇的中年的男子。宝宗定神地一看——是三胡髭。
“为什么这样慌张呢?三胡髭!”
“不,不,不得了!县里又派人来征什么懒……懒捐的来了。上屋的王子和,同李老大,江六师公,都给捉了去。现在还到处捉人。很多人都跑到罗罗山去了,你,你……”
“什么?懒捐!?”
“是的!懒捐!拔掉了烟苗的都是懒鬼,都得抽懒捐。”
“抽多少?为什么这样快呢?”
“没有数!见人就抓!你得赶快跑!你是发起技苗的人,你得赶快跑……要不然!……”
三胡髭象怕人追着了他似地,话还没有说完,就拔着腿子逃了。
“怎么办呢?妈!”
“你!你,你赶快逃啦!”
“逃?你老人家?……”
“你去!你不要管我!去吧!平静了,再回来。”
“我,我不能放心你,妈!……”
“赶快去……”
丁娘,尽量地挥着手,样子象急得要爬起来,宝宗连忙跑上去将她扶着。
“好!妈!你睡吧!我去,我就去!你放心吧!放心吧!我,我!……”
天色已经乌黑了,远远地,有一阵嘈杂的人声,渐渐地向这儿扑来了。宝宗,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他很急速地蹈出了自己的茅棚子,准备向着罗罗山那方奔逃着。因为那儿,还有早就被赶去了的一大伙呢。
回头望望家,望望妈妈的病床,宝宗的心房象炸裂了一样。腿子抖战地,象浸在水里。他再用力地提将起来,向黑暗中飞跑着。
“妈呀!……”
第二天,全邓石桥象沉了似的。旷野里,看不到行人,看不到任何生物。除了那遍野憔悴的罂花,和一杆团防分队的大旗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