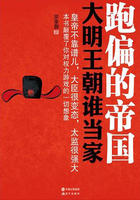“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封建时期每一个汉人必须恪守的孝道。但清军入关后,却要强行推行“薙发令”,一时间人心惶惶,在孝道和性命面前,汉人不知何去何从。
但他自10岁成童束发,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了48年,始终是“高挽玄鬓”,史传也说他是“完发以殁身”,可以说,王夫之是抵制清廷的薙发令最彻底的一个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还留下了许多抗拒剃发的诗赋,“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已经67岁的他在让人画像时还要强调他头上的“千茎雪”,因为那是他作为明朝遗老的标志。在他的绝笔《船山记》中他以山之“顽石”自喻,单从他一生誓不剃发已经可以窥见一斑了。
誓死不剃“千茎雪”
清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军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除了大量圈占土地、血腥镇压汉族抗清斗争外,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薙发。就像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在建立新朝时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一样,行薙发也是新朝的一种制度,它意味着世居中原的汉族的中华冠裳的改变,也象征着满清征服了华夏,汉族人民通过薙发表示臣服满清的统治。
在顺治元年薙发令推行之初,因遭到汉族广大人民的抵制,推行者还能够听其自便,略微宽松点,但到了第二年,清廷便以屠刀加颈来强制推行薙发令。据《东华录》记载,这一年六月顺治谕令豫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自应尽令薙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又谕令礼部,限部文到达十日内,尽行薙发,如有迟疑不决,按逆命之寇处置。可见清廷上下是要将薙发令当作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来贯彻实施的。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就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从家庭来说,汉族长期沿袭的束发具有“孝”的意义,而从社会意义上讲,束发还有“礼”的意义,它是汉民族区别于蛮夷、索虏的重要象征。因而清廷在汉族人中间强行推行薙发令,自然是对汉民族情感和自尊心的极大伤害和侮辱,这也就难怪许多汉族的士大夫和儒生们奋起抵制,有的甚至不惜以头颅热血为代价。“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汉族士人的铮铮傲骨。
作为一名汉族士人,一名儒生,王夫之自然要坚定地抵制所谓的薙发令,而且他也的确彻底地坚持了下来,到死都没有剃发。其实,王夫之不惜以头颅抗拒薙发,已经不是单纯的忠于朱明王朝,而是忠于整个民族,他反抗的是民族征服和压迫,维护的是民族尊严和文明。
清廷在推行薙发令的时候,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叫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鲁迅先生也曾在文章中这样写到:“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可以说是杀气腾腾,鲜血淋淋,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尽管这样,江南人民仍展开了持久的反薙发斗争。王夫之和他的好友如李跨鳌、李国相、姚湘等人自然也在其中。
王夫之誓死不薙发的决心,在他留下的大量诗作中我们可以略窥一二。
“回首人间镜影非,下自黄童上白叟”(《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之七》)写的是清军薙发,从黄发儿童到皓首老翁无一幸免,被薙发的人用镜子照看,都已经不是旧时容貌,这实际上也是说江山易主,山河变色;“呜呼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发肤”(同上)则明确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容毁伤!”
“扯断藕丝无住处,弥天元不罥修罗。”(《偶闷自遣》)作这首诗时王夫之33岁,诗中他说“我头上的乌黑之发一定要好生保护,一旦被剃去,那天地之间就没有我容身之处了!即使布下天罗地网,也不能束缚住阿修罗的反抗。”
“始自今以延延兮,羌百龄而犹参。”(《惜余鬒赋》)今后我的头发要让它长远地留着,一直到百年之后;“往者既已返乎皇天兮,遗来者之归后土;惟兹心之硕兮,永不食于终古。”(同上)已经梳落了的头发只是自然现象,现在头上之发,我要让它与我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同回归大地。这首《惜余鬒赋》就在王夫之逝世的前一年,还为他的学生唐端笏在绢上重新写了一遍。
“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走笔示刘生思肯》)此时已经67岁的王夫之在让人给他画像的时候仍要强调他头顶上的“千茎雪”。
王夫之的一生言行一致,不管面临什么艰难困苦,他始终能坚持不薙发,为了躲避薙发,他不得不一度更名换姓、改冠易服,自称瑶人,居瑶洞,浪迹于荒山野岭之间达三年之久。
康熙三十一年(1692),这个坚持不肯薙发的老“顽石”终于得以完发而终,做了一个真正而彻底的大明遗民。
策划衡山起义,胎死腹中
抵制薙发只是表明自己不是满清统治下的顺民,而是明朝的遗民,因此虽然可以说是反清之举,但还算不上是一种积极的反清复明的行动。王夫之清醒地知道,要想恢复大明河山,就要采取积极行动,武装起来与清廷抗争,于是,他在清顺治五年(1648)前后参加和组织义军,进行武装抗清。
在清顺治二年至四年,先后在南京、绍兴、福州和肇庆成立了弘光、鲁王、隆武和永历四个南明政权,但当时南明的抗清形势却不容乐观,主要就表现在各抗清武装和农民起义部队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有些部队为了保存实力,故意避敌锋芒,朝廷军队更是猜忌、排挤农民起义军,之间经常起争端,闹摩擦;南明各小政权之间也争正统,抢地盘,在萧墙内搞消耗。
王夫之所在的湖广地区情况也不例外,当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的湖广的何腾蛟与湖北巡抚堵胤锡两人之间“措置无术”,不能周密布置抗清队伍,又不能妥善处理好后勤供给,更不能主动联合湖广地区的广大农民起义军,而这些问题却都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关键问题。王夫之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何、堵就像是鼎耳上面的吊环,而章旷(时任佥都御史巡抚江北)则是“雉膏”,三者各当重任,如果相互之间不合作,那鼎就会倾覆,里面的食物自然也就不存在,也就是说抗清队伍会全军覆没,南明政权会覆亡。应该说这是一种全局的眼光,当时南明政权中缺少的也正是这样的人。
清顺治三年(1646)夏天,王夫之独自一人奔赴湘阳,求见了当时被何腾蛟任为监军的章旷。他上书给章旷,向他分析了当下的抗清形势,明确提出何、堵两军一定要鼎力合作,同时尽可能联合大顺农民军,统筹粮饷,方能共同抗清,以挽救时局。王夫之是想通过章旷与何、堵两家均保持有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把自己的想法、策划传达给何腾蛟、堵胤锡,并使他们采纳。只可惜王夫之的意见在章旷这就被否了,章认为何、堵之间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凡说王夫之是过虑了,这让王夫之大失所望。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王夫之所提的意见非但不是过虑,更是切中要害,是影响抗清大局的大问题。只可惜那个时候已经迟了。
就在第二年,湖广地区就尝到了将领失和给抗清大业带来的恶果。这年二月,明降将孔有德奉清主之命率兵大举进犯湖南,攻打长沙等地,除了章旷督孤军与之奋战,余者皆不听调度,不去参加长沙保卫战。还有何腾蛟手下的马进忠曾经率部收复常德,但此时堵胤锡却调集军队夺常德,火并马进忠的部队,马只好弃城而走。就这样,由于各军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先后都被清军各个击破了,最后章旷于顺治五年(1648)兵败绝食而死,而何腾蛟自己也被俘遇害。王夫之看到此等情景,心里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从湘阴上书归来,王夫之的家庭又遭遇了巨变,这也是拜当时的战争所赐。首先是王夫之的妻子陶氏,因其父母兄弟均于丧乱中亡故,因而悲痛致死,王夫之曾作《陶孺人像赞》、《悼亡诗》等悼念亡妻。接着,由于清军两路南攻,汉奸孔有德带队攻下湘阴、长沙、衡州等地,王夫之全家在逃亡时失散,其父亲、二叔、三叔以及仲兄均在战乱中相继去世。王夫之本人也是四处逃难,可以说此时的王夫之也是背负着国仇家很。
清顺治五年(1648),湖广地区战局曾经一度发生过有利于抗清力量的戏剧性转变:首先明降将金生桓、李成栋等先后在广西、广州反正;然后是大顺农民军组成“忠贞营”,奋起反攻,大败清军于湘潭地区,收复了益阳、湘潭、衡山等地;何腾蛟也曾一度反攻,取得全州大捷。此时的王夫之大受鼓舞,毅然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当即决定与夏汝弼、管嗣裘等在南岳方广寺举兵起义。此次起义虽经王夫之等人艰苦筹划,但终因势单力孤,起义尚未发动,就被尹长明所率部队袭击而溃败,管嗣裘一家老小被害。此次衡山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王夫之对其的评价是“能与仇战,虽败犹荣”,起义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王夫之却丝毫没有因为失败而感到气馁或后悔,反而让人感受到了他那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对于王夫之与好友组织的这次武装起义,潘宗洛在《船山先生传》中曾这样说:“诚知时势已去,独慨然出而图之,奋不顾身”,的确,在清兵势如破竹的攻击下,在南明政权相继覆亡、数百万军队土崩瓦解的形势下,王夫之以一介书生、若干义勇去迎敌,无异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其实,王夫之又何曾不知?但国仇家恨已容不得他做选择。
衡山举兵失败后,王夫之为了逃避清兵的追捕,与管嗣裘一路南下直至肇庆,他想要依附在这刚成立不久的永历政权而有所作为。
远赴“行在”,献身永历政权
永历政权是于清顺治三年(1646)十月在广东肇庆成立的,这是继南京弘光政权、福州隆武政权、绍兴鲁王政权之后的第四个南明政权。永历政权的建立,给出在悲痛和绝望中的王夫之又带来了一丝希望,他曾用“圣孙龙翔翔桂海”(《忆得·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来赞颂桂王朱由榔的即位,也寄托了他对永历政权恢复大明河山的热切希望。因此,他在衡山举兵起义失败后,当即决定南下,投奔永历政权,继续为抗清效命。
王夫之与管嗣裘到达肇庆后,管被授以中书舍人,王则被堵胤锡举荐为翰林院庶吉士,但被他以父丧在身为由辞谢了,故这一次王夫之以布衣身份在肇庆活动了将近三个月。
不过,在王夫之在永历政权的这三个月中,他看到的、经历的却是这个小政权内部严重的派系斗争和贪污腐败。这个永历小朝廷从一开始成立,便通过卖官鬻爵来筹备粮饷,所谓的朝臣们贪污成风,一个个是醉生梦死,整个朝廷上下哪有什么抗清复明的紧张气氛。眼前的这个朝廷无疑给空有满腔热情的王夫之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经过犹豫再三,反复思量之后,王夫之最后决定返归家乡。
虽然王夫之返回了家乡,但他的内心仍牵挂着永历政权的兴亡,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为朝廷效力。此后他还曾劝当时已经削发为僧的方以智出山为永历政权效力,可见他自己也不会长期待在家乡,一有机会他还是要复出的。
果不其然,王夫之是在顺治六年(1649)夏天从肇庆回来的,秋天他又离开衡山,再度奔赴肇庆。不过这次南下也有点被逼无奈的味道。这年年初,湖广的抗清斗争接连失利,先是何腾蛟被俘遇害,接着湖南全境得而复失,被清军占领全境,又加上地方武装骚乱,当时王夫之一家在骚乱中被抢劫一空,就连他所作的《采薇稿》也未能幸免于难。又因为王夫之曾经组织过抗清武装,当地的土寇企图借此勒索王夫之,在这种处境中,王夫之的母亲谭太夫人遂叫儿子早点离开衡州,王夫之这才成行。
在这次南下的过程中,王夫之先到庆州拜见了堵胤锡。堵胤锡深知王夫之的学术造诣和文学才能,所以将自己多年的戎马生涯和与士兵共同生活战斗的体验写成军谣十首交给王夫之,嘱咐他代为传之于世。之后,他又往桂林拜见了瞿式耜,参加了瞿的60寿庆。这时瞿式耜又推荐王夫之到朝廷任职,起初他还是以父丧未满为由辞而不受。到了次年春天,清军南攻,永历帝不得已逃往梧州,此时王夫之的父丧已满,于是他随即赶往梧州,接受了行人司行人之职,实际上也就是掌管传旨、册封等礼仪的一个小官吏,并没有什么实权。其实这个官职对王夫之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取得上书言事的机会。
当时永历政权内部朝纲败坏,党争十分激烈。大学士王化澄与马吉翔、夏国祥等奸臣、宦官勾结为“吴党”,他们贪赃枉法,陷害忠良,最为发指的是将当时的抗清中坚金堡等污蔑为“五虎”,将他们打入锦衣卫大狱,欲置之于死地。如此颠倒黑白、残害忠良的行为自然让王夫之义愤填膺,他抱着自己必死的决心展开了营救金堡等忠臣的行动。
他先是和管嗣裘一起去拜谒了严起恒,在严面前他痛切陈词:“诸君弃坟墓,捐妻子,从王于刀剑之中,而党人杀之,则志士解体,虽欲效赵氏之亡,明白慷慨,谁与共之者!国势如此,而作如此事,奈天下后世何?”那些个忠臣义士出生入死,本要想为国尽忠,保的也是大明王朝,却不能死在疆场上,而被奸人所害,这样还有谁愿意为大明效忠呢?可谓句句情恳意切,于是严起恒就率诸大臣向永历帝“泣陈”,同时瞿式耜也向朝廷“亢疏申理”,即便是这样,永历帝仍旧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可见这位皇帝已经昏聩到何种程度。后来还是由忠贞营主帅高一功、总兵焦琏等人出面相救,金堡等人才得以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