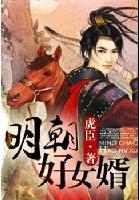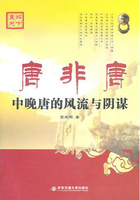没错,明代的“陈世美”是钧州才子,而之后广为流传的“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则是均州人士。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因为钧州在河南,而均州则在湖北,相差何止千里。而陈熟美恰好是均州人士,同“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刚好一致。如果“铡美案”同《包公案》是一脉相承的,那又何必煞费苦心更改地名呢?
但说来说去,我们好像还是没搞清楚陈世美到底是谁。目前已知的最早有关陈世美的记载,就是这本明朝小说《包公案》。明代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借古讽今。无论是《西游记》还是《水浒传》,甚至包括《金瓶梅》在内,这些明人所著的小说看似说的是古事,实则讲的都是明代的事情,《包公案》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此书成书于万历年间,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却很繁荣。作者很可能不满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借包大人之手,“惩治”恶人,抒发心中愤懑;但明代一朝都不见驸马因抛弃妻子而被杀之事,所以,陈世美的原型人物很可能是明代的某个官员。作者安遇时将其化作陈世美,编写了《秦氏还魂配世美》的故事。到了清代,有别具用心之人发现了这个故事同陈熟美的相似之处,恶意篡改,形成了我们熟悉的“铡美案”。
不管陈世美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原型,但“铡美案”为人杜撰却是板上钉钉之事。为了一桩子虚乌有的杀妻案,陈世美背负了上百年的骂名,要多冤枉有多冤枉!
链接一:宋代真有“包青天”?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英雄豪杰,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这是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当年,电视剧《包青天》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剧中所塑造的公正廉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包拯的“标准像”,在海峡两岸都有着数量庞大的拥趸。但每次重温这部经典剧集之时,总有人难免心生疑问:宋朝真有“包青天”吗?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包拯形象,大都出自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三侠五义》。作为一本侠义小说,《三侠五义》把江湖恩怨、除暴安良等等元素引入到传统的公案小说中,因此使得包公案相较以往更具吸引力,经久不衰。包拯的艺术形象也在这部书中基本定型,他深明大义,足智多谋,恩威并施,是典型的清官,人称“包青天”。可惜,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同这个“包青天”相差得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包拯是宋仁宗时的重臣,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等职,授龙图阁直学士,曾经出使契丹。从他升迁轨迹以及其文集《包拯集》中记述的言论来看,他是一个心系家国大事的政治家,而非体恤百姓的父母官。他所提出的精兵简政、减轻赋税等等主张,其出发点是巩固皇权统治,同救民于水火没多大关系。
由于文学作品的渲染,很多人都把包拯当作开封府尹,以为那才是他的正职。实际上,恰恰相反,开封府尹只是包拯众多兼职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帝主宰一切,官员的“官职”和实际负责的“实职”是相分离的。官职只是一个虚称,相当于职称等级,只决定官员的俸禄。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谋一个“实职”才行。皇帝会根据官员的实际才能和职务需求,调遣官员临时担任某项职务,称之为“差遣”。“差遣”的名头很多,包括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等,非常复杂。
据史书记载,包拯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三月“知开封府”,也就是暂代开封府府尹的职权。根据北宋惯例,开封府尹乃京师职守,关系重大,因此,这个职位一直是由皇亲国戚担任的。但亲王之流显然不会管事,因此要派一个普通官员“知”开封府,行使实际的权力才行。这个“知”的周期不会太长,一般也就是一年。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里,“知”过开封府尹的官员不下180人。所以,包拯也只是这个位置上的普通过客而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至于包拯断案如神,在历史上的记载就更少了,实属明确记载的只是包拯早年破获的一桩“割牛舌案”。至于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铡美案”、“铡包勉”等案件,则只字未见,疑为后人杜撰。而那三口赫赫有名的铡刀更是子虚乌有。
所以说,“包青天”只是文学作品中对于清廉官员的一种美好期许,跟现实中的包拯并没多大关联。历史是很奇妙的东西,既能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也会引发无以名状的失望。世事无常,但人们渴望公理和正义的心思是不变的,这也是“包青天”故事长盛不衰的原因吧。
链接二:官司,不是这么打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打官司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就能见到青天大老爷,洗脱冤屈,仿佛打官司就如同吃顿便饭那般简单。尽管打官司时常有恶吏从中作梗,但总能遇到明镜高悬的“包大人”,惩处不法宵小,还百姓公道。
古人打官司真是如此吗?哪有这种好事儿!
民谚有云:“饿死莫作贼,气死莫告状。”不少古代名士也劝诫世人,莫要轻易动打官司的念头,称“讼而终凶”。为什么古人都不主张告状打官司呢?原因很简单,在古代打官司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吃力不讨好。
首先,不是随时都可以告状的。古代没有专职的法官,审理案件的职权都是由县官以上官员兼任的。这些官员平时公务繁忙,不可能每天坐在堂上等着老百姓来告状。因此,官府就规定出几个专门用来受理诉讼的日子,称为“放告”;而衙门口的鼓,也并非为老百姓“鸣冤”准备的,而是官府用来通知百姓“放告”的信号。每到“放告”之日,官员准备好受理案件之时,就会命人击鼓。听见鼓声,老百姓就知道:哦,可以告状了。于是纷纷拿着状纸前来,申诉冤情。
其次,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控告的。古代封建社会讲究礼法,因此法律也要遵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原则。奴婢不能控告主人,妻子不能控告丈夫,亲属之间原则上也不能相互控告;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或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不得告状;妇女告状也受到严格限制,除非家里没有男人,而又非告不可,一般“不许妇人诉”;另外,在押犯人也是不能告状的。
第三,不同的案件告状的时间也不一样。尤其是对于民事案件,历代都规定只有农闲时节才可以告状。我国古代以农立国,不误农时是头等大事,因此宋代律法就明确规定,但凡有关田宅、婚姻、债务的案件,一律在每年十月初至次年三月期间受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告状容易“很受伤”。古代没有什么先进的刑侦手段,官员断案全凭个人判断,依靠察言观色来识别诉讼双方所言的真伪。但人眼不比测谎仪,有时候很难区分到底谁在撒谎。那怎么办呢?打!不光被告要打,原告也要打。常有原告官司没打赢,自己反而吃了一顿板子的情况出现。轻者皮开肉绽,重者一命呜呼。刑堂之上,生死有命,所言非虚啊。
这么看来,古代打官司实在是一件费事费心的事情,难怪那么多的“有识之士”劝导时人,没事儿别打官司了。
链接三:公主只嫁状元郎?
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可谓天下第一女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公主万金之躯,婚配对象自然不能是凡夫俗子,一定要是人中之龙才行。依照寻常看法,状元郎乃是文曲星降世,才高八斗,肯定满足这个条件。因此“公主只嫁状元郎”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不过,翻过史书之后,我们却隐约感到,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公主的夫婿称为驸马。驸马原本是一个官职,全称是驸马都尉。这个官,是皇帝出游时坐在副车上的替身。这个职位非常危险,一般人做不来。皇帝的女婿是皇亲,给皇帝当替身不会有损皇室威仪,也相对靠得住;如果发生意外,因公殉职,死的不过是个外戚,因此皇帝的女婿就逐渐成为这个职位的内定人选,驸马也就逐渐成为帝婿的代称,延续下来了。
驸马虽然是皇帝的女婿,但地位却不高。历代的驸马品级都很低。唐宋两代,驸马都是从五品,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驸马是唯一地位比自己妻子低贱的男性。生死富贵,全看公主一人,因此卑躬屈膝是难免的。“醉打金枝”这类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就算两口子闹矛盾,驸马爷不高兴了,充其量也就是跑回老家。当然,最后还是要乖乖回来向公主和皇帝认罪赔礼的。
至于驸马的选定,也是有一定标准的。皇帝家是天下第一世家,门第最为显赫。想要跟皇帝攀亲家,最起码也得是达官显贵。魏晋时代,驸马一般都是在知名士族子弟中选择;到了宋代,则一般选择重臣之子。可见,驸马这个位子平头百姓是万万高攀不上的。
而状元呢,指的是科举殿试第一名。状元并不是个官名,只是说明这个人很会考试;至于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那都是后话,全凭个人能耐。一般,官宦之后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能混得很好,即使参加了,成绩也不会太好——只要勉强中个进士,就能平步青云,何苦独占鳌头惹人非议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中状元的人,家世都不会显赫。只有贫苦人家的孩子才能耐得住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寂寞,埋头苦读,击败众多士子,拔得头筹。这样的状元,跨马游街只是一个开始,新鲜劲儿过了之后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找一个朝中显贵拜入其门下,才有机会出人头地。
这样看来,状元郎想娶公主,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在历史上,我们也没听说哪个状元当上驸马爷的例子。“公主只嫁状元郎”,可能只是我们对于郎才女貌的美好期许罢了。
链接四:那些被戏剧“诬陷”的人们
戏剧这种东西,亦真亦假,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往往要做一些艺术加工。因此,被戏说的历史人物往往同真实相去甚远。可惜,观众们并不管“艺术夸张”那一套,常常把戏文和现实混为一谈。拜戏剧所赐,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骂名一背就是几百年。
中国各种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戏剧流传甚广,不仅塑造了一个个传奇人物,也“捧红”了一群恶人。这其中,就不乏像陈世美一样被戏剧“诬陷”的人物。
“狸猫换太子”里面的皇后刘娥因为嫉妒,居然用狸猫换掉了别人的孩子,真是罪大恶极。刘娥在历史上是实有的人物。她是宋真宗的皇后,在宋仁宗时期,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11年,抚育小皇帝仁宗长大成人,居功至伟。史学界常常将她同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并称,并称赞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刘娥抱养太子之事,的确属实。但这孩子的生母并非什么真宗宠妃,而是刘娥自己的侍女李氏。当年,刘娥一直不能生育,作为太后近侍的李氏于是想出了一个借腹生子的法子,产下一子,也就是日后的宋仁宗;仁宗一生下来,就交给刘娥抚养。而刘娥待李氏也不薄,让真宗将李氏晋为才人,也算有了名分。这件事,满朝文武尽人皆知,并不存在刘娥为争宠“偷抱”皇子的桥段。
另外一位被“冤枉”的人物是《杨家将》里的大奸角潘仁美。潘仁美的人物原型名叫潘美,是北宋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在杨家将的故事中,潘仁美嫉贤妒能,为了争功导致杨家太公杨业战死,是杨家将中所有悲喜剧的始作俑者。
实际上,潘美是北宋的开国元勋,宋辽岐沟关之战时已经年逾六旬,位高权重,是杨业的上司。当时,北宋趁辽国换帝之际,派三路大军进攻辽国。起初,宋军打得顺风顺水,但很快就遭到契丹军队的顽强反击,东路军大败于岐沟关。因此,上谕潘美撤兵,并掩护云、应等州军民一道撤走。撤军途中,监军王侁强令杨业所部出战,置之于必败境地。杨业兵败被俘,绝食而亡。潘美因阻止不力被降职,但次年又官复原职。
所以说,杨业之死,同潘美关系不大,要怪只能怪皇帝决策失误。赵匡胤是以哗变武将的身份取得天下的,因此对于武人非常忌惮。不仅杯酒释兵权,还大大限制武将的职权。和平时期,士兵同将领是分离的,战时才临时编组,以致“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同时,武将在阵前没有指挥权,只能听命于朝廷派来监军的文官,严格依照皇帝的旨意行事。换言之,在宋代,行军打仗是由皇帝一个人在宫城遥控的,武将只起到一个传达命令的作用。这种军事制度导致宋代军事实力空前衰弱,也为其亡国埋下了祸根。
《杨家将》的作者大概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为避免毁谤之嫌,才将潘美和杨业的名字中间各加一字,写成“潘仁美”和“杨继业”。虽然也算煞费苦心,却依旧挡不住世人对潘美的唾骂。北宋开国名臣,至忠至诚的潘美,就这样沦为不仁不义的奸佞小人,冤枉得一塌糊涂。
“卖国贼”的无奈——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清朝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因“天津教案”交涉失当,被污为“民贼、汉奸”,引起举国唾骂。
当20世纪的到来尚使不少人欣喜迷茫之时,清王朝,这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绝响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崩溃。在这个帝国最后的那段岁月里,无数枭雄豪杰粉墨登场,上演着各自的戏码。在这些“戏子”中,有个人我们不得不提。他,被称为“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人”,更是晚清的中兴之臣;他文治武功卓著,却被视为“民贼汉奸”。他,就是曾国藩,晚清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激昂热血枉然之时,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卖国贼”的一生,可能会有别样的发现。
带兵如子弟,平叛不留情
如果不是因为太平天国,曾国藩可能至死都只是个仕途平顺、波澜不惊的职业官僚。他甚至都不会被载入史册,充其量只是晚清壮阔的历史画卷上微不足道的一点。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席卷半个清帝国。此时的曾国藩已然是二品大员,十年七迁的官场神话一时无人能够超越。不过,上天似乎并不希望曾国藩一直在公文堆里打滚,因此给了他一个成就伟业的机会。
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和“绿营”。清王朝立国的根本,也是“八旗”。这支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的骁勇劲旅,来去如风,曾经是华夏大地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女真人口稀少,无法维持一只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因此努尔哈赤在传统的“牛录制”基础上,整合麾下满、蒙、汉诸族军兵,创建了“八旗”。满、蒙、汉各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满人的军事核心力量。这种耕战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使得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人得以统治将近一亿的汉人,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牢牢控制在满人手中。正因为战功彪炳,八旗子弟才世代享受国家厚遇,成为清帝国的贵族阶层。
而“绿营”则是国家的常备军。绿营兵是清政府仿照明代军制所创制的汉族军队,因以绿旗为标志而得名。绿营兵的规模要远高于八旗,主要以步兵为主,驻扎全国。在清代初期平定三藩之乱以及之后的历次战争中,绿营兵表现较为出色,战功卓著。绿营兵组织系统严密,分工明确,是清王朝维持其统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