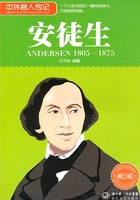1.做事击中要害,才能稳保自己的地位
做事情,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遭到别人反对的时候,更不能火冒三丈,意气用事。只有找出事情的重点,抓住事情的要害,才能对反对者一击而中。
面对反对者死缠滥打的攻击,李鸿章的处理不能不称之为睿智。第一,抓住攻击者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第二,避重就轻,尽量不刺激反对者,将反对的力量降到最低。
在修建铁路上,李鸿章的这种睿智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既降低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风险,同时,也不断地推进着铁路的进程。
李鸿章知道,如果等到让所有的人都同意修铁路的时候再行动,一切就太迟了。关于修铁路的利弊,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而不是泛泛的讨论,于是,在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为避免朝廷非议,他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是以骡马拖载车皮前行,他相信只要铁轨在就有希望,只要火车在走,哪怕是骡马拖着,就有希望。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剪彩,意味深远。
唐胥铁路,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唐胥铁路虽然只是一条长约十公里的小铁路,但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开始,意义重大。修建唐胥铁路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平煤矿煤炭的外运,所以,一经通车便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由“萧瑟荒村”发展为“大市落”。
李鸿章对洋务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采取避重就轻、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
1887年春,由奕出面,以“为调兵运军火之用”为由,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第二年竣工,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将铁路延长到天津,李鸿章一直以各种名义,避开敏感的话题,避开反对派的弹劾,低调但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铁路建设。
而此时,铁路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以及铁路的效益也显现出来。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一百三十公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顽固派本来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开始了。
这次李鸿章有醇亲王奕的支持,又有现实的铁路作为依据,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
针对反对派提出的责难,李鸿章一一加以辩驳。
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
同时,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
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这一次大争论,有已经修成的唐津铁路的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更加上中法战争后奕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所以坚决支持修路。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终告结束。
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
李鸿章十分清楚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谈何容易!他认为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就在这时,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东北的安全,于是李鸿章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
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一百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铁路”这种新式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争夺……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而李鸿章避重就轻,绕开障碍,抓住要害,避开非议,既避开矛盾,把阻力降到最小,又抓住要害,保住自己政治地位的同时,有力地推动着事情前进。
2.不染指他人之功,官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在取舍之间就决定了。
1864年,淮军力克常州,苏南战局基本平定。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顺江而下形成对南京的包围。
这时,朝廷命令李鸿章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南京的曾国荃部。对于曾氏兄弟而言,他们非常忌讳兵强马壮的淮军助攻南京,假如那样,曾氏十数年苦战的果实将被别人摘得,这是曾氏兄弟极不愿看到的。
尤其是曾国荃,自尊心非常强,对于淮军的节节胜利,倔强的他几近忧郁成疾。曾国藩当然心疼弟弟,多次写信给曾国荃,劝慰他要宽心,假如李鸿章要来合攻南京的话,千万不要多心,“独克固佳,会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
此时的金陵,已经是囊中之物,李鸿章到否,与南京是否会被攻克毫无关系。
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顺从朝廷的命令,会攻南京,或许会夺得头功,但会让曾国藩兄弟两人颜面无光,可能还会被朝廷怪罪,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必将彻底终结。如果自己不能得头功,劳神费力的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第二,如果不会攻南京,会被朝廷责备,但不攻金陵,李鸿章可以有若干理由搪塞。
孰重孰轻,李鸿章自然明白。经过思量之后,李鸿章选择了拖延。
李鸿章之所以选择拖延,还有一个原因。
在1862年底,忠王李秀成回到南京以后,太平军和曾国荃之间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了。曾国荃感到他的力量不足,所以就给他哥哥曾国藩写信说,我原来的那个部下程学启现在给了李鸿章,能不能把他再调回给我,以解燃眉之急。曾国藩就给李鸿章写了信,叫李鸿章把程学启派到南京,帮助曾国荃。
当时程学启在李鸿章的手下非常受重用,而且程学启和曾国荃的关系又不好,所以程学启本人不愿意去,李鸿章也不愿意放掉这样一个得力的干将。尤其是刚刚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站住脚,他更不愿意失去这样的干将。
所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这事不太好办。然后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信,说程学启现在无法离开。
当时,李鸿章为了保证自己的实力,拼着与曾国藩撕破脸,拒不援助南京。当然,后来曾国藩原谅了李鸿章,但这件事毕竟让俩人心生芥蒂。这时,李鸿章如果贸然会攻南京,一旦处理不好,要么自己劳而无功,要么就是与曾国藩彻底决裂了,孰重孰轻,李鸿章心里自然清楚。
李鸿章在接到朝廷命令后,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李鸿章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队伍疲惫,想休整一段时间。实际上,李鸿章是想给曾国荃预留充足的时间。朝廷见淮军迟迟未动,连降谕旨,敦促李鸿章火速调兵。
李鸿章只好借口生病回苏州,不久又提出部队要休整两个月才能再战,最后李鸿章实在拖不过去了,便灵机一动,出兵浙江,谎称要从湖州对南京形成包围。谁料此举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左、李二人成了一辈子冤家。
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他为之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南京,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因为湘军已将南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又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的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
李鸿章一拖再拖,实在是用心良苦,后来,连淮军将领都看不过去了,纷纷表达对李鸿章的不满。李鸿章只好再次给曾国荃写信,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严令李鸿章派刘铭传等先锋火速驰往南京。
李鸿章无奈,只好派刘铭传、王永胜、刘士奇各率一万五千人前往,自己大队人马仍按兵不动。此时,曾国荃接到李鸿章调兵前来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将李鸿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诸将,说:“他人将要来了,难道我们苦苦攻了两年的成果将要拱手相让吗?”手下的将领果断表示:“愿尽死力。”当晚,通向南京城内的地道已经完工,次日,曾国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门城垣二十余丈,攻下南京。
对此,曾国藩极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鸿章赶到,曾国藩亲至城外下关迎接,拉着李鸿章的手连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
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晋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李鸿章在这次拖延当中可谓名利双收了。
其实当时就实力而言,淮军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攻坚能力,都在湘军之上。但即便当时李鸿章抢得了头功,获得的封赏也不一定能超过他放弃的时候。
在小利面前懂得放手,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又一秘诀。
3.与狼共舞,需要的不止是胆识
一个团队讲究可控性,对人的利用同样讲究可控性。
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如果处理不好,尾大不掉就会被牵累,甚至被反控制。
所以,在利用的同时,要讲控制。
在利用洋人方面,用得好,是锦上添花,用得不好,是画蛇添足,如果尾大不掉,被其裹挟与控制,那就是引狼入室。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
咸丰帝在临逃之际,任命恭亲王奕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经过一番“谈判”,奕终于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次与洋人打交道,让奕认识到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外族入侵的不同: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利益,而不要清政府的土地与人民。也就是说,他们对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不感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奕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的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唯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
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最后,奕得出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既然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是根本政治利益的矛盾,而是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那清政府大可利用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技术优势,来解除内患。
于是,借师助剿的策略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早在1860年,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雇美国人华尔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昉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李鸿章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
李鸿章开始在内心敲打自己的算盘:如果把“常胜军”收归己有,同时加以控制的话,那自己就是如虎添翼。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常胜军”虽然战斗力强悍,但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只是雇佣军的性质,换句话说,不过是从洋人那里买来的一杆枪。这杆枪认钱不认人,一旦失控,必然后患无穷。
李鸿章于是着手“常胜军”的改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