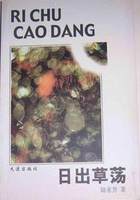第二部第五章第五个故事 (2)
纸条上整齐地写着这么几句话:“对不起,先生,我想睡了。明天上午九、十点之间我再来。”我一问,得知那突眼的孩子来过了,看了我的名片和留言之后,等了一个小时,什么都没做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写下这句话就回家了,并告诉佣人说“他晚上不睡觉什么也干不成。”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已经在等着客人。九点半,我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进来,鹅莓!”我喊道。“谢谢,先生,”一个忧郁的声音应道。门开了。我一骨碌站了起来,正面对着的是克夫探长!
“我想我在往约克郡写信之前说不定会在这里碰见你,”克夫探长说道。
他还像以往一样消瘦。他的眼睛仍不失往日的那种神情,“看你的时候似乎比你自己发现的还要多。”可是,看起来衣服能改变一个人。克夫探长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他戴了顶阔边帽,穿了一件浅色的猎装和一条白色的裤子,下穿一双黄褐色的高统靴。他拿着一根橡木拐杖。他好像故意要显得像是一辈子住在乡下似的。我夸了几句他这副打扮,他也不觉得我是在打趣。他阴沉沉地埋怨伦敦的噪音和气味。我真拿不准,他说话是不是带点儿乡土音!我请他吃早饭。这单纯的乡下人吃了一惊。他的早饭是六点半吃的——而他上床睡觉的时间是和鸡鸭同一时间!
“我昨晚刚从爱尔兰回来,”探长说道。“上床睡觉前,我读到了你的来信,知道了自去年我调查那颗钻石之后又发生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好说。我完全搞错了。我不知碰见我当时那样的情况,又有多少人弄得清真相。可是事实不容质疑。我承认我搞得一团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不是第一次!从不出错的警官只有书本里才有。”
“你正好碰上恢复你名誉的关键时刻,”我说道。
“对不起,布莱克先生,”探长接过话去说道。“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一点也不在乎我的名誉。感谢上帝,我已经结束了我的名誉!我来这里,先生,是为了感谢范林达夫人在世时给我的重酬。如果你需要我,并且信任我的话,我想从新开始工作——完全是出于感激,而不是为了别的。请不要给我任何报酬。这是信誉问题。现在告诉我你上次写信给我以后,这案子的情况吧。”
我把鸦片试验,以及后来发生在仑巴德街银行里的事都告诉了他。他听到鸦片试验的事大吃一惊——这可是他从未听说过的事。他特别注意埃兹拉?詹宁斯有关过生日那晚,我离开雷切儿的房间之后,藏起了那颗钻石的说法。
“我不同意詹宁斯先生说的,说你把月亮宝石藏了起来,”克夫探长说道。“但我同意,你可能把它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怎么样了呢?”我问道。
“你自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吗,先生?”
“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布罗夫先生也猜不出什么吗?”
“和我一样。”
克夫探长站了起来,走到写字桌前。他拿过来一个封着的信封。上面标名“私信”;是给我的;角落里是探长的签名。
“我去年怀疑错了人,”他说;“现在可能又会搞错。布莱克先生,请你等到真相大白后再打开这封信。然后比较一下罪犯的姓名和我这封信里写的名字。”
我把信放进了口袋——然后询问探长对我们在银行采取的措施的看法。
“主意很好,先生,”他回答道,“而且应该这么做。可是除了鲁克先生,还有一个人应该受到监视。”
“就是你刚才给我的信里提到的那个人吗?”
“是的,布莱克先生,是信里提到的人。现在没有办法。到时候我会提醒你和布罗夫先生的。我们先等等,看那孩子有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告诉我们。”
十点钟了,那孩子还没来。克夫探长谈起了其它的事情。他打听了一下他的老朋友贝特里奇,还有那个老对手花匠的事。用不了一会儿,他自然会谈到他最喜爱的玫瑰花了。正好,我的仆人进来通知说,那孩子在楼下。
鹅莓被带进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住了。他怀疑地看着和我在一起的这个陌生人。我叫那孩子过来。
“你可以当着这位先生的面说,”我说道。“他是来帮我的;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克夫探长,”我补充道,“这就是布罗夫先生办事处的那个孩子。”
在我们现代文明社会里,名望(不管哪一种)是推动任何东西的杠杆。克夫探长的名望甚至已传到了小鹅莓的耳朵里。我刚一提到这著名的名字,那孩子的突眼就骨碌碌地转动起来,直到我真的担心它们会掉到地毯上。
“这边来,小家伙,”探长说道,“让我们听听你带来些什么消息。”
受到这位大人物——这位在伦敦每一个律师事务所流传的故事中的英雄——的关注,看来使这孩子受宠若惊了。他站在克夫探长的面前,手放在背后,像个新入教的教徒,在接受有关教义的题问。
“你叫什么名字?”探长开始提第一个问题。
“奥克塔维斯?盖伊,”那孩子回答道。“办事处的人根据我的眼睛都叫我鹅莓。”
“奥克塔维斯?盖伊,或是鹅莓,”探长非常庄重地继续说道,“你昨天在银行失踪了。你干什么去了?”
“对不起,先生,我是跟踪一个人去了。”
“是谁?”
“一个留黑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穿得像个水手。”
“我记得那个人!”我插了一句。“布罗夫先生和我认为他是那些印度人雇佣的一个间谍。”
克夫探长好像并不注意我和布罗夫先生的看法。他继续问鹅莓。
“那你为什么要跟踪那个水手呢?”
“对不起,先生,因为布罗夫先生想要知道,鲁克先生从银行出来时是不是把什么东西交给了别人。我看见鲁克先生把一样东西交给了那个留黑胡子的水手。”
“你为什么不把你看见的事告诉布罗夫先生呢?”
“我来不及了,先生。那水手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你就跟在他后面吗?”
“是的,先生。”
“鹅莓,”探长拍拍他的头说道,“你那小脑瓜子还挺灵——不是塞的棉花。我很喜欢你。”
那孩子高兴得脸都红了。探长继续往下说。
“那么,那水手到了街上又干了什么呢?”
“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先生。”
“你怎么办呢?”
“我跟在后面跑。”
探长还没来得及问下一个问题,仆人进来通知说,又来了一个客人——是布罗夫先生办事处的总秘书。
我觉得不该打断克夫探长询问那孩子,便在另一个房间里接待了那个秘书。他带来了关于他老板的坏消息。这两天的折腾把布罗夫先生累垮了。那天一早起来,他的痛风就发作了;他只有待在家里;在眼下这关键的时刻,他对于撇下我一个人孤立无援感到非常的不安。这位高级秘书受命听从我的指挥,而且愿意尽可能地替代好布罗夫先生。
我立刻写信安慰这位老先生,告诉他克夫探长来了;并补充说鹅莓正在接受盘问;我还答应他一有消息就写信或是亲自去告诉他。打发这个秘书拿我的信回去之后,我回到我刚才离开的那个房间,看见克夫探长在壁炉边,正在拉铃。
“对不起,布莱克先生,”探长说道。“我正想叫佣人去找你,我有话要对你说。我确信,这孩子,”探长拍了拍鹅莓的头说,“跟对了人。昨晚十点半钟你不巧没在家已失去了珍贵的时间。现在要做的是立刻叫一辆出租马车。”
五分钟后,探长和我(还有鹅莓坐在车顶上)向东朝城里赶去。
“总有一天,”探长指着前窗外说道,“那孩子会对我的晚年事业有所帮助的。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像他这样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了。我把刚才你离开房间后他说的事告诉你吧。好像,他刚才提到他跟在车后追的时候,你在吧?”
“是的。”
“那么后来,先生,那辆车从仑巴德街到了伦敦塔码头。黑胡子水手下了车,跟一条去鹿特丹的船上的水手说了几句话,这条船第二天早上就要开船。他问那水手,他能不能当时就上船,在他的仓房里过夜。那水手说不行。所有的仓房和床铺当晚都要进行一次彻底地清洗,天亮之前不允许乘客上船。那人转身离开了码头。等他走到街上后,这孩子才发现,有个穿得像技工的人走在街的对面,显然是在跟踪那个水手。水手在附近一个饭馆门前停了下来,然后走了进去。这孩子当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就混在别的孩子中,看橱窗里的好吃的东西。他发现那个技工也像他一样,仍在街对面等着。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慢慢地开了过来,停在那技工站的地方。那孩子只看得清,马车里有一个人,凑到窗口对那技工说了几句话。他描述的那个人,布莱克先生,有一张黑脸,像个印度人的脸。”
这一次,看来我和布莱克先生又犯了一个错误。留黑胡子的水手不是那些印度人派出的探子。他会不会是那个拿了钻石的人呢?
“过了一会儿,”探长继续说道,“马车又继续慢慢地往前行驶。那技工过了街,走进了那家饭馆。那孩子一直等在外面,又饿又累,随后他也走进了那家饭馆。他口袋里有一个先令;他对我说他大吃了一顿,有黑布丁、馅饼、还有一瓶黑啤酒。还有什么一个男孩不能吃的?这问题从来也找不到答案。”
“他在那家饭馆里看见什么了?”我问道。
“哦,布莱克先生,他看见那个水手坐在一张桌子旁看报,那个技工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边看报。天黑后,那水手站起身,离开了那地方。他走到街上后,警惕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那孩子(因为是个孩子)走过他身边时没被注意。那技工也出来了。那水手边走边环顾四周,显然拿不准下一步该往哪儿去。那技工又在街对面出现了。那水手一直走到通往泰晤士下街的海滨大道。他在一幢标有‘幸运轮盘’的小酒店前停了下来,打量了一下之后,走了进去。鹅莓也走了进去。酒吧里有许多人,大多数都是下层人士。‘幸运轮盘’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布莱克先生;以它的牛排和猪肉馅饼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