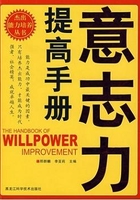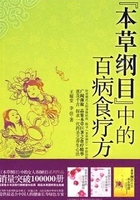张元济(1867~1959年)出版家、目录学家。浙江海盐人。20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董事长。建国后,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创办《教育杂志》等多种刊物。著有《涵芬楼烬余书录》、《校史随笔》
张元济是20世纪前期的文化人、大出版家,“百日维新”后,在上海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出版业,既是教育界著名人士,又是位企业家。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元济入京会试中进士,后曾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主办通艺学堂。参加过“百日维新”变法运动。受到光绪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参与主持商务印书馆近六十年,并曾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南洋译书院院长。
喜读西学,孜孜不倦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十岁的张元济出任总理衙门(相当于外务部)章京,专门处理涉外事务。那个时代普通的读书人,特别是已有功名的朝廷官员,愿意了解西学接受新知的人还不多,张元济在其间可谓突出者。他喜欢新书,常开列书目,交由总理衙门购进。由于新书缺乏,他还向上海的友人了解上海售书的情况,函索书目,尽量订购新书刊及关于政事的英文书,拟自己尝试翻译。
作为倾向维新的人物,他读书注意的是知识意义上的启蒙。他认为“自强之道,以兴学为先”,深知改革绝非易事,一切还得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他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和政治社团,而是积极筹建新学堂,自觉承担起“醒人救人”之责。从那个时代起,他读书精力已由长久埋首于传统经籍,转向时务西学,攻英文,“读公学,兼公法”。后又与诸好友设馆教授英文,甚至自己也迁寓学馆,发愤攻读英文。这所教授西学的学堂,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
张元济喜读西学,兴办通艺学堂寄托他“英才教育”的事业和“醒人救人”启迪民智的理想。晚年他在写给商务印书馆同人的一首告别诗中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从中可看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毕生尽瘁的事业深深的挚爱和眷恋。
博览群书,重视“修身”与“合群”
张元济读书同他从事的编纂、出版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他博览群书的嗜好反映在他所编纂的教科书与翻译的西文图书上。他主持商务印书馆不久,即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代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和《各国国民公私参考》等,还推出了政学丛书、历史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传记丛书、哲学丛书等。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名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为旧中国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尤其以严复所译名著《原富》、《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真理》、《名学浅说》等和林译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影响最大。读书界、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张元济读书之广,对西方名著和先进思想的热忱由此可见。
张元济认为读书人仅拥有新书、新知,而在人格上东倒西歪,这样的读书人仍然是不成功的。他提倡知识与道德并重,并躬自实践。20世纪初,他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一套《最新修身教科书》,说明他把读书与重视修身合群看成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他认为,重视修身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一种教育传统,《礼记·大学》讲:“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当然修身的内容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他认为修身除了激励自信、自立、自强,坚忍不拔、奋发向上外,还要“戒迷信,勿信鬼神”,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团结友爱,勤俭节约,讲究卫生,热心公益,廉洁奉公,急公好义,公平正直,奉行平等、博爱之道。他指出,人与人之间是有“智愚强弱,贵贱贫富”之别,但同样是人类,自然都有不愿受欺凌之意,不要因为人有贫富贵贱而厚此薄彼,甚至以我之智强富贵凌彼愚弱贫贱。他认为,人有了“博爱之心”,然后才会有慈善之事。
所谓“合群”,是19世纪末传人中国的“群学”(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群是与独相对的,独是寡而无助、弱而无力的,要有力量就只有合群。“人之群,以国为最大”。一个国家如果人人各顾各的事,一盘散沙,“不能合力的为国”是没有力量的。他认为,国家的存亡与否,系于国民爱国心之厚薄。“一国之中,无论为士、为农、为工商,必人之有爱国之心,而后国将亡而可存,国虽亡而可复”。“今诸生皆为中国人,则必对之以爱父母之国,无论此时在校,即一时留学他国,亦必时时以爱父母之国为心,而永久不变”,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国民”,才算得上“爱国之国民”。因此博览群书,吸收西学必须明辨是非,重视修身与具有爱国之心。
饱览古书,抢救古籍
张元济退休后,一头扎进故纸堆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古籍抢救和版本研究。他为商务主持编校、编印的主要古籍有:《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续编及三编、《续古逸从书》、《道藏》、《续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初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孤本元明杂剧》等等。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套古籍丛书的整理与校勘就足以不朽了,张元济做成了如此惊人的文化伟业,实属不易。顾廷龙曾由衷地赞叹道:这是现代出版史上绽放异彩的大事。
1928年,为了抢救和研究古籍版本,张元济东渡日本访书。抵达后访问了日本各公私图书馆,如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及京都东福寺藏书楼等处。一个月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公私图书馆内所藏丰富的中国旧籍。每到一处,都商借摄片,并雇佣日本摄影师用特种相机将书按页摄成小胶片,然后带回上海影印出版。他不仅查清了日本中国古籍收藏的详细情况,而且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搜集、校勘、影印出版古籍善本,目的在于流通古籍,以最完善的形式保存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他还耐心说服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成员们,斥巨资建造涵芬楼,并于1926年更名为东方图书馆,正式向社会开放。他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说,早年在商务不图名,不图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商务印书馆培养的各方面人才,都受过涵芬楼丰富藏书的滋养,像张明养、沈雁冰这样的受益者,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凝聚着张元济一生的心血和期望,也折射出他与书结下的不解之缘。
周荣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