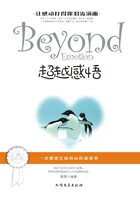陈独秀(1879~1942年)学者。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多种刊物。后从事文字学研究。后人辑有《独秀文存》。
20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中国的浮沉兴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国文人形象。他的一生,从“酒旗风暖少年狂”,到“笔底寒潮憾星斗”,再到“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令人深思感叹。但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他终究要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上占一席之地。
陈独秀豪爽、机敏、善谈、喜辩,话锋所向,鞭辟入里,对于读书治学,也多有宏论妙语。
现在许多翻译的书,读它如读天书
陈独秀出生在诗礼之家。从他的父辈上溯,“习儒业十二世”,即使在太平天国时期,也未使“读书种子”断线。陈独秀很早进学,十八岁那年考取了秀才。二十岁,即1898年他人杭州求是书院,在此受到新式教育,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1901年,二十三岁的陈独秀赴日留学,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探索与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新闻、文学、人口、戏曲、文字、小说和诗歌等。他参加或主办的报纸、刊物有九种之多,如《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无产者》、《火花》、《热潮》等,他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考据最感兴趣,终其一生都研究不辍。
陈独秀力主治学要实事求是。他在谈论读书时曾特别提到哲学家尼采。他说自己以前道听途说,以为尼采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在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尼采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他说,所以读书要自己钻研,决不能以耳代目,道听途说。
陈独秀懂日、英两种文字,看外文著作喜读原著。他对当时翻译过来的书曾大发议论。他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它在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他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胡译乱译,还美其名曰“直译”。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A、B、C、D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做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着启蒙作用。现在哩,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决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直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辅以意译,我意直译意译应相辅相成,决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
陈独秀还研究诗歌,他认为诗歌是一种美的语言和文字,恐不能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诗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怀,诗的腔调等等需要去琢磨。决不是把要说的话,一字不留地写出来就是诗。他说自己不提倡也不赞成青年人学作古诗,因为古诗讲究音韵格律,有人穷毕生之力,也不能运用自如。要么严守格律,写出来的东西毫无生气,要么破律放韵,仅求一句之得,据此而求千古绝唱,难矣。青年人想写诗,最好先读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了解一些诗味,然后动笔,想来会有进益的。
在狱中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解字》
陈独秀一生的精力,“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不过,他对政治的介入是以学术研究为先导的。陈独秀热情赞扬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这本书曾在当时风靡世界。他说:“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存已无数,可以逆睹。”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把“革命”亦理解为进化方式的一种。这在我国20世纪有其独特之处。他对经世、教育、学术、立身等方面的看法,亦无不以进化哲理为指导。
陈独秀对文字学的研究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有详细描述。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狱中监视颇严,不准读书看报,后经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濮清泉写到他在狱中的生活: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说文解字》)。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他说到:“中国过去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原著和段玉裁的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他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谈到“六书”(即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濮清泉认为古之文人也会创造别字、错字。转注、假借不就是当时没有的字就转借来用吗?陈独秀认为这个意见很新鲜。他说,“我研究文字学。就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主张语言文字都大众化,由繁入简,最后目的是拉丁化即拼音文字,不过在这方面只能促渐变,不能来突变,如果来突变,那就要大家读天书,任何人也看不懂”。
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起互道钦佩,继而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不久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好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盒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隔了一会,两人又和好了,陈独秀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
陈独秀的书法相当挺秀,他能写好几种字体。有许多人请他写字。他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希望学校多购参考书
谈到学习,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中讲,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列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唯第一目的,始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日,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日,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日,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许多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晚年僻居四川江津,病逝时院子里还剩下一堆自己种的土豆没吃完,但台静农回忆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说他从容谈笑,读书写字,文化趣味不灭。他有这样两句诗: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王晓临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