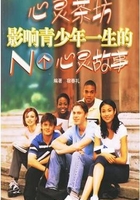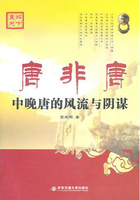仲夏的一天早晨,斯佳丽坐在卧室的窗口,忧伤地望着大车和马车,满载姑娘、士兵和陪伴,兴高采烈地顺着桃树街驶去,为当天晚上筹款资助医院的义卖会到林子里寻找装饰品,去采摘绿叶,去野餐,去分西瓜吃。
作为一个寡妇,斯佳丽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
斯佳丽想去,真的想去,很想很想。
斯佳丽为了准备义卖会的货物,比城里哪个姑娘都加倍卖力。她编织过袜子、娃娃帽、羊毛披肩、围脖等,还绣过六个沙发套,上面绣有南部邦联旗帜。辛苦是辛苦一些,但斯佳丽从中获得了乐趣。
看着别人为义卖会忙碌,斯佳丽不得不袖手旁观。唉,她死了丈夫,隔壁房里又有个娃娃在啼哭,她就活该不得享受一切乐趣,这真不公平啊。就在一年多一点以前,她还在跳舞,还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而不是这身老气横秋的深色丧服。她还必须对别人不能太热情,也不能把手招得太起劲,对别人笑的时候还不能露出酒窝,明明心没有死,却要摆出一副心如死水的样子。
佩蒂帕特爬上楼梯,照例爬得气喘吁吁的,一头闯进来,这时斯佳丽正频频冲外面点头招手,见了佩蒂帕特,冷不防停了下来。
“宝贝儿,你发昏了吗,竟在自己卧室窗口向外面的男人招手?斯佳丽,我简直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是不是太轻浮了?”
“人家不知道这是我的卧室啊。”
“可是人家会猜想这是你的卧室,那还不是一样坏事吗?宝贝儿,这种事千万做不得。人人都会议论你,说你放荡……总而言之,梅里韦瑟太太知道这是你的卧室。”
斯佳丽一点也不想待在屋子里,她都坐腻了,而佩蒂帕特的话只能是火上浇油。那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升到斯佳丽的喉头,她哇地一声哭起来。
佩蒂帕特以为斯佳丽是在哭已故的查理。
在斯佳丽的哭声里,那些车轮声和欢笑声终于消失了。
玫兰妮急忙从自己的屋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梳子,她的头发还没来得及梳。
玫兰妮慌张地走到斯佳丽的跟前:“心肝儿,怎么啦?”
“查理!”佩蒂帕特说,她也哭了,并且一头扑在玫兰妮肩上。
见斯佳丽如此重情重义,玫兰妮嘴唇都颤抖了,她安慰斯佳丽说:“亲爱的,放勇敢些,别哭了。”
斯佳丽已经扑在床上,索性放声大哭,哭她失去的青春,哭她无缘享受的青春乐趣,从前她想要什么只消一哭便到手了,如今再哭也没用,她就怀着这种愤怒而失望的孩子心情哭着。她脑袋蒙在枕头里,径自哭着,双脚蹬着有流苏装饰的床罩。
她为什么要为查理哭?凭什么?斯佳丽既气恼,又夹杂着样样享受被剥夺的凄凉心情,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幸亏这样,因为她要说得出口就会像她父亲那样直率,大声说出真情来。
玫兰妮拍拍斯佳丽的肩膀,佩蒂帕特吃力地踮起脚,拉下百叶窗。
“别拉!”斯佳丽从枕头上抬起红肿的眼睛,大喝一声,“我还没死呢,你不用拉上百叶窗。你们都走开吧,别管我!”
玫兰妮和佩蒂帕特交头接耳了一下,就踮着脚出去了。她们还是坚信斯佳丽这样为的是查理。玫兰妮甚至希望姑妈在斯佳丽面前不要提查理的名字。
斯佳丽闷闷不乐地在屋里一直待到下午,那时看见去野餐的人回来,大车上高高堆着松树枝、藤蔓、凤尾草,她心里也高兴不起来了。大家又一次向她招手时脸上都露出愉快的倦容,但斯佳丽只是郁郁寡欢地回礼。
午睡时间,斯佳丽万万没有想到梅里韦瑟太太和艾尔辛太太上门。她们的到来,使斯佳丽终于有机会去参加晚上的义卖会,因为正是她们建议斯佳丽和玫兰妮一起去义卖会场看管货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