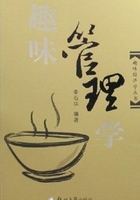那时我奶奶还活着,她是大家庭里的首领,环绕着她的有大伯一家、三叔一家、三姑一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家人丁兴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各家住的平房小院,冬天堆满取暖的煤块和木柴;夏天栽种着向日葵、茉莉花,挂着竹门帘,门口摆一张小方桌,和小马扎、小板凳。黄昏时,下班的人推着自行车“叮里当啷”进来了,往小桌前一坐,女主人就端上清凉的绿豆汤和饭菜,孩子们也围坐过来,一派温馨画面。
晚饭后,孩子们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疯玩,他们下河游泳,那时的大河小河里的水都比较清澈,比较安全。我哥跟着亲戚家的哥哥去游泳,或去小河沟里逮蚂蚱,到工厂俱乐部看“宣传队”的演出,没有人要票,那真是孩子们的嬉戏乐园。
当小院被夜色笼罩时,女主人已经洗好了锅碗,沏上一壶茶,摆在小桌上。大人们边闲聊,边乘凉。为了驱蚊子,女主人会点燃一把蒿草,屋里屋外都不点灯,就摸黑坐着的,唯一的光亮就是天上的星星。我在奶奶家,或是大妈家住着时候,一到晚上,就是这样的情景,我就特别想家,并非想念父母,而是天津家里的热闹。那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一到晚上家家的灯光亮亮堂堂,炉子上烧水做饭,不到夜深不熄火。女人们坐院子织毛衣,唠家常,男人们打着大蒲扇,聊着“国家大事”,一样也是乘凉,大城市到底和小城市的风景有些不同吧!
四十多年前的唐山,在我的小时候记忆里,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空气里裹夹着细细的煤屑的小城市,人们的穿衣打扮,日常用品,都比天津要落后,所以在老家人眼里,天津是个大码头。我的衣服只能用“朴素”形容,可老家人一见到我,就忍不住地夸我的皮肤白,衣服洋气,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可接下来几天,看到我的同辈哥哥姐姐,个个皮肤粗黄,衣着发型土气,我就飘飘然起来。
我对老家既新鲜,又厌恶的纠结,一到了三姑家即刻烟消云散。我有三个姑妈,二姑远嫁乡下,我从没去过。大姑和三姑住在唐山市里,大姑家都是男孩,她脾气暴躁,家里邋里邋遢,我很怕去她家。我喜欢去三姑家,那时三姑家的日子过得红火,住房敞亮,干净整洁,小院里的葡萄架果实累累,我整天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看书,恍惚觉得自己也成了书里的“小姐”。
三姑家的表哥表姐,个个风华正茂。大表哥在部队当连长,一见我,满口马恩列斯毛,打倒美帝苏修!似乎祖国的未来都压在他的小肩膀上。二表哥最像三姑,帅气英俊,是宣传队的台柱子,总有女同学羞答答地找上门来,二表哥冷傲得像“张国荣”,对追求他的女同学不理不睬。大我五岁的表姐,和我最要好,她的身材和伶俐很像三姑,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五官和三姑夫似一个模子拓下来的。地震之前的两年,是表姐的幸福时光倒计时。
她在乡下插队选调回城,先在商校学会计,毕业后分到钢厂工作。大表哥还把自己的部队战友介绍给她,结果一见钟情,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战友复员到了开滦煤矿当了工会干部,令人唏嘘的是,就在婚礼将近的日子里,大地震的死神捷足先登,结束了表姐二十四岁的如花生命。
我从小就喜欢“人生如戏”,何况是“血色浪漫”的爱情故事。表哥和表姐的爱情,不知不觉地演绎成了我的成长启示录。
但表哥表姐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母亲——我三姑比起来就显得苍白、稚拙多了。我没有见过三姑年轻的样子,只在她的照片上见过,美得不可方物。我见她的时候,她已人到中年,还是苗条轻盈,五官清秀。那是讲究朴素的年代,她的穿着一般,冬天蓝布棉罩衫,夏天细布格子小褂,可穿在她身上,似乎就成了时装,那么合体,那么富有诗意。
三姑从小就是个美人。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叫她“小周璇”,模样像大明星周璇,嗓音也跟周璇一样甜美,她爱唱歌,可惜家境衰微,大人哪有心思留意女儿的艺术天分?!
三姑十六岁就被一个其貌不扬的小男人追得昏天黑地, 他一天一封情书,用几粒糖块贿赂年幼的我三叔,让他转给三姑。奶奶也看不上他,可日渐败落的家境,病入膏肓的爷爷,让奶奶难以招架,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婚事。那是解放前夕,十七岁的美丽少女,坐着一顶破花桥出嫁了。婆婆家一贫如洗,饭都吃不饱。
万幸的是,唐山解放了。华新纺织厂招工人,三姑拉着姑父去报名,双双被录取。这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外表却像是妙龄少女,梳着两根大辫子。很快她就成了工友们公认的全厂“五朵金花”里最漂亮的一朵。她在车间当挡车工,车间主任,甚至厂长都爱到她的机器前转悠,就为了多看她几眼。姑父是维修工人,见老婆这么招眼,醋劲十足,就逼着三姑辞职,说宁肯饿肚子,也不能愿意她给自己戴绿帽子。三姑坚决不肯,三姑夫就打她,她就哭着跑回娘家,可刚回到娘家,姑夫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追来了,又是求饶,又叫俩儿子下跪,三姑心疼孩子就回去了。没多久,三姑夫又吃起干醋,再次逼她辞工,她不肯,于是又动拳头打她,她哭着跑回娘家,这幕闹剧,后来成为我三叔对自己少年时的深刻记忆。
三姑始终不肯让步,姑父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她照样上班,在大家面前永远是笑靥如花,她年年被厂里评为“劳模”“生产标兵”。五十年代,厂里就因三姑的突出贡献,分给她一间职工宿舍,他们一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我的父母结婚后,父亲带着母亲第一次回老家见婆婆和其他亲戚,就是在三姑的新家吃的喜面。母亲只比三姑小一岁,也是纺织女工,两人特别有共同语言,每次见面,两人睡在一条炕上,聊到半夜。
三姑妈是五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职业女性,在她的一餐一饭、一针一线的母爱之下,五个儿女健康成长起来。她的家永远是干净整洁的,粗茶淡饭,永远是定点开饭;亲戚来了,不管饥馑年代,还是票证年代,三姑永远面带微笑,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她谈吐幽默,处事伶俐,我的憨直的母亲,下辈子也学不了她。女孩的成长是需要榜样的,三姑对我的潜移默化,要比我的亲生母亲大得多。我的洁癖,我的处事灵活,我的以柔克刚,我的女性温柔,大都是来自三姑的熏陶和影响。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三姑失去了她心爱的长女,还失去了和她打了大半辈子架的姑父。那一年,她四十七岁,已经当奶奶了。所有人都以为,三姑从此形单影只,或跟着儿女,委曲求全。可三姑却做出惊人举措,地震后第二年,她就再婚了。新姑父和她是同事,老婆孩子都在地震中丧生,得知三姑幸免于难,就向她求婚,态度决绝。儿女们一致反对,理由是你都当奶奶了,一双儿女还没结婚,你就改嫁一走了之,是不是太自私了?!
一向和睦的母子关系陷入冷战,三姑病重发高烧,儿子媳妇连面都没露。这更坚定了三姑再嫁的决心。1977年的阴霾冬天,三姑和新姑父来天津住了几天,就算旅行结婚了。她依然娴静,爱美,爱清洁。我观察她,时不时对着我家墙上的小圆镜子,梳梳头,涂涂口红。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经历过命运重创的女人,丈夫、女儿、小孙子一夜之间都被死神掳走了,她被倒塌的房子砸成重伤,被解放军的飞机送到沈阳医院,才捡回性命。
“活着,就要往好处活,自己幸福了,别人才幸福,他们以后就会理解我的选择!”三姑这么诠释她的再婚,以及劫后余生。
今年三姑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和后老伴相依为命了三十多年,老两口一直单过,比她小好几岁的姑父,从始至终把三姑奉为“女神”,他服侍她,崇拜她,从来不吵架拌嘴,谁说半路夫妻就没有爱情?!老两口有自己的房子,有养老金,衣食无忧,他们的家仍旧是亲戚们的聚会中心,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三姑,还是那么好客、开朗。我去看她时,她还和从前一样,对我的穿衣打扮,饶有兴趣,摸摸这,摸摸那,跟老小孩一样。
三姑像是一朵绽放在废墟上的玫瑰,她柔美却不失坚韧,生命的智慧也正如此。
2014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