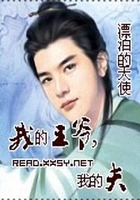帝顺闻言转头看向云凤弦道:“凤兄莫看凤源兄这般清狂,实是天下间难得的情痴之人,他与夫人……”
“莫说我的闲话了。”凤源浑似无意地打断了帝顺接下来的话,“琥珀姑娘的画舫亮起迎客之灯,我们这等俗客,切莫叫主人久等了。”
画舫之上,宾客十人,舞姬十位,客人分席而坐,美人居中做舞,清音曼舞,果香酒醇,极尽享乐,令人顿生此生何求之感。
只是此时,纵美酒置案,美人在前,不见仙子,又有谁能安然享乐,还不是东张西望,苦苦期盼。
在场众人大多相熟,皆是山海湖城中世家公子、大人物,见面打起招呼,热络做一团,说说笑笑间,又忍不住期盼起琥珀快快出现。
就连云凤弦都隐隐的期盼。
唯有风紫辉始终沉静默然。
凤源犹且自饮,更大声品评歌舞。虽然一动一静,正好相反,却又不约而同,表现出相同的淡漠平静。
“凤源公子依旧是千金座上疏狂态,诗酒风流轻王侯。”清柔低媚的声音带着音乐般的韵致响起,衬着珠帘掀起明珠相撞声,这声音,却比珠玉相击,更清美动人。
明彩烛影中,雪衣飘然。只一眼看去,只记得那清眸倦眼,风华逼人。她依然是一袭白衣,不扎不束,清淡得连一点装饰的丝带也没有,宽松得仿佛衣裳都随着她的步伐而飘动,却偏偏让人感觉到她身姿楚楚,步步生莲。乌发不再披散下来,也只闲闲挽了一个髻,甚至还有几丝散发垂落飘乱,却有一种独属于她的慵懒。
她每一步行来,便是一千种风姿,悠然一回眸,清清眉眼,倦倦神情,顾盼间似红尘万丈,三千繁华,都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
云凤弦怔怔地望着她一步步行来,目不能转,眼不能移,恍似石雕一般,却惊觉一只手伸到面前,手中握着一方丝帕:“擦擦嘴吧!”
云凤弦一愣,却见楚韵如手握丝帕,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再复忆起这番话,心中徒然一惊,莫不是真看得呆了,竟把口水流出来了?完了完了,形象全完了。
云凤弦忙干笑着一把接过:“是刚才喝酒时弄湿的。”伸手一摸,却觉嘴角一片干燥,原来根本不曾失态。
古奕霖低笑一声:“此地无银三百两。”
云凤弦只觉面红耳赤,不敢回嘴。
二人低声笑语,琥珀却拂衣缓步,到了古奕霖面前:“清音雅乐,必是姑娘无疑了,”
古奕霖虽对琥珀原本是极是好奇,又爱那一舞倾世之美,只是见云凤弦为她的姿容所动,心中未免有些不自在,但此刻见琥珀倾身施礼,动作优美如舞,声音清美如梦,却也不免喜爱,忙忙还礼,却又忍不住细细端详道:“真真绝世风姿,我见犹怜。”
琥珀悠然一笑,小声道:“姑娘眉目如画,何尝不是绝世风姿。”云凤弦心中暗笑,古奕霖真是男生女貌,见他的表情尴尬忙站起来岔开话题:“在下凤翔,来自京师,久闻姑娘芳名,特来相会。”
没想到这一声才报出来,就听到一声冷笑:“原来你就是凤翔。”
云凤弦应声转头望去,见一旁席上,一个年轻男子挺身立起,眉很浓,目很亮,个子高大,长得极是英武,手自然而然摸向腰间,摸了一个空后,想是忆起来见伊人未带兵刃,所以冷眉利眼,狠狠瞪着云凤弦,十指缓缓伸屈,指节竟响起咯咯之声。
帝顺一阵头皮发麻,干笑一声,急步走到二人之间:“我来介绍,这位是和道盟尘先生的独子,尘洛冰尘少侠。”一边说,一边背对尘洛冰,用身子阻止他随时会扑出来的势子,一边对着云凤弦挤眉弄眼。
云凤弦这才明白,为什么这帮人上船之后,大多对帝顺打招呼,帝顺却不肯为自己做介绍的原故,想是为了避开冤家路窄的难堪,没想到云凤弦一时失口,终是把名字报了出来。
云凤弦倒也不怕惹什么尘洛冰,可既碍着帝顺,不愿让他难做,又不好扰了琥珀的宴会,一时倒为难起来。
尘洛冰冷笑一声:“帝公子不必着急,昨日帝家老先生即亲临相访,为我们说合,家父又亲口允诺不加追究,我自是不能不给帝家和琥珀姑娘面子,以前的纷争再也休提。不过凤翔公子大名如雷贯耳,昨日帝家老先生对你大加夸奖,今日既见了,总要好好亲热才是。”他口里说着不计较,身上散发的却是恨不得要将人千刀万剐的气势,一边说,一边大步向云凤弦走去。
云凤弦微微一笑,向前一步走向了尘洛冰。
古奕霖心中一急,想要挺身而出,但见自己一身绮装,怎好与人伸手相握……他心急如焚,用求助的目光望向自上船后就静静站在云凤弦身后的风紫辉,偏偏风紫辉恍似未见,目光清澈得可以看清天地间的一切,却又淡漠得恍似整个天地根本不在他眼中心中,更何况一个云凤弦。
他这里又急又乱,偏当事人云凤弦却像迟钝得一点也意识不到危机,满脸堆笑,连连说些客气抬爱之类的场面话,就把手伸出去了。
两人双手互握的时候,古奕霖一颗心几乎跳出胸口,耳边似已听到手骨碎裂和凄厉惨叫的声音。但最终除了一声闷哼,却什么也没有,而闷哼的人也不是云凤弦。
却是尘洛冰猛然松手,用左手握住自己刚才伸出去的右手,脸色铁青,死死瞪着云凤弦。
云凤弦满面讶然,满脸关切:“尘公子,你的脸色不太好,你的手怎么了?唉呀!莫不是被我戒指弄伤了?”她假惺惺地抬起左手,对着右手上戴着戒指的位置轻轻一拍:“我就是爱这琉璃漂亮珍贵,才镶在戒指上,虽说这石头有些棱角,也没关系,便是与人握手,只要人家不太用力,也不会被石头弄疼。想必公子是学武人,手劲大,一时高兴,忘了情,这么热情用力一握,反而让石头伤着了。都怪我太不细心,居然没想到先把这戒指拿下来。”
她这一番话说得又是惶恐又是歉疚,听得尘洛冰暗中直磨牙,哪里是什么琉璃,分明是一根针突然从戒指里冒出来,若不是他松手得早,只怕手心都给洞穿了。偏那针又极细,刺伤了人,竟是连血也不流出一滴来,就是要指责她也没有证据。
此时手心里一阵阵发麻,让尘洛冰意识到,那绝不是一根普通的针那么简单。一时又惊又怒,又气又恼,咬牙如磨,恨恨道:“卑鄙无耻。”
云凤弦听而不闻,还无比热心地道:“尘公子,我这块琉璃曾受过高僧祝祷的,若被扎伤后,还妄动肝火,恐伤性命。若是能静心休养,不动无名火,只需三日,便可恢复无忧了。”
尘洛冰本来惊怒交加,吃了这等暗亏,还待强提内力,不顾性命,就此一拼了事,听云凤弦这么一说,倒是一怔,若是休养几天便没事,此时拚命,岂不愚笨,但要就此收手,却又丢了颜面。
云凤弦拿起一杯酒,恭敬地对他举杯:“以前多有得罪尘小姐,就以此酒赔罪吧!”说着举杯就唇,大口饮下。
尘洛冰心中一动,左手食指微弹,一道指风几不可察地在云凤弦腰间笑穴处一撞。指风虽发得轻,不能真的点中笑穴,但也足够让云凤弦那杯酒呛住了。
尘洛冰原意只是要云凤弦被酒呛个半死,没想到云凤弦脸上一红,一张嘴,一口酒全喷了出来。尘洛冰躲闪不及,被云凤弦喷了一头一脸,大是狼狈,偏云凤弦还满脸关怀,一边猛咳嗽,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手忙脚乱地要帮他擦,偏是越擦越糟,酒渍污痕越是显眼触目。
云凤弦越是道歉不绝,眼神却越是暗含戏谑,四周的人虽然都不说话,想来也是在暗中好笑。
耳旁只听到云凤弦乱七八糟的声音,眼中只见云凤弦一双手忙前忙后忙上忙下地乱擦,尘洛冰的脸由青转白,由白变紫,由紫再变黑,真真七彩纷呈,精彩得很。就在他忍无可忍,就要大喝一声,不顾一切,出手把这混蛋大卸八块之时,琥珀突然开口道:“琥珀当真有幸,今日竟见到这么多贵客。既有京中贵客,又有城中才子,便连和道盟的英雄、帝家的少爷也都赏我薄面,且让琥珀置酒一杯,以谢大家。”
她话声清丽婉然,如春阳融冰雪,叫尘洛冰满心怒火,忽的消融,又见美人微笑,已奉了满满的美酒敬上来。
是男人都不可以在美人面前失态,更不能不给佳人面子。尘洛冰忙双手接过,一饮而尽。
只这一缓,原本即起的干戈便是悄然化玉帛。
琥珀感激地冲他一笑,美人承情,眉目生辉,多少君王倾国倾城,求的不过是一笑,既得佳人笑颜,尘洛冰哪里还顾得上去生气,只觉神清气爽,胸怀舒畅,皆是无尽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