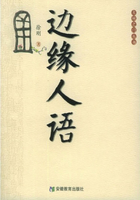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丹麦着名神学哲学家、文体学家。他是所有生存哲学思想家的鼻祖,是控明确地追求做生存式思考的第一人。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或此或彼》、《恐惧与颤栗》、《人生道路诸阶段》等。
当你的期待破灭时,那并非是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期待为你获得了一种现实,这个现实往往能使你猛醒。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你的期待便显得毫无价值。
——克尔凯郭尔
绝望与希望
我在一本旧的祈祷书里摘录到这样一句话:人类说的一切谎话,既有绝望也有希望。
我思想的命运和它们的实现很像是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里钓鱼——鱼儿轻轻地咬鱼饵——有很多鱼来咬鱼饵,可就是钓不起鱼来。
不幸的是,我真正的精神常常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我身上。
这几天,当我睁开双眼时,我仿佛是举起了很沉重的物体(昌出一大堆狂想),但随后又镇静了下来;我的希望也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可通过这扇门看到更加明亮的地方(我日常生活的环境和气氛就像在格陵兰的一个洞穴里的景象和气候,由于那个原因,很少有人光顾我冬天的住所,因为只有那些传教士才有勇气爬进这样的洞穴——希望,即天堂的传教士——几乎发不出一丝光线)一旦这扇门打开以后,它却不是一直敞开的,它也不是一扇慢慢再关闭的门,以便人们仍有希望在它关闭之前通过这扇门再偷窥几次;不,它很快又关闭了,可怕的事是人们几乎忘记了所看到的东西。
我总是在迈出绝望的一步的时候,就很快耗尽了那一点点我在辛勤的智力生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快乐的信心。
我之所以从生活中寻找到的快乐极少,这是因为当年对某事的思考唤醒了我的灵魂时,它的苏醒带有比生命更强的力量,以致我实际上是过度紧张了。就我而言,理想中的预见远不止于是对生命的解释,相反,当我与之分离时,我却筋疲力尽地发现某种等同于这种思想的东西。我的心太乱了,可以说神经极度衰弱。
有这样一些动物,只要有人望着它们,它们就不会吃东西,这些动物是以最奇妙而又狡猾的办法获取营养——我的心情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我看上去鄙视的东西,我会秘密地,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去吸取。
雨伞绝不会遗弃我;那样的事它曾做过一次。那是在一次可怕的暴风雨中,没有一个人理我,然后,我的雨伞张开了。我感到困惑,不知是否由于它的不忠实而遗弃它并变成了一位愤世嫉俗者。我对它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所以,无论是天晴下雨我总是把它携带在身。当然,这表明我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用才喜欢它,我有时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装成在室外的样子,一会儿靠在它上面,一会儿把它撑开,一会儿又把我的下巴放在它的手柄上,然后又将它移到我的嘴唇边,等等。
众所周知,在过去,人们只是一个字接一个字不停地写下去,一句接一句而没有标点符号。我们一想到阅读这样的书就感到头痛!可现在,我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写的东西只有标点符号,没有词语,没有意思,仅仅是简单的感叹和问号而已。
我的脑海就像是散了戏的剧场那样空荡和死一般地寂静。
什么是罪?邪恶的良心与魔鬼的契约——如像邪恶的良心所具有的东西那样,记忆又有什么呢?
你问我在这世界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是:我自娱自乐——你认为如何——我清楚地知道我干的职业与多数其他人的职业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你说我在恋爱,我不得不同意你的说法,但不会同意你要继续说下去的话,即:我应该结婚。我的爱情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激情,它需要做出牺牲。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与狂人谈话,并把我的手伸给他们。
有一天傍晚,我去剧场看了一场《Don Giovanni》的戏。我很少在这种场合与别人说话;我碰巧遇到一个人,他连续30年逢场必看这出戏。就这样,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握手,共同赞美这永恒的音乐。
你还记得第一次你偷偷去一个约会地点?当你隐隐约约地想到等待你的是什么的时候,你的心是多么的充实而又激动——你还记得当时你是多么盼望太阳早点下山?——你还记得第一次敲那小门吗?——你还记得第一次你匆匆忙忙去听《D·G》音乐会吗?你记得那彩灯是什么时候升起来而那段音乐还末开始?你记得第一次在幕后由指控发出的那三下敲打信号声?你记得第一次他曾用棒敲打三次吗?
有些野兽在有人观看它们时是不会进食的。
对于我来说,人生中不能容忍的关系就是在任何涉及到爱情的关系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具有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相对性。恰如自然学家把液体注射到动物的血管里,使它们俯首就擒,而且还能更加清晰地显露出那些静脉血管;同样,我把金钱注射到具有那种本性的每一种生命,由此而杀死它。人们在寒冷的天气会穿上厚厚的衣服,在战斗中会披上盔甲——我用金钱武装自己,旨在保护自己不受到所有那些人之间关系的偷袭。
当我赤裸着身体站在其中一个浴室里时,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门开了,视线一下子开阔起来,天空雾蒙蒙的,我与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关系,我一丝不挂地跳进水中。
我很富有——这是为了不让经济方面有所担忧和冷却我那发热的头脑;我总是微笑——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内心的哭泣和心灵上那令人窒息的哀叹;我有知识——这是为了我那受伤的心灵不会缺乏用来掩盖它的物质;我有众多的朋友——这是为了防止我只对一个人的信任。
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因此,人们常常也就变成一幅模仿它的漫画。我的理想是住在地下室里的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我可以追忆我童年时的身影,那时,他站在地下室的门口,沐浴在下午的阳光之中,嘴里还含着烟斗——就这样,我变成了一幅漫画!
一切悲痛都是幻想
一切悲痛皆是幻想。人们因为不相信他们应该尽职而悲痛,但因为这是传统和习俗,所以,悲痛会停止。倘若在悲痛的场合下发笑是一种传统和习俗,那么,每个人也应该那样做。只有在一个人的情形复杂得他用一种情感来掩盖另一种情感时,如果人们能看透心的话,也只有在那时,一个人才能真正看到谁在伤心,谁又没有伤心。
凭借努力而获得某种东西一定是件妙不可言的事;直到现在我挣得的惟一东西就是我散步或是骑马时从我身上流过的一种温柔的热情,那是多么令人惬意的啊!我不能说我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挣得我的面包钱,但依靠辛勤劳动,我挣得了我的血汗钱,这些钱给我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吃的面包是我的血汗钱,所以,面包给了我最大的好处。
我在广阔的世界里发泄我的痛苦——看看我是否能赶走这些痛苦,或者,回音是否能把它从我身上窃走,但是,回音对此又太过于有良心了。——我已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我的灵魂中,深藏在了世界的喧哗声中,把我误置于它的娱乐和欣喜之中——我把自己与自己缠在了一起。
当代的悲剧把喜剧融为一体,人们对此思考得越多,就越有可能排除那些统一在悲剧体中的悲剧和喜剧的区别。很显然,两者均依赖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错误关系,并且,人们力图减小悲喜剧两个方面的差异,即一方面是哭,另一方面是笑,但这种错误关系本身就明显是悲剧,由此成为悲喜剧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