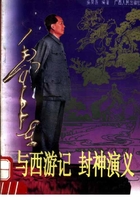“孩子啊,我们动作得快一点,把牝马弄进去。”他跟雷谛说。
“我说啊,尼尔思……劳你跑一趟去叫赛仁回来吧,他在田里挖萝卜。”
大约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一个沉静的男人在教区会议主席坚生家,那个著名的客厅里靠窗边处坐着。那男人高高瘦瘦、脸色苍白,身上穿着一件家庭裁制的衣服,是用那种最粗糙的手织黑布做成的,领子高高的、衣袖窄窄的。在他的外套外面有一个缝成的、藏钱用的黑色钱包,这种钱包在如今已经是难得一见的东西了。他腕上带有紧紧的赛璐珞制的袖口,这东西似乎把那血液都挤压到他那只巨大的手掌上了。
他向前弯伏着,把双臂搁在腿上,双手插在双膝之间。他的头有些平,和身高相比显得相当小。他的头发和胡子是灰红色的。他的脸显得扭曲变形,并散布着些微雀斑。
这个人完全静止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眼半闭,眼神呆滞,只一味直直地注视他的前面,这样子予人一种怪异的感觉,而屋里的那片寂静和透过湿气浓厚的玻璃窗漏进来的灰暗光线,更是加深了人们这种印象。平板的头、扭曲的嘴巴,以及浮肿的眼皮,使他看起来就像只在警戒中的山猫,从它在原始森林中的巢穴里在外观望,望那一片无垠空荡的平原。
他就是那个织工韩森。
这厅堂在往昔是最负盛名的,许多饮宴欢畅的盛会曾在这里举行,而晚近几年景况却完全改观了。擦得亮亮的桃花心木制的椅子,依然靠着墙排成一列,那镶镜的有屉立柜上,有一口镀金的钟,是位于两个轻披着折缀衣物的牧羊女石膏像之间,那钟滴答响着,似贵族般的高远清幽。但是,窗与窗之间的位置在以前放的是一张牌桌,是兽医爱格勒勒、鞋匠维林、八十多岁高龄的老校长莫天生(如今已过世了),以及他们的主人这一伙人,玩牌、喝酒共度了许多欢乐夜晚的处所;如今那里放的却是一张堆满了纸张的巨型写字桌。靠着另一面墙壁摆有几个书架,其内塞满了账簿、登记簿,还有一捆捆的报纸,使那房间的外观看来就像是个正正式式的办公重地。
事实上它也差不多是变成这么一个场所,而坚生他自己也发生了与此相应的改变。
农人阶级的启蒙觉醒所引起的政治风暴,以及晚近几年遍及全国都发生的这种暴乱,终于唤醒了他那昏昏欲睡的良知,促使他起而为自身的阶级之独立自主而奋斗。由于他是教区里最富有的农民,并且比一般农人来得慷慨大方,因此他很快地就在地方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另外也由于他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搞公共事务、从事政治活动的才具,和具有“能言善道的好口才”,他逐渐地使自己日渐活跃、地位显赫起来,在地方上成为公认的政治领袖,报纸上常可看到他的名字,被称为“末尔必的汉斯?坚生,著名的农民领袖”。
不过,要是没有那个最初在教区会众里鼓动叛乱的人的支持通过,他是不会获得这个领导地位的。而那个鼓动者即织工韩森。有几个人起初看到坚生这么突然崛起,曾担心这位顽强的织工如此被公然忽视、无礼对待,他会心有不甘、不肯罢休的;但这回却是让所有的人都大感吃惊,因为这位织工以异乎寻常的平静态度接受了那些。而且让人们大感惊奇的还不只是这样,因为后来人们发现,帮助坚生去搞公共事务、参与政治活动的,竟然是织工他自身。因为他曾向坚生指出——十分郑重其事地——在他的独立自主的情势下,于现任的会员老毕谢普退休后,他实际上对选区的全体选民是有义务提供服务的,而毕谢普的退休是为期不远的事了。
危险已经过去了,而“人民的主义”胜利,现在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那位织工自动地允许其他的人士享有他那多年来辛劳努力所获致的报偿和荣誉。带着某种程度的不自私——这使得会众们对他既惊奇又赞赏——他一年一年地变得更为沉默寡言,甚至于连大家为了酬庸他的贡献而提供给他的、最小的名誉职位他都辞谢了。开展会务、促进目的的达成上,他只负担一些属于老兵的卑微职务。他自动地担任信差的角色,并且协助各种委员会处理账目和通信方面的事务;他也继续忠于他在会众里所负的侦察职责——甚至比以往更为小心警醒,经常地突然出现于人们最不希望他出现的角落,脸上露着扭曲的微笑。
所有被召集的会员都到齐时,几乎快过三点半了。他们这几个人是所谓的“选举委员会”,会员有六名,是由教区的会众选出来的,他们的特别职责就是保护会众的政治权益、安排选举的集会、在促使演说者时间到时下台、保管选举人的名册,并处理和其他重要民主团体之间的往来事务。
他们全体都到齐之后,坚生自隔壁的一个房间走了进来——穿着白色的简便衣着,一件苹果绿的厚绒布背心,系着一条金链,一块浆硬的前遮布,由于中午打盹小睡的关系,突出于背心外面。他走过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说:“日安,欢迎光临”;于是他们在他的邀请下,围绕着房间中央的一张椭圆形桌子,一一坐到他们的椅子上去。他们似乎都怀着一种颇不寻常的严肃心情。几个会员在坚生还没有进来前曾问那位织工,这次集会是要干什么;经由他语意不明的回答,他们推测这次集会应当是非常重要的。
屋子的主人、委员会的主席,在坐席的主位上坐了下来。他的体态厚重,头发卷曲,下颏理得光光的,这使得他看起来很具有威严。当然啦,他的长而下垂的鼻子同一向那样是紫色的,脸孔也同样是红色的——他们让人联想到过去,令人着恼;但是他也得到了补偿,因为他的态度、他的动作,和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让他显得平易和蔼;这与公众服务生涯里的惯见的态度、作风,是相配合而不至于格格不入的。
伊曼纽坐在主席的右侧,这时他已脱下工作服换上了一件轻便的灰色外套,他再过去是一个矮胖的末尔必农夫,眉毛浓密、脸圆圆胖胖的。主席的左边是两名金发的、年轻的斯奇倍莱农夫,右边有那个高大的木匠尼尔生,他留得一把海盗胡子,几年来长了好几寸,其长也差不多及腰了。那位织工担任秘书的工作,坐于桌子的一个边角处。
“好,现在我们全都到齐了。”主席说,声音带着明察细究的意味,眼光逐一地望望他们。“各位朋友,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向你们各位报告……是啦,韩森请你开始吧!”
最后那句话是对织工说的,这时从他后面的口袋里抽出了一大叠文件,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后,以一种徐缓、单调乏趣的声音,他读了下列的宣言:
“机密文件。
从我们党的领导人物那里我们接到指令,要我们各个民主委员会,对最近出现于某些报纸的、令人不安的政治谣传,加以研讨一番。为顾及时机之迫切、事情之重大,我们认为应当及早将此消息告知当地的委员会,使其注意,不宜延误。消息内容主要是说,在上下议院里,政府和保守党双方可能有阴谋正在酝酿,预计图谋者将会激起每一个爱好自由的人的极大愤怒和焦虑不安。当然真相如何我们并不确知,因为那些谈判都是在极端秘密下进行的;但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在议院的辩论会里,部长们甚至在小事上也突然不愿让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来。如果将其他一些具有意义的事项也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此事似乎并非不可能!——政府确然与保守党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无顾民意,专断地撤消了全民参政权,来与平民对政府日渐增大的影响力相对抗。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忠于自由运动的人,都知道怎样去判断其是非对错的。
“因此,我们请求各委员会召开会议,并发出一个有力的通告,声明人民的宗旨绝不更改,更要竭尽全力来和当权者的不当措施相抗衡、周旋到底,以作为对议院里我党议员的支持。至于此事该如何处理,我们留待各委员会自行决定;只是,遵照我们国会里朋友的意思,我们奉劝要给我们的党员适当的时机,使其通过决议案,在争取人民的权利和不可剥夺的自由战斗中,继续不断地、给予我党议员具体而有力的支持。
“对各个委员会我们都发出了同样的恳求文件,希望这样的一个郑重声明,这样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全体一心、异口同声的对我们的敌对者的警告,可以使他们恢复清醒的神志,促使他们放弃邪恶的意图。
“自由与正义万岁!人民所挚爱的人!宪法的赐予者!永不会被遗忘,常在我们悼念之中的故菲烈王——在我们的记忆里万岁!”“PVB—提倡人,约翰生。”
这文件的内容在那会里激起了极大的骚动。甚至在还没下结论之前,伊曼纽就脸色苍ft,情绪激动起来,他终于爆发了:
“但那是叛乱的行为啊!那是叛国的行为啊!”
“是的,这个你没弄错……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没有不说这不是那样的一回事,”坚生插嘴说。挥动了一下手,并发出使别人听他讲话的声音。他继续说:“但是,各位朋友,在这个会里表明我们严正的态度,这表示我们完全做对了。他们只以吵吵闹闹争权夺利为惟—目的,甚至为了要达到此一S的,可以置国家的福祉与前途不顾;这样的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同胞了……他们是丹麦的敌人!”
“听着,听着,”声音来自那位木匠的胡须深处,像是一个沉重的回声。
“绝不……丹麦的人民绝不忍受这样的耻辱!”伊曼纽激动地说,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提议今天晚上就集合所有的党员,让他们知道这面临危险关头的事件。我们没有时间浪费。我们要同心一德地团结起来与之相抗,表示我们要竭尽全力来保卫我们的名誉和权利。”
“平静些,伊曼纽——平静些,”那位主席说,表示抚慰地把他的手放在伊曼纽的臂K,“首先我们必须当心别做的太过分了!最重要的是冷静,在政治上这样才能够行之久远!我们不要忘了,在目前我们并不确知任何事情,有句古老格言说,还没看到熊你不必举枪瞄准。所以,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至于我,我怀疑那些消息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只不过谣言罢了,是政府的朋友散播来惊吓我们在议院里的人的,也或许是个小型的试验气球,以观测民意,探究民情!我们得记住,政坛上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干出来的!”他继续着,言词浮夸、指手画脚地。“首先我们必须做的是,详究我们的敌对者所用的策略。各位朋友,可别忘了这一着!”
“但假使它们并不是査无其事的谣言呢……假使他们果真把他们所威胁的事情干出来呢——使国会变成他们的机构,以权势取代了公理、正义……那么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那位主席专注地注视了伊曼纽片刻。然后,充满自信地,把他的手重重的放在桌上,他缓缓地说:
“要是事情真是如此——愿上帝勿使其发生——则三十万国人将奋身而起,宣言道:‘他们做得够了!谁将是主人呢,是你们或我们自己呢,我们必须为这个问题而效命牺牲、奋斗到底……我说得对吗?’”
说罢,他转身对着那来自斯奇倍莱的农夫,而他们都报以大声的“好哇,好哇”,而那个矮胖的末尔必人则是表示赞许地点着头。
“现在我提议——下星期晚我们安排一次集会,届时我愿意负责向与会的人士说明我们当前的处境,然后我们将提出拟议中的决议案。并且我们要把这个消息加以保密,以免太过——或甚至不必要地——惊动了党方面。可敬的上峰委员会显然也认为事情应当如此。我们的对手,经由我们的各个集会,听到人民的心声后,他们对发动另一回合的交战会失去兴趣的,我对于这一点并不怀疑。我的朋友们,你们不同意我的说法吗?”
有四个会员表示了赞成,而伊曼纽为他们的勇敢无畏所感动,也终于变得较为平静了。他不惯于谈论政治方面的话题,而事实上,在政治会议里他之所以被选为委员,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有着卓越贡献。他对国会里的争论或报上的消息很不容易发生兴趣,更不用说对那位主席以及其他委员所津津乐道的“策略”、“战术”云云会感兴趣了。
他绝不会让自己怀疑正义的一方——如诗篇里所说的于“上帝所选定的合宜时日会胜利成功”,对那些要使时日快速些或迟延些到来的计策,纵使是最聪明智巧的,他也不相信会奏功生效。
在斯奇倍莱农夫当中之一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届时邀请两名来宾出席讲话,使那集会更显其重要性。有一阵子他们甚至考虑到要邀请一名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委员的人——老毕谢普。但是在最近一连串政治风暴的争论中,人们看到他在他的天鹅绒袍和外交家的外套下,依然穿着他年轻时代所穿的那种加里波底的红衬衫,然而迄今他却不会任他自己听从别人的进言,舍弃所谓的阿基米德立场——超然于两党之外的。所以这个想法他们旋即放弃了,因为那将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想他们可以说服另外几个民主党员,来参加那一次集会,并且立刻发信向总部报告。主席提出意见说他要以他的马车到车站去接载特别邀请的来宾,并招待他们吃饭——这个提议赢得了纷纷的赞许。
集会的时问确定了,韩森写好会议记录,于是主席宣布会议结束。
“好了,我们把那麻烦事儿摆平了,”他站起来,快活地说。“各位,折腾了半天我想我们该吃喝点什么了。”
他这样说指的是那“小小的饮宴作乐”——在这个屋子里不可或缺的,此时在隔壁房间里已准备就绪了。一个肥胖的农家妇女把那房间的门打开;那妇人戴着一顶绣着金线的便帽,鹰钩鼻,三重下巴,她是那位主席的女管家。
那桌席一如以往那样地摆设布置,灯光辉映下摆满了丰盛、精美的食物;那盏灯所放射的黄色光芒和夕阳无限好的余晖,相映并照耀。在那斑斓多变的光华里,那一桌筵席更显得格外地引人垂涎,在开会久坐之余早已饥肠辘辘胃口大开,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入席就座了。
甚至伊曼纽也轻松愉快了起来。他逐一地望望这些肩膀宽阔的汉子,尽管他们的未来受到了威胁,他们却安安静静、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对于他们的权利全然不忧不惧的。对这些总以这种平静如恒的态度去面对他们的命运的人,他不禁重新兴起了仰慕之情。
甚至他不会看过他们须臾之间失去了他们的沉着镇静。即使是在命运的最沉重打击之下,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有益于身心的宁静,一种他自身很难做到的、男子汉的自我控制。
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一会儿杯盘就空空如也了。而新的菜肴又一盘盘由“大希施”送了进来。希施自从坚生的妻子死后便在这里帮忙料理家事。这个胖女人一直偷偷地为那位织工所注意着;在这一顿饮食间他几乎是一言不发的,只是任由食物和饮料搁在那里,几乎碰也不碰的。他的邻座要给他倒杯白兰地时,他用手遮住了杯口,脸上露着诡谲的微笑——近来他变成了一个绝对滴酒不沾的戒酒者,不管坚生怎么开玩笑、作弄,他也不愿违规开戒喝一口,甚至在纪念庆祝日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