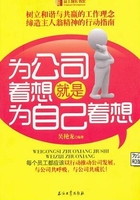“这样更好,这样,我有幸可以向一位同乡致意了。”这番谈话后,他又埋在报纸中。他脸上有自我满足、白我陶醉的样子。“他好像在咀嚼婚姻的乐果。”
乐果尝过后,红心老K指着报纸上少年维特的照片,“你认为如何?”他以忧郁的语调问。
“你相信今生今世还有这种无尽疯狂式的恋情存在吗?”
“在自然界!这是很自然的事。”维德顶撞似的回他一句。
红心老K微笑着,然后说:“不错,必须看一个人对自然界的定义是多宽广和多狭窄了。所以你真的相信--在我们写实的时代--”
“没有什么写实的时代。”
“若你要如此说,那就算了。但是你总得承认每个时代都有其潮流和方向吧?例如一个时代的特色在另一时代里就变得不可理喻了。早期的心灵状态在今日当然也无法理喻。您能想像--例如:施洗者约翰,或我们要坚持刚才学过的例子少年维特或穿着高领的圣芳济一喔,抱歉,我不是想冒犯你,不,真的,请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维德对紧张的红心老K安抚式的微笑后说:“我对施洗者约翰和圣芳济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圣灵是吃蚱蜢才会临身,忘形的境界说不定是由穿高领而来。我是宁可不信有这回事,但若我的消息正确的话:维特的创造者是位天性喜欢穿好衣服、矫揉造作、虚荣的人。”
两人之间有段长的沉默,维德脑海内有个想法,他愈等愈久,愈不能把这想法驱走。终于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您可不可能认识魏斯主任这个人?”这句话一出口,他就感觉浑身上下热晕晕的。
红心老K很惊讶地看着他:“当然!为什么?”
“他是怎样的人?他是什么样格调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长的什么样子?个子是高还是矮?是老还是年轻?是令人讨厌呢,还是令人愉快?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由他的头衔上猜得着他是位受过颇高教育的人。”
红心老K很愉快地笑。“像许多人一样。他也有很多缺点,同时,会可能,至少,我自己很自豪是有许多长处和优点,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魏斯主任。”
一切在很优雅、反讽,但可亲的情况下进行。维德是善于应付精致感情状态的人,他立刻在感觉之下伸出他的手。另一位也怀着相同的热情与他握手。友情的盟约在两人中发生了。
维德说出他的名字之后,主任高兴地说:“你显然就是今天早上到我家拜访的那位先生。我们很诚恳地向你道歉,并向您表示我们的遗憾。尤其是我太太,我相信,若我没记错的话,你们曾经在海边的游览胜地见过一面。”
“不是在海滨而是在山上的空气疗养地。”维德有点懊丧地说。
“不幸的是她必须再一次出门,不能来欢迎你。因为她和合唱团的妇女已有约在先。我才从车站回来,我希望您不至于因此失望。若你不介意我的侵扰,那,请您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理想社。您不要拘形式,就像您现在穿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还有,我太太是理想社的荣誉社长。”
“理想社?”
“喔!是的,我真健忘,您完全不知这件事。”说完之后,他以运动员起跳时的动作先后退几步,然后以飞奔前冲的姿势讲起这个社。“这是对我逝去的岳丈的追恩和缅怀。是轻松的场合,没有任何的拘束,没有固定仪式、服装和各种虚伪,也没有正式的晚餐,纯粹是要培养较有内容的社交活动,提升每个社员的精神领域。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可以得到充分的恢复(当然我必须说明二者是不互相冲突的)。这种场合自然有音乐,音乐是占极重大地位。--其参与的朋友,聚会的地点,以及如何安排聚会等等,通常聚会的日子是星期一、三、五。”
维德很注意地倾听他的话,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精神却凝聚到眼睛。他打量着,这位就是房子主人不在时照顾房子的人。为何他会胡思乱想把对方想成荒唐笨拙的人?这位红心老K完全不是那个类型的喜剧人物,他惊讶地注视眼前的人,屏住呼吸,几乎要昏厥了。现在你应高兴才对,他竟然是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一表人才的人。他是光荣骄傲的男子汉。维德发现一切都秩序井然,显然她是爱他的。其实,维德自认没有任何妄想。上帝禁止他有这种想法。相反的,若情况不是这样,那有一天,维德自认会有一大堆麻烦和困扰。对她而言,梦乡之会是无法追忆的。因为她竟然知道要来访之后还出发去郊外远足。这种作为毫无疑问证明这女人是一点羞耻心也没有。
“你也是音乐剧迷吧?”老K的声音在维德的脑海中回响,“或你喜欢音乐?是不是?”
“我相信如此,但我实在也不太清楚,还要看很多因素才能决定!”
教堂的钟声响起。
“三点了?”老K很快地站起来,“我讲话讲得忘了时间,我必须尽快赶到博物馆。--那么,我盼望,你能让我有机会在理想社欢迎你。”
老K犹豫地握维德的手后,很快地走了。维德在后巷徘徊,心情是绝望的。多少次,他告诉自己:“维德,你要快乐点儿。”但一点儿帮助也没有,他仍是受挫、失望。“刚才并没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呀!”但不论他怎样安慰自己,他的挫折感还是很重。他走过城市,直走到城外,他走累了,站在城外看着整个城市。然后,他才启程回家去。他把自己的身体安置在床上,四肢伸展,躺得他感到好过一点儿。这一切之后,他的身体祝他“健康”。
“谢谢你!同志!”维德的声音说。他是习惯性地称他的身体为同志。因为他和他的身体处在极和谐的状况下。
在他把身体伸展到满意的程度后,他注意到桌上的一封信。从自然情况来看,这封信躺在那里已经很久。这是石女士写来的一封信。
“你这邪恶的人,魏斯夫人并不需要在他人面前低下头。我会立刻赶来此地,斥骂你一番。”
“准备好防卫。”
“我不知道你竟是这样让人不愉快的人。”她一开始就突击,“坐在被告的椅上,自己反省吧。”
“你要向主任要什么?”
“通奸。”
“你再以较理性的语言解释一遍。”
“理性的语言就是我们说的,这是我的意思。不须再解释或翻译--”
“她破坏了婚姻--”
“我亲爱的先生,我必须严肃地与你谈一谈。”
“因为这牵涉一个没有瑕疵女人的名节,我深切相信我必须唤醒你的良知:你们有没有订过婚?”
维德精神抖擞地拔掉这像剑的语言。他没有回答。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有些爱情的证据,比如说订婚或和订婚差不多的仪式。这些至少会使你的结论正确一点--甚至一个爱的诺言?盟约?一个表征?一个吻?我怎么知道,任何事都可以。”
维德再次打起精神闪掉剑击。“没有!没有!没有!”
“你完全想错方向,只有交谈过两三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正巧坐在她桌旁,我们一起从花园中拔了一些草,她唱了一首歌,如此而已。”
“或你们有信件往来?”
“一封信也没有。”
“我摆不下我的尊严,另一方面她也很小心。女人常会忘情于鱼雁往还中。而且她们从不忘记她们所写的。”
“是呀!那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帮帮我这颗贫乏的脑袋来理解你俩之间的事。”
突然地,他变了脸。他的表情变成奇怪,深沉,好像见到鬼一样。
“一个在遥远梦乡的非常私密性的会面。”他的声音颤抖。
“很抱歉,我一直和你针锋相对,但我也从主任夫人那里听了一些事。而她是从不说谎--”
“我也不说谎呀!”
“再回来说说私密性的会面,我不是说肉体的接触。”
一点也没注意维德的表情,她搬动她的椅子,听到这句话之后,她立刻抬起头来瞪着他。“不是肉体的接触,我希望你不是说……我怎能了解这些事?”
“你的了解是正确的。这是灵魂和灵魂的结合!你冷静一点!我是正常的。我对四周的观察和其他人一样敏锐。你为什么有不信任的眼光?你相信人脑中空无一物会想得更多,还是饱学之士会想得更多?我的意思是指看到的幻象。”
“你相信幻象?”她像控诉似的大叫。
“像每一件事,比如你会有梦想,回忆,爱情的憧憬。在艺术家的心中闪电似浮现的意象。这些不都是幻象吗?”
“请不要诡辩,说正经的,回忆或艺术创作中,当事者仍很清楚他们的对象是幻象。”
“我是很清楚。”
“感谢神!你让我松了一口气,刚才你那样说,差点让我以为你所说的幻象会影响你的生活和行动。”
“事实上,这就是我正在做的,我是受幻象影响的。”
“不!你不可这样做!”她大叫禁止他。
他向她鞠躬。“F我很抱歉,但我已经做了。”
“但,这是疯狂!”她大叫。
维德笑着说:“什么是疯狂,告诉我?什么?外在和内在的经验中,我更珍惜内在的经验。我使自己变成内在经验所左右的人--意识?神?还有疯狂。当一个人在内在经验中受神或意识控制时是疯狂吗?”
她震惊了,一会儿之后,他的话语锤打着她的胸膛,但维德仍不愿放弃,再接再厉地讲下去:“惟一的不同是有人很清楚,但有些人迷迷糊糊不清不楚地盲日追随幻象。我必须看得很确切,像画圣母升天图的画家一样的确切才行。‘上帝的手指’、‘神的眼睛’、‘大自然的声音’‘命运的招手’--我怎能处理这些被肢解的四分五裂的博物馆?不论如何,我要全部的面貌。”
“没有勇气,没有胆量,”她失望地叹气,“你明明是在搪塞责任。这种精密、高深的想法,你比我这弱女人的脑筋强一百倍。在这范畴里,我不要有任何的牵扯。我对你的决定很遗憾,为你感到悲伤。”
维德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最最崇高的朋友,这是真的。你从来不了解我,你也从不让你自己明白我好意的暗示。为了证明索伊达和我有约在先。承认吧!你仍是有结婚、不结婚的那种想法--认为我摒弃人生的幸福是因为我害怕婚姻,看看你,你竟然在点头哩!”
“这是现在还无法看出来的。”她用比较和缓的语气说。
“不!我真的懦弱、胆怯,因为无法作决定就是胆怯,是意识上的胆怯。但我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无法忍受你错误的眼光。因此,我要告诉你我辩证的方法。你准备好了吗?”
“我对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她低下头,喃喃地说。
“我不必假装,但是谈这个题目对我是很痛苦。而且我也不明白唤醒一些老故事会有什么好处。同时--若你想要--”
“不是我要,而是我必须!”维德改变声调后开始说,“不是因胆怯,不是因愚蠢使我没有抓住机会。在幸福以轻柔的脚步走到我身旁对我轻语时,我没有及时抓住幸福。而是我知道我自己做的决定,我珍惜我婉拒的幸福,我的决定是在深思熟虑后,很困难的抉择。我的决定是种成熟,大丈夫气魄的决定。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抉择时是怎样的情况。”
说过这些话之后,维德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但是这一口气是伸延不断。她抬起头看着他。维德站在她面前颤抖着,嘴紧紧地闭着,因为内心中的暴风雨使他震撼不已。
“不!我不能对你讲我的故事。”维德终于很困难地说出这句话。这话实在太沉、太重,以至于他必须靠在钢琴上支撑自己。
“唉啊!”她很快地跳起来,以便能扶住他。
但稍过一会儿,他很快地恢复了。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知道我的决定是对的。若我有机会再站在这些决定之前,我也会做相同的选择。”他抓起他的帽子,握着她的手,并且在手上吻了一下。“我会为你把这一切写下来。”她深受感动,陪伴他走到门口。“好!只要说这些事就好了。”她尽量使自己声音不带感情,“好!为我,你好好地把一切写下来。”
“你知道,一切会令你感动的事我都关心,我相信,虽然我并不是永远了解你或甚至我误解你,但是对于你生命的真诚和勇敢以及智慧,我是从不怀疑的。”
“谢谢你,高贵的友人。”维德热情地说,手握着拳头。“你像甘霖一样治好我的心。”“虽然我已伤心至极,但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有崇高人格的人,会做这种事。”她心犹未甘,有点生气地大叫。
维德震惊了。他忧郁地回答:“没有人会做你想像的那种事呀!”这时,她挣脱他,很快地爬回楼梯上。“还有一件事,你不会不公平吧?你不会伤害她吧?”
他苦笑:“我不会伤害任何人,不会伤得比自己多。”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你是个危险、讨厌、不受欢迎、妨碍别人的人。”她在他背后低声地吼叫,一边把自己抛到一张软椅上,尝试恢复她已精疲力竭的身体。
总之,他走回他的房间写下他的忏悔。看呀!写作对他像是毒药一样,使他像中毒一样的难过。在自我反省时,他感觉有股贪婪的欲望从回忆中再度被勾起。为了要抓住他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为了保存他高贵的秘密,他要使自己的想法独立自成一格,变成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他咬着牙,抗拒着思考的逻辑,他愤怒地反抗各种逻辑式的想法,而以一种类似发高烧一样的犹豫不决想要一泻千里,振笔疾书。他写道:
给石玛莎女士:虽然空洞的散文体是对语文的大不敬。诅咒这种散文式的文体,但我还是必须用这种文体诉说我的故事。
题目:我的抉择时刻
今早收到你的信,和信中夹的索伊达的照片。这封指名要我收的信,再度使我的脑筋清醒。我确定我可以回答你的信,但长时间的犹豫会被误认为放弃写回信。我了解下一个警告会比这一个更激烈,但是我也了解我的日子过得极为严肃。今天做决定是必要的。我看着这张照片,许多有关索伊达鲜明活泼的影像又回到我脑海中。这张照片中的她也看着我。
在信中,你指明要我有个清楚的交代。而且你说对我任何回答,你都会很包容。但另一方面,我了解,任何的拖延都会被诠释为背信和放弃。我了解这样拖延只会使你的警告愈变愈激烈。
这一天是很严肃的一天。今天做个了断是应该的。我看着照片,千万个正义的表情从照片中回看我,她的眼光是被拣选处女纯洁的眼光,她因美丽和贞德而显得超脱凡俗--我们彼此都有很多回忆,只是这些回忆并不是共享的。在许多事件的接触之后,一切仍是没有结果(没有行动!什么也没做成)。除此之外,这一切仍是充满诗意,这时刻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她亲密的眼神,充满灵性地对我诉说: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无上的喜悦,终能赢得他的人是多么可喜可贺呀!在照片之后,我仍能读出隐藏不见的题字。这是最高的代价,你信中的字耳语着说:代价要付给你。
只要日常的琐事占据我的感官,我就会偷偷地看这张照片一眼(只是偶然偷看一眼,在匆忙中偷看一眼)。只是为了要沉浸到她深思眼中美妙的谜里,只是为了要尝尝女性美永不褪色的奇妙。我深深地陶醉在我心中的秘密里。
但有一天深夜,我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里,虽然在黑暗中我已无法看清她,我仍把照片放在我面前的桌上。我形容忧郁地注视着前面的照片。沉静、空旷的公寓中每间房间的门都敞开。在漆黑的大厅里传来鸽子咕咕的充满旋律的音调。还有吊灯亮起的房间传来梦幻似金丝雀在人工光明中所吟唱出的声音。我坐在那里,估量着我的命运,好像地球两极各自吹来一阵风环绕着我,但是在中心点,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你会被允准吗?伟大和幸福可以相提并论吗?我哀愁地反复思考这类问题。因我害怕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否则起初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庸人自扰了。我的心在感知这危机之后怦怦地像暴风雨一样地乱跳。为了你伟大的糖衣,你要牺牲我?问题是你何处伟大?丢给我呀!我要证据。未来的伟大?啊!谁保证你将来一定会伟大?这种未来太没有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