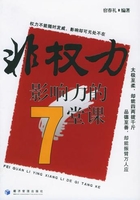四楼以上有晾衣物的顶楼,还有两个小间,分别住着干粗活的伙计克里斯托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除了七位住宿客人,伏盖太太不管年景好坏,还有八个法科、医科的大学生,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他们都只包晚餐。饭厅开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最多可以坐下二十来人。但上午只有七位房客,吃午饭时聚在一起的情景,颇像一家子。人人都趿着拖鞋下楼,私下议论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态和隔夜的事情,他们之间说话毫无顾忌。这七位房客是伏盖太太的宠儿,她依据每人交纳膳宿费的数额,对各人定下待遇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考量。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七十二法郎。这样便宜的价钱,库蒂尔太太是惟一的例外,只能在圣马塞尔区修道院和收容院之间的那个地段才能找到。价钱便宜说明这些房客大概明里暗里都受着穷困的压迫。所以,房子内部寒酸的样子,也反映在常客们的褴褛衣衫上。男人穿的礼服已经说不出是什么颜色,鞋子像是富人区被人扔在墙角的,衬衣快磨破了,衣服有名无实。女人穿着黯淡陈旧、染过却又褪色的连衣裙,旧花边后来补过,手套用得发亮,绉领发黄,头巾的经纬已经稀松。衣服虽是如此,人却差不多个个都很结实健壮,抵御过人生的暴风骤雨;面孔冷峻,就像不再流通的钱币一般模糊。嘴唇干瘪,却长着贪婪的牙齿。公寓的这些客人使人想起已经演过或正在演出的戏剧,并非那种脚灯前、布景间演出的戏剧,而是活生生的,虽然没有声音,冷冰冰的,但却把人心搅得发热,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小姐米旭诺,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个绿色塔夫绸遮阳罩,用黄铜丝箍着,脏兮兮的,准会叫怜悯天使吓一大跳。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似乎盖着一副枯骨,隐藏在内的形体是那么嶙峋。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形销骨立的呢?她当年一定漂亮风韵过。是荒唐、忧伤,还是贪婪?是情网陷得太深,兜售过脂粉服饰,还是仅仅当过烟花女?难道她年轻时春风得意,所向披靡,享尽欢乐,以致老来遭报,路人惟恐避之不及?她目光凝滞,看得人发冷,面容憔悴狰狞。她说话声音很尖,仿佛冬天将临时,灌木丛中的蝉鸣。她自称伺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以为山穷水尽而遗弃。老人给她留下了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每隔一段时间,继承人便为此跟她吵闹,说她坏话。尽管情欲摧残了她的面容,但肌肤还有某些白皙细嫩的痕迹,足见她身上还残留一些美的踪影。
波阿莱先生简直是一架机器。他沿着植物园小径走着,像一个逐渐伸长的灰色幽灵;头上戴一顶无精打采的旧鸭舌帽,手上好不容易才拿住象牙柄已经发黄的手杖,外套早已褪色,衣摆一掀一掀,露出几乎空荡荡的裤子;套着蓝色长袜的两腿哆哆嗦嗦,像个醉鬼;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色坎肩;皱缩的粗布襟饰,跟系在他火鸡般脖子上的领带不太相称。看见他这副模样,许多人都纳闷,这个皮影戏似的怪物,与意大利大街上翩翩而行的雅弗[10]子孙,是否同属血气方刚的种族。到底是什么工作使他干瘪成这副模样?是什么样的情欲使他那张葱头脸变成茶褐色?那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真的。他当过什么差?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在办公室管过刽子手送来的账单、物料单,单子上的东西有处决犯上杀人者所用的黑纱、垫囚笼用的锯末、挂大刀的绳子。也许他当过屠宰场入口的收税员,要么当过管卫生的副督察。总之,这个人似乎曾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是一个巴黎拉东[11],虽然火中取栗,却不知谁是坐享其成的贝特朗;也好像是公众的不幸或劣迹赖以转动的某个枢纽。总之,他是这样一种人,我们见了会说:毕竟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他们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面如死灰,巴黎上流社会却一无所知。巴黎实在是一片汪洋大海,你即使投下探海锤,也永远测不出它到底有多深。你去探索去描写好了。不管你如何用心去探索去描写,不管海洋探险者如何众多,如何热心,这片海洋总还有人迹未至的地方、不为人知的洞穴,总还有花朵珍珠、妖魔鬼怪,某些文学潜水员闻所未闻、忘却忽略的东西。伏盖公寓便是这千奇百怪中的一怪。
在这群房客和包饭客人中间,有两张面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维多琳·泰伊番小姐皮肤苍白,显着病态,像患上萎黄病的少女;整天愁眉不展、举止局促、孤苦伶仃的样子,与这里整个愁苦的画面基调十分相称。虽然如此,她的脸毕竟不老,动作和声音还是轻快的。不幸的少女仿佛一株刚移栽的小树,由于水土不服,叶片已经萎黄了。她的脸微泛红色,头发是褐黄色,身材格外苗条,透出现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秀美。她的眼睛灰里带黑,流露出基督徒般的温和与随顺。朴素而经济的衣着,勾勒出年轻的体态。她美就美在匀称。若领略了幸福,她一定十分动人:幸福本是女人的诗,一如服饰是她们的脂粉。如果舞会的欢乐使这张苍白的脸庞映上粉红的色调,如果讲究而舒适的生活使她那已经微微凹陷的面颊丰满起来,泛起红晕,如果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重放光彩,维多琳大可与最美丽的姑娘们比个高低。她只缺少令女人再现青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可以写一本书。她父亲认为有理由不认她这个女儿,不愿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六百法郎,还在财产上做手脚,好全部传给儿子。维多琳的母亲投奔远房亲戚库蒂尔太太,后来绝望地死在那里。库蒂尔太太把孤儿视同己出,抚养长大。可惜,这位共和国军需官的遗孀,除了亡夫的那点预赠财产和抚恤金之外一无所有;说不定有朝一日会撇下这个不谙世事、一文不名的可怜姑娘,任由社会去摆布。好心的女人每星期天都带维多琳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做一次忏悔,看她能否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她的考虑是对的。有了宗教感情,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到父亲那里,带去母亲对他的宽恕;但每年都吃无情父亲的闭门羹。能够居间斡旋的只有她的兄长,而当哥哥的四年里一次也没来看她,也不给她任何帮助。她祈求上帝让父亲开眼,让兄长软心;对他们非但没有怨言,反而为他们祈祷。库蒂尔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词典上骂人的词语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行径。她们咒骂这个混账的百万富翁时,维多琳便喃喃细语,仿佛一只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呻吟中还吐露出爱心。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长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面孔,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惯有姿势都显出是贵族人家子弟;从小学的就是高雅的传统习惯。他爱惜衣服,平日穿的都是隔年的旧衣,但有时出门也能穿得像个翩翩青年。他日常则穿一件旧外套、粗坎肩,蹩脚的黑色旧领带系得马马虎虎,像一般大学生一样;长裤也跟上装差不多,靴子已经换过掌。
在这两个人物和其他人之间,有一个过渡的角色,那就是年届四十,鬓脚染过的伏脱冷。他属于谁见了都会说声“好家伙!”的那种人;肩宽胸健,肌肉突起,方方的手十分厚实,指节上长着火红色的浓毛,很是显眼。他的脸过早地爬上了皱纹,看上去有点冷峻,但待人接物却又随和平易。他的中低音嗓子,跟他快快活活的性格非常合拍,一点也不讨厌。他乐于助人,嘻嘻哈哈。如果有什么锁坏了,他会立刻拆下来,鼓捣好,上点油,锉一锉,再装上,一边说:“这我内行。”而且,他什么都懂,举凡船舶、大海、法国、外国、生意、人物、时事、法律、旅馆和监狱,无所不知。要是有人苦经叹多了,他赶紧出手帮忙。他曾好几次借钱给伏盖太太和几位房客,但借他钱的人宁死也不赖他的账,因为尽管他外表像个好好先生,可是目光却深邃而坚毅,令人望而生畏。从他吐口水的架势,看得出他沉着镇静,若要跳出困境,一定会铤而走险。他的目光像威严的法官,似乎能看透所有悬疑、所有思想、所有感情。他习惯午饭后出门,回来吃晚饭,整个晚间都在外面,深更半夜才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万能钥匙开门。只有他才享受这种优待。而且,他跟寡妇相处得非常好,搂着她的腰喊她妈妈,这种奉承也实在让人费解!那女人以为这只是举手之劳,殊不知只有伏脱冷才有那么长的胳臂,搂得住她粗大的腰围。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阔绰地每月交十五法郎,好在饭后能喝上一杯兑酒咖啡。那班青年人固然卷在巴黎生活的旋涡里忘乎所以,那班老年人也固然事不关己无动于衷,但即便不像他们那么肤浅的人,也不会注意到伏脱冷形迹可疑。周围别人的事,他都知道或者猜到;而他自己在想什么干什么,却没有一个人看得透。他明里与人为善,总是客客气气,乐天快活,暗里却把这些当作一道藩篱,隔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虽然如此,却不时流露他城府极深。他往往会冒出一句尤维纳利斯[12]式的俏皮话,似乎热衷于嘲弄法律,鞭挞上流社会,指责它自相矛盾,使人感觉到他对社会现状怀有仇恨,心底里小心翼翼地藏着什么秘密事儿。
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年轻的大学生,一个精力充沛,一个长得俊美;泰伊番小姐也许无意间受到二者吸引,她暗中偷觑的目光和私下的念头,总离不了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位,好像谁心里都没有她,尽管说不定哪天,她会时来运转,一变而为富有的婚姻对象。再说,这些人谁也不会费神去弄清旁人所诉的苦是真还是假。他们彼此无动于衷,而且出于各自不同的处境,互不信任。他们知道无力减轻对方的痛苦,而且平时一遍遍地互相诉苦,安慰的话也早已说尽;俨然像老夫老妻,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只剩下机械的生活,就像没上油的齿轮,在那里咬合转动。在街上遇到盲人,他们会毫不理睬地径直走过,听别人说起什么倒霉事,他们会毫不动情,还会把死亡看作是脱离苦海;饱经苦难的结果,对人间最悲惨的景象也冷眼看待。在这群失意的人中,最幸福的要数伏盖太太了,她高高在上地管着这所私人济贫院。只有伏盖太太觉得,那个小园子是一块锦绣花园,其实,寂静和寒冷,干燥和潮湿,使园子显得空旷辽阔,仿佛一片茫茫荒原。只有她才觉得,这所颜色发黄、阴森沉闷,散发出柜台铜臭味的房子有着种种乐趣。这一间间牢房都是她的。她喂养着这帮终身做苦役的囚犯,对他们颐指气使,他们一个个唯唯诺诺。以她所定的价钱,这些苦命人在巴黎,哪里找得到如此卫生而量足的伙食,以及能自己做主安排得虽谈不上雅致舒适,至少也算干净卫生的住房呢?哪怕她极不公道,人家也只是逆来顺受,没有二话。
这些人凑在一起,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简直是,而且实际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中学和交际场里一样,一起吃饭的十八个人中,总有一个可怜的受气包,一个出气筒,大家都拿他取笑。到了第二年年初,欧也纳·德·拉斯蒂涅发现,在这群他注定还要共同生活两年的人里,这个受气包的角色显得格外突出。这个受气包就是以前做面条的高里奥老头,如果有人来画画,一定会如历史学家一样,把画面的所有光线集中到他头上。半带仇恨的轻蔑,掺杂轻视的欺凌,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为什么全都倾泻在这个资格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古怪的地方,比恶习还难以原谅吗?这类问题与社会种种不公密切相关。也许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要是一个人真的谦卑处世,懦弱无争,或者满不在乎,别人就什么气都让他受。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当牺牲品,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吗?最弱小者如小孩,也会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按响各家的门铃;或者踮起脚把自己的名字,涂写在洁净的纪念性建筑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