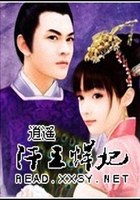伏盖太太娘家姓孔弗朗,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四十年来在巴黎开一家平民公寓。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区之间,坐落在圣热内维埃芙新街[1]上。这家公寓名叫伏盖公寓,客人无论男女老少,一概欢迎,风气端正,从没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然而三十年间,却不曾见过年轻女客在这里住宿;青年男子非得家里给的生活费少之又少,才会住到这里来。话虽如此,一八一九年时,正当下面的悲剧开场的时候,这里倒真的住着个可怜的少女。伤感文学盛行的时代,悲剧一词泛滥成灾,敲击身心,以致无人真信,而在这里却不得不用。这并不是因为,从词语的真正含义上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悲剧成分,而是因为这部小说完成之后,intra muros et extra[2]的读者也许会掉几滴眼泪。这部作品能否为巴黎以外的人所理解?大可怀疑。书中的实地采访和地方色彩比比皆是,其特色只有住在蒙马特尔和蒙鲁日这两处高地[3]之间的人才能领略。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地带,墙上的处处灰泥摇摇欲坠,地上的条条泥浆乌黑乌黑;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人心是那么浮躁激昂,不知要有何等非同寻常的事件才能造成一时的感触。然而,东零西碎的痛苦随处可见,因为善恶混杂而变得伟大而庄严:面对这些景象,连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人都不免停下脚步,动起恻隐之心;可是他们获得的印象转瞬即逝,就好比囫囵吞下的美果。文明之车,就像载着札格纳特偶像的神车[4]一样,被一颗比较不易碾碎的心略微耽搁,阻住车轮,立刻把它压碎,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行。你们读者也会这样,用白皙的手拿着这本书,埋在柔软的安乐椅里自言自语说道,这一本大概可以让我消遣一下。看完高老头隐秘的伤心史之后,你们晚饭照样吃得很香,而把自己的无动于衷归咎于作者,说他言过其实,自作多情。哎,各位须知,这部悲剧并非杜撰,也不是小说。All is true[5],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抑或在自己心里,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分。
公寓的房子属于伏盖太太,位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下段;那地方的地面往下通向弓弩街,坡道很陡,难得见有马匹取道上下。恩谷医院和先贤祠之间那些小街,因而就格外宁静。这两座历史建筑投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氛,圆圆的穹顶庄严肃穆,使下面的一切黯然失色。这里路面干燥,沟里没有泥水淤积,沿着墙根长着杂草。行人到了这里都怏怏不乐,最乐观的人也概莫能外。一辆马车的声音都会造成轰动。房屋死气沉沉,墙壁散发出牢狱的气息。巴黎人若是走错路来到这里,目之所及,只能看见些公寓、学校,不是苦难便是烦恼,老年人苟延残喘,本应快活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埋头发奋。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加阴森可怕,可以说,更加不为人知。尤其是圣热内维埃芙新街,仿佛一个青铜边框,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为了便于理解故事,多用一些灰暗的色调和沉闷的形象,实在也并不为过。这就如同游客参观地下墓穴,一级级走下去,日光随之渐弱,向导的声音也变得空洞起来。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谁又说得清,心如古井和脑袋空空,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为可怕呢?
公寓正面对着小花园,因而房子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成直角,在街上看得出房屋的进深。房屋与花园之间,沿着正墙有条微凹的碎石带,宽近两米;前面有一条平行的铺砂小径,两旁蓝白二色的大陶盆里,种着天竺葵、夹竹桃和石榴树。小径靠街的那头开一扇半大不小的门,上方有块牌子,写着:伏盖公寓,下面的字是:寄宿包饭,男女宾客,一概欢迎。白天是一道栅门,上面装有声音刺耳的门铃。透过栅门,可以望见小径那头正对着街的墙上,画着个仿绿色大理石的神龛,那是本区画匠的手笔,里面立着一尊爱神像。喜欢联想的人见了那浑身斑驳的釉彩,说不定会看出一段巴黎艳事;这种毛病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便可医治。底座下方有铭文,模糊的字迹反映出当年人们情之所致制作神龛的年代,伏尔泰一七七七年荣归巴黎的年代。铭文是这样写的:
无论你是谁,这便是你的良师,
过去是,现在是,或者将来是。[6]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道板门便代替了栅门。园子的宽度正好等于房子正面的长度,两边各有一道墙:一道是街墙,另一道是与隔壁分开的界墙。旁边那所屋子爬满了常春藤,把屋子整个遮住了,在巴黎也算是一景,格外令行人瞩目。两面墙都被成排的果树和葡萄藤遮盖着,瘦小而蒙尘的果实,每年都要使伏盖太太大伤脑筋,而且成为她与房客聊天的话题。沿着两道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往一片椴树树阴。伏盖太太虽然出身于孔弗朗家族,却总把椴树说成椴叶树,客人们用词法来纠正她也无济于事。两条沿墙小径之间是一方洋蓟,两旁是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边上还有酸模、生菜、香芹。椴树树阴下有一张绿漆圆桌,桌边放了一圈椅子。每当炎夏,在热得可以孵出小鸡的日子里,喝得起咖啡的客人便到这里来品咖啡。房子由方石砌成,正面有四层,上面还有阁楼;墙面刷的是那种难看的黄色,巴黎的房屋几乎都这样。每层有五扇窗,装着小块玻璃,百叶帘卷得高高低低,参差不一。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都装有铁栅和铁网。房后是个宽约二十尺的院子,猪啊、鸡啊、兔啊混在一起相安无事;靠里有个棚子,堆放木柴。棚子和厨房窗户之间,吊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的油腻污水。院子有一扇临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小门,厨娘从这里把屋里的垃圾清出去,用大量的水洗这块肮脏潮湿的地方,以免臭气难闻。
房子一楼的布局,自然是按开公寓的要求安排;第一间是客厅,从临街的两扇窗户采光,一个落地门窗供人出入。客厅与饭厅相通。饭厅和厨房之间隔着楼梯,梯级是木料和方砖做的,上了色擦得亮。一眼望去,客厅的景象再凄凉没有,里面放几把扶手椅和普通椅,包着明暗条纹相间的马鬃布套;中间摆一张灰底白纹大理石面圆桌,上面放一套白瓷杯子,杯子上的金线已经模糊不清,这种杯子今天还到处可以看到。房里的地板铺得很糟,护墙板有半人高;墙壁的其余部分,糊的是上了清漆的壁纸,壁纸上画着《忒勒玛科斯历险记》[7]里的几个主要场景,经典人物是彩绘的。装了铁栅的两个窗户之间的部位,有一幅画映入客人的眼帘,那是女仙卡吕普索宴请乌利西斯的儿子。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引得年轻客人开玩笑,他们自认身份高于现实处境,而调侃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石砌的壁炉,炉膛里总是干干净净,说明只在重大节日才生火。壁炉上摆一对花瓶,插满了纸花,纸花因年久而显陈旧,还用罩子罩着;当中放一个极为难看的灰蓝色大理石座钟。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气味,也许该称之为公寓气味吧。那是闷味、霉味、哈喇味,叫人冷飕飕的,吸到鼻子里湿漉漉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屋里刚吃过饭的气味、杯盘酒菜的气味、济贫院的气味。老少客人呼出的伤风气息,以及各自的特殊气味,若能设法检测其中令人作呕的成分,也许这气味还能形容。哦!尽管俗不可耐,但与毗连的饭厅相比,您会觉得,这客厅还算高雅、芬芳了,一如贵妇的小沙龙呢。饭厅整个装着护墙板,原来的漆色如今已难以辨认,上面的污垢层层叠叠,构成一幅幅狰狞怪异的图案。靠墙有几个黏糊糊的餐橱,橱上摆着几个缺了口的玻璃水瓶,暗淡无光;还有几个镀锡花纹铁皮圆垫,几摞图尔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子。角落里有个小柜子,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用以存放每个客人的餐巾,餐巾上不是污迹点点,就是酒痕片片。这里还有一些用不坏的家什,没处摆放而扔在这里,仿佛文明的残片留在了痼疾收容院。你会看到一个晴雨表,每逢下雨就出来一个修士;还有几幅倒人胃口的劣质版画,镶在黑漆描金的木框里;一个嵌铜的玳瑁挂钟;一个绿色炉子;几盏灰油积垢的油灯;一张长桌,上面铺着漆布,油腻之厚,足够无聊食客用手指在上面刻画自己的姓名;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椅子;几块破旧的擦鞋垫,散了的草辫若即若离;破破烂烂的脚炉,孔眼豁了,铰链脱了,木架子像炭一样焦黑。这些家什不是陈旧、裂缝、朽烂、摇晃、虫蛀,就是缺这少那,不堪使用,摇摇欲坠;若要一一说明,非得还要描写一番,那样拖泥带水,势必会影响故事的趣味,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方砖地因摩擦和上色,到处是一条条凹痕。总之,这儿毫无诗意,一派贫困,一种锱铢必较的,浓重的,破败的贫困,即使还没有污泥浊水,但已是秽迹斑斑,虽说还不至于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离腐朽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早上将近七点,是这间屋子最辉煌的时刻;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首先出现,它跳上餐橱,把好几碗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然后呼噜呼噜地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露面了,做作地戴着罗纱软帽,帽子下面露出一圈没戴好的假发,懒洋洋地趿拉着一双愁眉苦脸的拖鞋。老不老少不少的胖脸,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子,一双肉乎乎的小手,身材富态得像教堂里的老鼠[8],胸前膨亨饱满,颤颤巍巍,这一切与这间屋子倒很相宜,这里渗透出落魄失意,隐伏着算计投机;伏盖太太呼吸着屋里暖烘烘的臭味,一点都不觉得难受。她的脸像秋季初霜般清新,有皱纹的眼睛,表情可以从舞女般的笑容,一变而为债主的横眉冷对。总之,她整个的人足以说明公寓的内涵,一如公寓可以暗示她这个人。监狱少了牢头不成其为监狱,诸位也难以想象有此而无彼。这矮个妇人肥胖而苍白的身躯正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如同伤寒是医院气息的结果一样。她的毛织衬裙比罩裙还长,罩裙是旧连衣裙改制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里绽出,可说是客厅、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揭示了厨房的概貌和客人的品位。她一出场,舞台也就齐全了。伏盖太太年约半百,跟所有历经坎坷的女人一样。她目光无神,假惺惺的模样就像个老鸨,为了高价可以争个面红耳赤,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占便宜,如果还有什么乔治或皮什格吕[9]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然而,她其实是个好人,客人们如是说;他们听见她跟他们一样唉声叹气,咳嗽不已,便以为她真是个穷人。伏盖先生当初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从不谈起。他是怎么破产的呢?她总是回答说,倒霉呗。她男人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泪,这所房子好过活,还有就是不必同情任何不幸的权利,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都受尽了。胖子厨娘西尔维听见女主人急促的碎步,便赶紧给房客们开饭。
不在公寓住宿的客人,一般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餐。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住宿客人共有七位。整座房子最好的两套房间在二楼。伏盖太太住较小的一套;另一套归孀居的库蒂尔太太,她的先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名军需官。她带了个年轻少女,名叫维多琳·泰伊番;库蒂尔太太待她就如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达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房间,其中一套住着个老头,名叫波阿莱;另一套住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头戴黑色假发,染着大鬓脚,自称以前做过批发生意,叫做伏脱冷先生。四楼有四个房间,两间已经租出,老姑娘米旭诺住了一间;从前加工面条和淀粉,大家叫做高老头的,住了另外一间。其余两间用于租给候鸟一样的短期客人,租给那些潦倒的大学生,这些人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每月连吃带住只能交四十五法郎。可是伏盖太太不大欢迎这种人,除非没有办法才让他们入住,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那时候,这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个年轻人,他是从昂古莱姆附近到巴黎来学法律的,老家人口众多,格外省吃俭用,才每年给他寄一千二百法郎。他名叫欧也纳·德·拉斯蒂涅,是那种因贫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从小就明白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已经在盘算凭着学问,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而且使学业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如果没有他好奇的观察,没有他出入巴黎各处沙龙的高超本领,这个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也许这要归功于他有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探索的欲望,一定要看透一出惨剧的个中原委;而这惨剧,是制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