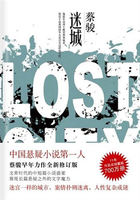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还少一张床。”拉斯蒂涅说。
“是的,先生。”她红着脸说,捏紧了他的手。
欧也纳望着但斐纳,他虽然年轻,也懂得女人动了爱情,心里就真的会有害臊之念了。
“您这样的人值得爱一辈子,”他附在但斐纳耳边说,“对,我敢这样说,因为咱们彼此十分理解:爱情愈是热烈真诚,就愈应该藏而不露,带几分神秘。咱们的秘密不能泄露给外人。”
“哦!我不是什么外人啊。”高老头嘟囔道。
“您知道您就是咱们……”
“对啦!我一直都这么希望。你们不会在意我的,是不是?我走来走去,像个善良的精灵,无处不在,你们只知道有他,可是眼睛却看不到他!嗳,小但斐纳,纳纳,但但!我当初跟你说:‘阿图瓦街有套漂亮屋子,咱们替他布置家具吧!’不是说得很对吗?你当时还不愿意。啊!你的生命是我给的,你的快乐还是我来给。做父亲的要幸福,就得永远地给。永远地付出,这就是父亲成其为父亲的道理。”
“怎么呢?”欧也纳问。
“是呀,她起先还不愿意,怕人家说闲话,好像人家抵得上自己的幸福!所有的女人做梦都想学她的样呢……”
高老头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德·纽沁根夫人早已把拉斯蒂涅领进了书房,里面传出一个亲吻的声音,尽管是那么轻轻的一吻。书房跟整套屋子一样高雅;这套屋子真是应有尽有。
“我们是不是猜对了您的心意?”她边问边走回客厅,准备吃饭。
“是,”他说,“太对了。不过,豪华无缺,美梦成真,年少倜傥的生活诗意,我都充分体会了,不至于配不上。但我不能从您那儿接受这一切,我还太穷,不能……”
“哈哈!您已经是不领我的情了。”说着她做出半严肃半玩笑的神气,有模有样地噘起了嘴。女人对人家的顾虑不屑一顾的时候,往往就用这个办法去消除。
这一天欧也纳曾经很当回事地扪心自问;伏脱冷被捕一事向他表明,他差点儿跌进的沟壑有多么深,因而高尚的情操、正直的修养再度抬头,即便是对方怀着慷慨的心意,那样娇媚地嗔怪,他也不为所动。一种悲哀在内心深处攫住了他。
“怎么!”德·纽沁根夫人说,“您不肯接受?您知道这样拒绝意味着什么吗?您是对前途没有信心,不敢跟我有什么瓜葛。莫非您是怕有朝一日会辜负我的一片真情?要是您爱我,我……也爱您,干吗面对这么点小意思您就缩手缩脚?要是您知道,我为您操办这个单身住处时,心里是多么高兴,您就不会犹犹豫豫,反而要向我赔不是了。当时我这儿有您的钱,我把这笔钱好好花了,仅此而已。您自以为高尚,其实恰恰相反。您的要求远不止这些……(哦!她说这句话时,捕捉到欧也纳的一道炽热目光。)却为了区区小事而忸忸怩怩。要是您不爱我,那好,就别接受。我的命运就凭一句话。您说呀!”她停了一会儿,转过来对她父亲说道:“父亲,您好好开导开导他。难道他以为,他在意名声,我就不在意吗?”
高老头看着、听着这场有趣的拌嘴,好像正在吸食鸦片一样,脸上的微笑凝固了。
“真是个孩子!您来到人生的大门,”但斐纳抓起欧也纳的手又说,“碰到许多人没法打破的关口,如今有个女人出手替您打开了,您却退缩了!可您一定会成功,一定会飞黄腾达;您天庭豁朗,分明写着成功二字。今天欠我的,那时不是可以还我吗?古代的贵族女子不是把盔甲、刀剑、骏马,供给她们的骑士,让他们能去比武,为自己增光吗?对,欧也纳,我送给您的,就是现代的武器,胸怀大志的人必不可少的工具。您住的那个什么阁楼,要是像爸爸的屋子,真是漂亮呀。嘿,咱们不吃饭了吗?您要我不高兴是不是?您说话呀!”说着她使劲摇对方的手。“天哪!爸爸,你叫他拿主意吧,不然我就走了,从此不见他了。”
“我来叫他拿主意吧,”高老头从陶醉中醒过来,说道,“亲爱的欧也纳先生,您不是要找犹太人借钱吗?”
“那是不得已呀。”他说。
“好,就要您这句话,”老人说着,掏出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破皮夹,“那么我来当犹太人。所有的账我都付了,有发票在这儿。这里的全部东西,账都清了。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充其量五千法郎;算我借给您的!您不会拒绝的,我又不是女人。您随便写个字条作凭据,将来还我就是了。”
几颗眼泪同时在欧也纳和但斐纳眼里打转,两个人面面相觑,愣住了。拉斯蒂涅过去握了握老人的手。
“哎哟!怎么!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吗?”高里奥说。
“不过,可怜的父亲,”德·纽沁根夫人道,“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喔!咱们谈到这上面来了,”他答道。“你当初听了我的话,决定把他迁到你身边,像办嫁妆似的采购东西,我就想:‘她手头要为难了!’诉讼代理人说,向你丈夫讨回财产的官司要半年多。好吧!我就卖掉了长期年金一千三百五十法郎的本金;拿出一万五存了一千二的终身年金,高息透本的那种;余下的本金付了你们的账,孩子们。我嘛,这儿楼上有间每年一百五十法郎的屋子,每天花上两法郎,日子就可以过得像王爷似的,还能有多余。我用什么都很省,也不用做什么衣服。半个月以来,我肚里笑着想:‘他们就要开心啦!’怎么样,你们难道不开心?”
“喔!爸爸,爸爸!”德·纽沁根夫人说着扑在父亲膝上,让他抱着。她拼命吻着老人,金色的头发在他的面颊上摩挲,滴滴泪水在那张笑逐颜开、眉飞色舞的老脸上洒落。“亲爱的父亲,您才是个父亲!天下哪有第二个像您这样的父亲!欧也纳过去已经非常爱您,何况现在呢!”
“噢,孩子们,”高老头说道,十年来,他不曾觉得女儿的心贴在他的心上跳过,“噢,小但斐纳,你真是要我高兴死了!我可怜的心都乐开了花。喂,欧也纳先生,咱们已经两讫了!”说罢老人抱着女儿,发疯似的蛮劲使她叫了起来:“哟!你把我弄痛了。”“把你弄痛了!”他说着,脸都白了。他瞧着女儿,一副痛苦得了不得的样子。这位慈父基督的面容,若要如实描绘下来,就得去看看绘画大师创作的救世主为人类受难的图像。高老头轻轻地吻女儿的腰,刚才他的手指在那儿搂得太重了。“不,不,我没有弄痛你,”他用微笑探询着她,继续说道,“倒是你那样叫喊使我难受。”他凑近女儿的耳朵,一边小心翼翼地吻着,一边说道,“钱花的不止这些呢,但要瞒着他,否则他会生气的。”
老人的无私奉献简直无穷无尽,欧也纳惊呆了,只能出神地望着他,流露出的那种天真的钦佩,在他这样的年龄,完全是由衷的表现。
“我一定对得起这一切。”他大声说道。
“噢,我的欧也纳,您说得真好。”德·纽沁根夫人说着,亲了亲大学生的额头。
“他为了你,拒绝了泰伊番小姐和她的几百万家财,”高老头说,“是的,小姑娘是爱您的;现在她哥哥一死,她就跟克罗伊斯[79]一样有钱了。”
“嗨!提这干吗?”拉斯蒂涅嚷道。
“欧也纳,”但斐纳凑在他的耳边说道,“现在我觉得,今晚还有点儿过意不去。啊!我会好好爱您的!永远爱您。”
“你们姐儿俩出嫁以来,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高老头大声说道。“仁慈的上帝要我受多少苦都可以,只要不是你们要我受的。将来我会想到:今年二月里我有过一阵幸福,那是别人一辈子都没有的。你看着我,斐斐!”他对女儿说。“她很美,不是吗?那么您告诉我,在您碰见过的女人当中,有她那样的漂亮脸色和小小酒窝的多吗?不多,对吗?嘿,这个美人儿是我的骨肉呀。从今以后,您给了她幸福,她还要漂亮不知多少倍呢。欧也纳,”他说,“如果您要我那份儿天堂,我给您就是;我可以下地狱。吃饭吧,吃饭吧,”他嚷道,不知道自己尽说些什么。“一切都是咱们的了。”
“可怜的父亲!”
“我的女儿,”说着他站起身来,过去捧着女儿的脑袋,亲吻她的头发,“你不知道,要使我幸福是多么容易!你不时来看我一下,往后我就住楼上,你走两步就到啦。要答应我,你说呀!”
“是的,亲爱的父亲。”
“再说一遍。”
“是的,我的好爸爸。”
“行啦行啦,由我的性子,会要你说上一百遍。咱们吃饭吧。”
整个晚上都像孩子闹着玩似的度过了,高老头的疯劲也不下于他们俩。他躺在女儿脚下,亲她的脚,老半天盯着她的眼睛看,脑袋在她的长裙上厮磨;总之,疯疯癫癫,像个极年轻极温柔的情人。
“您看见了吧?”但斐纳对欧也纳道,“我们和父亲在一起,就得整个儿属于他。有时候叫人很不自在。”
这句话是一切忘恩负义的根源,可是欧也纳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心里已经好几次升起了妒意。
“屋子什么时候收拾完呢?”欧也纳在房间里四下望了望,问道。“今晚我们还得分手吗?”
“是的,不过您明天来陪我吃饭吧,”她狡黠地说,“明天是意大利剧院演出的日子。”
“那么我去楼下的座位。”高老头道。
时间已是午夜。德·纽沁根夫人的马车早已等着。高老头和大学生回伏盖公寓,一路上谈着但斐纳,两人越谈越激动,竟然奇怪地较上了劲,争着抒发各自的强烈感情。欧也纳没法不承认,父爱绝不受个人利害的玷污,父爱的始终不渝和广阔无边,远过于他的爱。在父亲心目中,偶像永远纯洁美丽,过去的一切,将来的前景,都能增强崇拜之情。他们回家发现,伏盖太太待在炉子旁边,在西尔维和克里斯托夫之间。老房东待在那儿,好比马略身处迦太基废墟之上[80]。她一边等着这两位仅存的房客,一边对西尔维诉苦。拜伦把塔索的怨叹描写得虽然很美[81],但以真实和深刻而论,却远远不及伏盖太太的怨叹呢。
“明儿早上只须准备三杯咖啡了,西尔维。唉!公寓里空荡荡的,怎么不叫人伤心?没了客人还像什么生活!空空如也。公寓里的人一下子都走了;生活就靠那些衣食饭碗呀。我犯了什么天条要招来这样的横祸?咱们的豆角和土豆都是预备二十个人吃的。我的公寓跟案子牵连上啦!咱们只能尽吃土豆了!只能把克里斯托夫辞掉了!”
萨瓦人克里斯托夫正打瞌睡,蓦地惊醒过来,问道:“太太有什么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