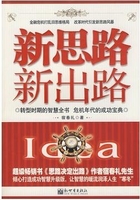“您这样子正是我要的效果。”伏脱冷对他道。“您做的事,您心中有数。好,我的小鹰!您将来一定是人上人;您有能耐,痛快、勇敢;我佩服您。”
伏脱冷想拉他的手,拉斯蒂涅急忙缩回去;他脸色发白,跌坐在椅子上,眼前似乎看到一大摊血。
“哟!咱们还有点过意不去呢,”伏脱冷低声说,“多利邦老伯[65]有三百万,我知道他的家底。这样一笔陪嫁尽可把您洗刷干净,跟新娘的婚纱裙一样白,即便在您眼里也是这样。”
拉斯蒂涅不再犹豫,决定当晚就去知会泰伊番父子。这时伏脱冷走开了,高老头凑在他耳边说:“您很不高兴,孩子!我来给您开开心吧,您来!”
说着老面条商凑在灯上点燃蜡烛;欧也纳好奇地跟他走去。
“到您房间吧。”老头子说道,他已向西尔维要了大学生的钥匙。“今天上午,您以为她并不爱您,嗨!”他接着又说,“她硬要您走,您就生气走了,绝望了。小傻瓜!她是在等我。明白吗?我们要去最后布置布置一套小巧玲珑的房子,让您三天之内搬去住。您别出卖我呀。她想给您一个惊喜;可我不想对您保密下去了。您要住到阿图瓦街,离圣拉扎尔街就两步路。您在那儿住得像个王子。我们为您置办的家具,就像新娘用的。这一个月下来,我们瞒着您做了好多事。我的诉讼代理人已经开始活动了,将来我女儿每年有三万六千法郎收入,是她陪嫁的利息;回头我要求把她的八十万法郎投资房地产。”
欧也纳默不作声,抱着手臂在他乱七八糟的小房间里踱来踱去。高老头趁大学生背转身的当儿,把一个红皮盒子放在壁炉架上,盒子外面有拉斯蒂涅家的烫金纹章。“亲爱的孩子,”可怜的老头儿说,“所有这些,我都办得很投入。可是您瞧,我也很自私,您换个地方住对我也有好处。要是我要求您一件事,嗯,您不会拒绝我吧?”
“什么事?”
“您新居的六层楼上,还有一间附属的卧室,将来我住,行吗?现在我老了,离两个女儿太远了。我不会妨碍您的;光是住在那儿。您每天晚上跟我谈谈她。您不讨厌吧,您说呢?您回家的时候,我在床上听到您的声音,心里想:‘他刚见过我的小但斐纳;带她去了舞会,使她开心了。’要是我病了,听着您回来、走动、出去,我心里就有了安慰。您身上有我女儿的气息!我只要走几步路就能到香榭丽舍大街,她们天天打那儿过,我总能看到她们了,不会再像现在这样有时去晚了。而且她说不定会上您那儿去!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看她穿着晨袄,走着碎步,像小猫一样可爱地走来走去。一个月以来,她又恢复了从前少女的样子,快活,漂亮。她的心情正在复原,是您给了她幸福。哦!什么办不到的事,我都可以为您办。她刚才回家的路上,对我说了又说:‘爸爸,我真快活!’要是她们彬彬有礼地叫我父亲,我的心就凉了;可一叫我爸爸,我好像又看到了她们小时候的样子,回忆起所有的往事。这样我就真是她们的父亲了。我觉得她们还没属于别人!”
老头儿揩了揩眼睛,他在落泪。
“好久我没听见女儿这样叫了,好久没挽过她的胳膊。唉!是呀,足有十年我没同女儿并肩走路了。挨着她的裙子,跟着她的步伐,感受她的热气,是多么惬意啊!今儿早上,我把但斐纳领着到处跑;同她一块儿逛店铺;又送她回家。噢!您把我留在身边吧。您要人帮忙的时候,有我在呀。喔!要是那个阿尔萨斯木头桩子死了,要是他的痛风症跑进他的胃了,我可怜的女儿不知该多么高兴呢!那时您就做我的女婿,堂堂正正做她的丈夫了。唉!她真不幸,世上的乐趣一点儿都没尝到,所以我什么都原谅她。仁慈的上帝总该站在慈爱的父亲一边吧。她太爱您了!”他停了一会儿,晃着脑袋说道。“她一边走,一边跟我谈着您:‘对不对,爸爸,他很不错!心肠好!他常提到我吗?’嘿,从阿图瓦街一直到帕诺拉玛巷,她跟我说了好多好多!总之,她把她的心都倒在我的心里了。整整一个上午真开心,我不觉得自己老了,身子骨轻着呢。我告诉她,您把那一千法郎交给了我。哦!小宝贝她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嗳,您壁炉架上放的什么呀?”高老头终于问道,因为他见拉斯蒂涅一动不动,急得忍不住了。
昏头昏脑的欧也纳呆呆地望着他的邻居。一方面,伏脱冷宣布说,明天就要决斗;另一方面,他最热切的种种希望即将成为现实。两者的反差如此强烈,使他觉得自己正在经历噩梦。他朝壁炉转过身,看到上面那个小方盒子,他把盒子打开,发现里面有张纸,纸下有一块布雷盖牌子的名表。纸上写着这样的字样:
我要您时时想着我……
但斐纳
最后一句大概是指他们俩有过的一次争吵;欧也纳看了大为感动。金壳上用珐琅镶嵌着他的纹章。这件向往已久的宝贝,链子、扳子式样、图案,他样样中意。高老头喜形于色。他也许答应过女儿,要把欧也纳见到礼物时的惊喜样子,一五一十说给她听;就年轻人的激动而言,他不过是第三方,但高兴程度却绝不逊色。他已经很喜欢拉斯蒂涅了,为了女儿,也为了他自己。
“今天晚上,您要去看看她,她在等您呢。那个阿尔萨斯木头桩子,在他的舞女那儿吃饭。哈哈!我的律师向他指出他的所作所为,他顿时傻了眼。他不是说,爱我女儿爱得五体投地吗?他要碰一碰她,我就把他宰了。一想到我的但斐纳在……(他叹了口气),我真能做出犯法的事来;不过那不叫杀人,他不过是个牛头猪身的怪物罢了。您会收留我的,是吗?”
“是的,我的高里奥好老伯,您知道我是敬重您的……”
“这我看得出来,您没觉得我丢您的面子!让我来拥抱您。”说着,他搂了搂大学生。“您得使她幸福,您要答应我!今晚您要去的,是吗?”
“哦,是的!我要出去办点事儿,不能耽搁。”
“我能不能给您帮忙呢?”
“噢,行啊!我上德·纽沁根夫人家,您去见泰伊番老头,要他晚上给我个时间,我有件要紧事儿和他谈。”
“是不是真的,小伙子,”高老头说着脸色陡变,“您在追他的女儿吧,楼下那些笨蛋都这么说。天打雷劈的!您可不知道什么叫做高里奥的老拳呢。您要对不起我们,那就拳头相见了。哦!那是不可能的。”
“我向您发誓,世界上我只爱一个女人,”大学生说,“我也是才知道的。”
“啊,那太好了!”高老头道。
“不过,”大学生又说,“泰伊番的儿子明天要去决斗,听说他会送命的。”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高老头说。
“可一定得告诉他,别让他儿子去……”欧也纳大声说道。
就在这时,他的话被打断了,只听得伏脱冷的嗓音在门口唱道:
噢,理查,噢,我的王上!
世界把你抛弃……[66]
“勃隆!勃隆!勃隆!勃隆!勃隆!”
我曾周游世界很久,
人们见我……
“特啦啦,啦,啦,啦……”
“先生们,”克里斯托夫喊道,“开饭了,饭厅里大家都坐好了。”
“喂,”伏脱冷说,“拿一瓶我的波尔多葡萄酒来。”
“您觉得好看吗,那块表?”高老头问,“她很会挑吧,嗯!”
伏脱冷、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三人一同下楼,因为迟到,在饭桌上挨在一处坐着。吃饭的时候,欧也纳对伏脱冷极为冷淡;而在伏盖太太眼里,伏脱冷真是可爱,他从来没这么风趣。他妙语连珠,把吃饭的人全逗乐了。这种泰然自若,这种沉着镇静,让欧也纳惊讶不已。
“您今儿是怎么啦?”伏盖太太问。“快活得像云雀一样。”
“我做了好买卖总是快活的。”
“买卖?”欧也纳说。
“是啊。我交了一部分货,要赚大笔佣金呢。米旭诺小姐,”他发觉老姑娘在打量他,便说,“您这样朝我盯着看,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地方让您不舒服?得告诉我呀!为了让您愉快,我可以改变的。”
“波阿莱,咱们不会因此生气吧,嗯?”他瞟了瞟老职员说道。
“见鬼!您应该当模特儿,去扮滑稽大力神。”青年画家对伏脱冷道。
“是呀,可以!只要米旭诺小姐肯扮拉雪兹神甫公墓的维纳斯。”伏脱冷回应道。
“那波阿莱呢?”比安训问。
“噢!波阿莱就扮波阿莱吧。他是园神呢!”伏脱冷大声说道,“波阿莱源出于梨[67]……”
“而且是熟透的软梨!”比安训抢着说。“那么您就在梨和奶酪之间了[68]。”
“尽是胡说八道,”伏盖太太说道,“最好还是把您的波尔多葡萄酒拿给我们吧,我看有一瓶已经露脸了!这东西既能健胃又能助兴。”
“先生们,”伏脱冷道,“主席女士叫咱们规矩点。你们打哈哈,库蒂尔太太和维多琳小姐虽不会生气,但要尊重老实人高老头。至于波尔多葡萄酒,我向你们提议喝一小瓶拉玛;拉菲特这个名字使它名气倍增,我这么说可没有政治影射[69]呀。来呀,呆子!”他说,一边望着克里斯托夫,伙计站着没动。“这儿,克里斯托夫!怎么啦,没听见你的名字?呆子,拿酒来!”
“给,先生。”克里斯托夫说着,把那瓶酒递给他。
伏脱冷先把欧也纳和高老头的杯子斟满,再给自己慢慢倒了几滴。旁边两位酒客在喝的时候,他自己也品了品,忽然做了个怪相。
“见鬼!见鬼!有瓶塞味儿。这就送你吧,克里斯托夫,给我们另外去拿;在右边,知道吗?我们一共十六个人,拿八瓶下来。”
“既然您破费,”画家说,“我出钱买百把个栗子。”
“喔!喔!”
“哟哟!”
“嘿!”
每个人都发出欢呼,仿佛烟火从花筒里一齐迸发。
“喂,伏盖妈妈,来两瓶香槟。”伏脱冷冲她叫道。
“亏您想得出!干吗不把屋子都要了?两瓶香槟!十二法郎呀!我哪儿去挣十二法郎!要是欧也纳先生肯付这笔账,我用果子露请客。”
“她的果子露呀,像果汁一样催泻呢。”医科大学生小声说。
“别说了,比安训,”拉斯蒂涅嚷道,“我听见汁心里就……行,去拿香槟,我付账就是了。”大学生又说。
“西尔维,”伏盖太太说,“拿饼干和小点心来。”
“您的小点心太大了,”伏脱冷道,“都长胡子了。还是拿饼干来吧。”
一时间,波尔多葡萄酒转过来转过去,饭桌上大家都来了劲,越来越开心。粗野的狂笑中,不时冒出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博物馆职员竟学起巴黎街头的叫卖声,活像猫儿叫春;立刻有八个人异口同声拉开嗓门怪叫起来:
“磨刀喂!”
“卖鸟食喔!”
“卷饼呀,女士们,卷饼呀!”
“补砂锅瓦罐咧!”
“鱼鲜到岸啦!”
“捶老婆,捶衣服喽!”
“旧衣服、旧饰带、旧帽子哟!”
“卖樱桃,好甜的樱桃!”
最妙的是比安训的鼻音,他叫的是:“卖伞的来啦!”
霎时间闹哄哄的,把人脑袋都吵破了;你一句我一句,全是东扯西拉,像一出真正的闹剧;伏脱冷一边当指挥,一边冷眼觑着欧也纳和高老头;这两人好像已经醉了,背靠着椅子,神情凝重,直勾勾地看着这不同寻常的混乱场面,酒喝得不多,都想着晚上要办的事,可是都觉得身子站不起来。伏脱冷不时瞟他们一眼,不放过他们的神色变化,等到他们眼睛忽闪忽闪快要闭上了,他侧身贴着拉斯蒂涅的耳朵,对他说道:
“小家伙,您还不够滑头,斗不过伏脱冷老头的;他太喜欢您了,不能让您胡来。我一旦决心要干什么,只有上帝拦得住我。哼!咱们想去给泰伊番老头通风报信,想犯小学生的错不是!炉子热了,面也揉了,面包上了铲子;明儿咱们就可以抛着面包小团,一口一口张嘴接住咬了,您却不让面包进炉?……不成不成,生面一定得烤成面包!要有什么小小的过意不去,等您吃的东西消化了,也就没什么了。咱们乖乖睡觉的时候,上校弗兰切西尼伯爵剑头一挥,替您把米歇尔·泰伊番的遗产安排好啦。维多琳继承了她的哥哥,一年就有小小的一万五千法郎收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母亲的遗产有三十多万呢……”
欧也纳听见这些话不能回应,只觉得舌头粘住上颚了,瞌睡一阵阵袭来不依不饶。他只能隔着一层明晃晃的雾,看见桌子和众食客的脸。不久,声音静了下来,客人一个一个离去;后来只剩下伏盖太太、库蒂尔太太、维多琳小姐、伏脱冷和高老头,拉斯蒂涅这时仿佛在梦里,依稀看见伏盖太太忙着拿过酒瓶倒着余酒,把别的瓶子装满。
“嗳!他们真是乐疯了,多么年轻啊!”寡妇咕哝道。
这是欧也纳听得懂的最后一句话。
“只有伏脱冷先生才弄得出这样的闹剧。”西尔维道,“哟!瞧克里斯托夫,打鼾打得像陀螺一样。”
“再见,大妈,”伏脱冷说,“我要到大街上看马蒂先生演《荒山》去了,那是根据《孤独者》[70]改编的大戏。要是您愿意,我带您和这两位女士一块儿去。”
“我心领了,谢谢您。”库蒂尔太太说。
“怎么,我的邻居!”伏盖太太大声说道,“您不想看《孤独者》改编的戏?那是阿达拉·德·夏多布里昂[71]写的书,咱们还读得津津有味呢,写得真好,去年夏天咱们在椴叶树下,还为那个埃洛迪的遭遇,哭得像抹大拉[72]似的;总之是一部教化作品,不是可以用来教育您的小姐吗?”
“照规矩,我们是不能去看戏的。”维多琳接过话头说道。
“哦,这两位喝醉了。”伏脱冷说着,把高老头和欧也纳的脑袋滑稽地摇了摇。
他把大学生的头靠在椅背上,让他睡得舒服些,又热烈地亲了亲他的额头,一边唱道:
睡吧,亲爱的宝贝!
我永远为你们守卫。
“我怕他病了。”维多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