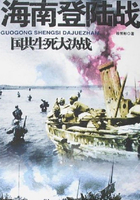“噢!”他哼了一声就放开了我,“我看出那个恶毒的小流氓不是哈里顿。我乞求你的宽恕,奈莉。要真是他,那该活剥他的皮,叫他不飞跑过来欢迎我,还一个劲儿尖叫仿佛我是个幽灵。没人性的小畜生,这边来!我来教你怎么来欺骗一个好心受欺的父亲。听着,你不觉得这小子耳朵上剪一刀更漂亮些吗?狗剪了耳朵尖儿可是更加凶猛,我就喜欢凶猛的东西!给我一把剪刀,那好凶猛的修理家伙!再说,珍惜耳朵那是地狱里的时尚,是魔鬼的虚荣心。没有耳朵也尽够做一头驴子。嘘,孩子,嘘,那么好吧,我的宝贝儿!别哭,擦干眼泪,笑一个,亲亲我。什么!他不亲?亲我,哈里顿!见你的鬼,亲我!天哪,好像我要来养这么一个妖怪!我要不把这小鬼的脖子拧断了,我就不是人!”
可怜的哈里顿在他父亲怀里使足劲儿乱叫乱踢,当他被抱到楼上,被举到栏杆外围的时候,更把叫喊声放大了两倍。我高声嚷着他会把孩子吓出疯病的,冲过去救他。
我到他们跟前时,亨德雷把身子斜出栏杆,想要细听楼下发出的一个声音,差不多忘了手里还抱着什么。
“那是谁?”他问,听出了有人走近楼梯脚边。
我也倾出身去,为的是给希斯克厉夫发个信号,我听出了他的脚步声,想叫他不要再往前走。就在我的眼睛离开哈里顿的一刹那间,他突然一窜,挣脱把住了他的那个心不在焉的怀抱,跌了下去。
我们都没来得及经历毛骨悚然的恐怖,便已看到那个小坏蛋安然无恙了。希斯克厉夫在千钓一发的关口正好走到底下,本性使然,他接住了从天而降的东西,继又扶他站稳,才抬起头来,探寻事故的作者。
一个吝啬鬼为了五先令放弃一张彩票,第二天发现他在这笔交易上是错过了五千英镑,也不会比在上头看到厄恩肖先生人影的希斯克厉夫,更要来得瞠目结舌。这神色比言语更是明白无误传达了最为强烈的痛苦,为他居然自投罗网,做了消解自己报仇计划的工具。假如是在夜里,我敢说,他真会把哈里顿的脑壳敲个粉碎,以此来弥补他的过失。可是我们眼见孩子是得救了。我当时就冲下楼去,把我在看护的小宝贝紧贴在心上。
亨德雷下楼要从容得多,他酒醒了,就有点局促不安的样子。
“这是你的错,艾伦,”他说,“你应当把他藏起来,别让我看见。你应当把他从我怀里抱开去!他受伤了吗?”
“受伤!”我愤怒地喊道。“即便他没给摔死,也会摔成一个白痴!噢,我真不明白他母亲怎么没有从坟墓里出来,看看你是怎样对待他的。你比邪教徒还不如,这样子来戕害你自己的骨肉!”
他想摸一摸他的孩子,孩子既经发觉是在我的怀里,就抽抽噎噎,哭走了他的恐怖。可是,他父亲的第一根手指触碰到他,他就重又尖叫起来,声音比先时更高。他死命挣扎,仿佛就要痉挛起来。
“你别管他啦!”我接着说。“他恨你,他们都恨你,那就是真情!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竟糟蹋到这样的境地!”
“这境地还能更好一些呢,奈莉,”这迷人歧途的人大笑着说,又恢复了他的铁石心肠。“现在,你抱着他走路。还有,你听着,希斯克厉夫,你也走开,别让我看到听到……今晚我不杀你,除非,或许,我放火把这屋子烧了。可是那还得看我的兴头。”
他这么说着,从碗柜里摸出一瓶白兰地,在酒杯里倒了些。
“别,别喝!”我求他说。“亨德雷先生,听我一句吧。饶了这个不幸的孩子,要是你对自己已经全不在乎!”
“随便是谁待他都比我好。”他回答说。
“可怜可怜你自己的灵魂!”我说,我竭力想夺下他手中的杯子。
“我不可怜J恰恰相反,我最高兴不过的是把我灵魂发落到地狱中去,来惩罚它的造物主,”这个渎神的人喊道,“来为它心甘情愿下地狱干杯!”
他喝干了酒,满不耐烦地示意我们走开,他用一连串可怕的诅咒结束他的命令,恶毒不堪重述,我都不愿记住。
“真可惜他喝酒喝不死自个儿,”希斯克厉夫说,门给关上的时候,嘴里一连串诅咒算是回敬。“他在往死里作践自己,可是抵挡不过他的身板。肯尼斯先生说他愿意赌上他的母马,管保他在吉默顿这一边儿,比随便哪个男人都要长命,等他走进坟墓,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罪徒了,除非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灾祸降临于他。”
我走进厨房,坐下来哄着我的小羊羔儿入睡。我原以为希斯克厉夫去了谷仓,后来才知道他才走到高背长椅的那一边,就倒在一条长凳上,离火挺远,死不吭气。
我把哈里顿放在膝头上摇着,哼着一支曲儿,它是这样开头的:
夜深了,孩儿们磨牙了,
坟茔底下的妈妈听见了。
凯茜小姐一直在她的房里倾听外面吵闹,这时候伸进头来,小声问我:
“你独个儿吗?奈莉?”
“是呀,小姐。”我回答说。
她进门走到壁炉边上。我以为她要说什么话,便抬起头来。她脸上的神色看上去迷惘又焦急。嘴唇半张着,像是要说话。她吸了一口气,可是吐出来的是叹息,却不是一句话。
我又哼哼我的曲儿,刚才她那两下子我还没有忘记呢。
“希斯克厉夫在哪儿?”她打断我说。
“马厩里干他的活儿。”我这样回答说。
他没有来更正,兴许是在打瞌睡口巴。
接着又沉默了好一阵儿,在这当儿我看到有一两滴眼泪从凯瑟琳脸上落下,滴在地上。
“她是为她那可耻的行为感到羞愧吗?”我问我自己。“那可真是新鲜事了。可她其实是能够羞愧的,只要她愿意。我可不能去帮她!”不去,她对任何事儿都懒得操心,除非她自个的事儿。
“哦,好人儿!”她终于喊出声来。“我真不高兴!”
“可惜哪,”我说,“要你高兴真不容易。这么多朋友,这么少牵挂,还不知足!”
“奈莉,你能给我保守一个秘密吗?”她跪在我身边继续说,抬起她那迷人的眼睛望住我的脸,那神气即令人有天大的理由要发怒也无从怒起了。
“值得保守吗?”我问,愠怒已经消了几分。
“值得的,他真叫我心烦,我非说出来不可!我想知道我应当怎么办。今儿个,艾德加·林顿向我求婚了,我也给了他答复。现在,我先不说我是同意了还是拒绝了,你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
“真的,凯瑟琳小姐,我怎么知道呢?”我回答说。“当然,从今儿下午你在他面前的那一番表演来看,我得说明智的做法该是拒绝他。因为这么闹下来他还来求婚,他不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就是个胆大包天的傻瓜。”
“你这么说,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她气冲冲地回敬我说,站直了身子。“我答应他了,奈莉。快点,说我是不是错了!”
“你答应他了!那么再商议这事有什么意思!一言既出,就没法收回了。”
“可是,说说我是不是应当这么做,说呀!”她用激愤的声调嚷道,搓着双手,紧皱了眉头。
“在好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呢,”我意味深长地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一个问题,你爱艾德加先生吗?”
“谁能不爱?当然我爱。”她回答说。
跟着我同她开始了下面的一系列对答,对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来说,这些对答是不算冒失了。
“你为什么爱他,凯茜小姐?”
“胡说八道,我爱,这就够了。”
“不行,你非得说为什么。”
“好吧,因为他漂亮,同他在一起心里高兴。”
“糟!”这是我的评语。
“因为他年轻又快乐。”
“还是糟糕。”
“因为他爱我。”
“这不相干。”
“他会发财,我要做这一带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将为有这样一个丈夫而骄傲。”
“糟透了。现在说说你怎么爱他。”
“就像每一个人那样爱呀!你真傻,奈莉。”
“一点都不傻,回答我。”
“我爱他脚下的地,爱他头上的天,爱他触摸的每一样东西,爱他说出的每一个词儿。我爱他所有的表情,所有的行为,整个儿爱他整个儿的人,好了吧!”
“那为什么呢?”
“不,你在开玩笑呢。坏透了心眼儿!这在我可不是玩笑事儿!”年轻的小姐说着皱起了眉,把脸转向了炉火。
“我才不开玩笑呢,凯瑟琳小姐,”我回答说,“你爱艾德加先生,是因为他漂亮、年轻、快乐、有钱,并且还爱你,可最后一点是不在话下的。少了它,你兴许还一样爱他。有了它,你倒未必,除非他拥有前面四种魅力。”
“不,当然不是。要是他长得丑,是个乡巴佬,兴许,我只会可怜他——恨他。”
“可是世上还有别的漂亮有钱的年轻人呢。兴许比他更漂亮、更有钱。你怎么不去爱他们呢?”
“就是有,我也没有看到。我没见过有谁像艾德加那样的。”
“你会见到一些的。再说他不会总是漂亮,总是年轻,也未必总是有钱。”
“他现在是。我只管现在。我希望你说话讲点情理。”
“好,那就成了,要是你只管现在,嫁给林顿先生吧。”
“这事儿我用不着你的恩准。我要嫁给他。可你还没有告诉我我做得对不对呢?”
“对极了,要是人结婚只图现在没错的话。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什么事叫你不高兴吧。你哥哥会乐意的……那老太太和老先生我想是不会反对的。你可以逃出一个乱糟糟浑身不自在的家,去到一个富足体面的家庭里边。况且你爱艾德加,艾德加也爱你。一切看来称心如意呀,麻烦在哪里呢?”
“这里,在这里!”凯瑟琳回答说,一手拍着额头,一手捶着胸脯,“总之是在灵魂居住的地方。在我的灵魂和我的心里,我确信我是错了尸。
“那倒怪了!我弄不懂它。”
“这是我的秘密,可要是你不来笑我,我就跟你解释。我说不清楚,可我要告诉你我的感觉。”
她重又坐到我的身边,面色变得凄婉沉重起来,紧握的双手也在颤动不止。
“奈莉,你从来没有做过稀奇古怪的梦吗?”她思索了片刻,突然说。
“做过,有时候做。”我回答说。
“我也做。我一生当中做过一些梦,从此之后,这些梦就永远相伴着我,改变我的思想。它们一遍一遍激励着我,就像酒激灵着水,让我的心灵换了色彩。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要来讲了,可是讲到哪儿,你都别笑话它呀。”
“噢!别讲,凯瑟琳小姐!”我嚷道。“没有鬼怪幽灵来纠缠我们,我们已经够凄惨的了。得啦,得啦,快活点儿,守住你的本色吧!看小哈里顿!他可从来不做噩梦。他睡着了,笑得多甜!”
“是呀,他父亲孤寂时分诅咒得多甜哪!我敢说你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吧,那时他也像这胖小子一样,也是这般年少,这般天真烂漫。可是,奈莉,我非要你听不可,话不长,而且今晚我也高兴不起来。”
“我不听,我不听!”我赶忙重申说。
那时候我对梦很是迷信,现在也还迷信。凯瑟琳身上有种异乎寻常的愁容,叫我害怕会有什么不祥之兆,预示一种可怕的灾祸。
她生气了,可是没有讲下去。显而易见她另外寻了一个话头,过了片刻又开口说:
“要是我在天堂,奈莉,我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为你不适宜去那里,”我回答说,“有罪的人在天堂都要痛苦的。”
“不是这么回事儿。有一次我做梦到了天堂。”
“我告诉你我不要听你的梦来着,凯瑟琳小姐!我睡觉去了。”我又打断她说。
她大笑了起来,按我坐下,因为我正要起身离开座椅。
“这没什么,”她喊道,“我只是要说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伤了心要回到地面上来,惹得天使们大发雷霆,一把扔我出去,摔在呼啸山庄的荒野中间。就在那里我醒了过来,快活得直哭。这就足以解释我的秘密了,还有别的愁苦。嫁给艾德加·林顿,其实也和到天堂去一样无味。要是那边那个坏蛋没有把希斯克厉夫打压得如此低贱,我是不会想到去嫁给林顿的。现在嫁给希斯克厉夫,就要有损我的身份。所以他永远都会不知道我多么爱他,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奈莉,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我和他的灵魂里一模一样的。而林顿的灵魂不同于我们,就像月光异于闪电,冰霜异于烈火。”
她这番话还没有说完,我就意识到了希斯克厉夫是在屋里。我察觉到一个小小的动静,转过头去,看到他从长凳上起来,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他一直在听,听到凯瑟琳说嫁给他会有损她的身份,就没有再听下去。
我的同伴坐在地上,正给长椅的高背挡住,没有看到希斯克厉夫是在屋里,以及他又走开。可是我吓了一跳,让她不要作声!
“怎么了?”她问,神经兮兮地四下里张望。
“约瑟来了,”我答道,恰巧听到他的手推车在路上嘎嘎滚过来的声音,“希斯克厉夫会跟他一起进来的。我不知道这会儿他是不是就在门口。”
“噢,他在门口是偷听不着的!”她说。“把哈里顿给我,去弄晚饭,饭做好叫我一声,我跟你一起吃。我要骗骗我那不安的良心,让我相信希斯克厉夫不懂得这一类事情。他是不懂,对吗?他不知道爱起来是怎么回事吧?”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懂,就好像你一样,”我答道,“要是他看中的是你,他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儿!你一旦做了林顿太太,他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失去了一切!你想过你将怎样来承受这分离,他将怎样来做这世上最孤单的人吗?因为,凯瑟琳小姐——”
“他做最孤单的人!我们分离!”她气呼呼地嚷道,“谁分离我们,请问?他们会遭遇米罗米罗(Milo),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著名摔跤手,多次在奥林匹克竞技大会上获胜,传说他要将大树撕裂,因双手夹在树缝中不出,为狼咬死。的命运!只要我还活着,艾伦,没有人敢。这地表上每一个林顿都化作烟云,我也不答应抛弃希斯克厉夫。噢,那可不是我的想法,那不是我的意思!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宁可不当林顿太太!他会像他过去这一生一样,永远伫留我的心上。艾德加必须摆脱他的成见,至少是容忍他。奈莉,我现在明白了,你觉得我是一个自私的坏蛋。可是难道你从未想到过,要是我和希斯克厉夫结婚,就只能当乞丐?所以,要是我嫁林顿,我可以相帮希斯克厉夫发达,把他从我哥哥的淫威中解救出来。”
“用你丈夫的钱,凯瑟琳小姐?”我问。“你会发现他并不像你算计的那样好说话,虽说我不是法官,可我觉得在你告诉我为何要做小林顿妻子的许多动机当中,这动机是最坏最坏的。”
“不对.”她反驳我说,“这动机是最好最好的!其他动机满足我的心血来潮,讲到艾德加,也为满足了他。这个动机却是为了另一个人,在他身上聚合了我对艾德加和对我自己的情感。我说不清楚。可是你和每一个人显然都很明白,在你自己身外,还有,或者说应当有一个你的存在。要是我整个儿就在这里,上帝造我出来又有什么用?在这世上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希斯克厉夫的痛苦,从一开始我就一一注视并且感觉着它们。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思想就是他本人。如果其他的一切毁灭了,唯独他安然无恙,我就还能活下去。如果其他的一切安然无恙,他却灭绝了,宇宙就变成一个巨大的陌生人,我再不像是它的一个部分了。我对林顿的爱像林中的树叶,时光会改变它的,我很清楚,就像冬天改变了树木。我对希斯克厉夫的爱好似树底下恒久不变的岩石,给出一丁点儿可见的快乐,然而是必不可少的快乐。奈莉,我就是希斯克厉夫!他总是,总是在我心里,不是作为一种愉悦,一点也不胜似我自得其乐,而是作为我自己的存在。所以别再讲我们分离,这是不可能的。况且——”
她打住了,把脸藏在我衣裙皱褶里。可是我猛一闪躲开了她,我对她的傻气已是忍无可忍了。
“要是我从你的胡说八道里听出什么名堂,小姐,”我说,“只是叫我明白你一点不懂婚姻要承当的责任,再不你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坏心眼女孩。可是别再拿你的秘密来烦我了,我不答应为你来保守它们。”
“你会守住我那些话吧?”她急切地问道。
“不,我不答应你。”我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