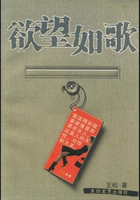我去布里斯托尔
我们为出海作准备所花费的时间比乡绅想象的要长一些。我们预先所设计的计划也都付之东流,甚至连利夫西大夫要我紧随在他身边的想法也落空了。大夫得上伦敦去找一个医生来做他的替身,绅士在布里斯托尔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则住在庄园里由猎场老总管雷德鲁斯负责照看,犹如囚犯一般。然而我一门子心思地幻想着海上冒险,奇异的岛屿、惊险的奇遇在我的心目中展现出一幅诱人的幻象。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面对地图沉思冥想,努力记住每一个细节。我坐在管家房间的火炉旁,想象着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登上那座岛屿;我搜索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无数次地攀登上望远镜山,在山顶上纵情浏览四周变幻万千的自然美景。有时候幻想到岛上成群结队的尽是一些野蛮人,我们同他们展开殊死的搏斗;有时候臆想到岛上有成群的猛兽,追得我们在岛上四散逃命。而这一切与我们其后在岛上遭遇的怪异、凄惨经历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时间就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过去了,直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们收到了一封寄给利夫西大夫的信,信上注明“若大夫不在,汤姆·雷德鲁斯或小霍金斯代折亦可”。遵照这条指示,我们一其实是我,因为猎场总管只认得印刷字体一获得了如下的重要消息。
寄自布里斯托尔老锚旅店一七——年三月一日
亲爱的利夫西院
由于不知道你是否巳从伦敦回到了庄园,我将这封信一式两份地寄向上述两个地点。
我巳买好船只和出海装备,目前停泊待出海。你再也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它更好的纵帆船了——甚至连小孩子都能驾驶它。它的载重量有二吨,船名——伊斯帕尼奥拉。
我是通过我的老友勃兰德里弄到这条船的。他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人,筒直像奴隶般对我言听计从。其实,在布里斯托尔,关于我们这次出海的目的一寻宝的消息一传开,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为我效劳。
“雷德鲁斯,”念到这儿我打住说道,“利夫西大夫会不高兴的,绅士到底还是把这件秘密给捅穿了。”
“算了吧,他们两个谁听谁的?”猎场总管嘟囔道。“我才不信绅士为了讨利夫西大夫的好而闭上自己的嘴巴哩。”
我打消了继续发表看法的念头,继续读信:
勃兰德里亲自发现了伊斯帕尼奥拉号,并且用极其令人惊叹的手段几乎没费什么钱就将它买了下来。布里斯托尔有一帮人老跟勃兰德里过不去,他们甚至诬蔑这个老实人,说他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说伊斯帕尼奥拉号是他自己的,他趁卖船的机会狠狠宰了我一下。这些都是不值一哂的谎言。无论如何,他们谁也无法否认这条船的优点。
到目前为止,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只是那些工匠一索具操纵工什么的一的工作进度慢得令人恼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好转的。我最担心的是水手的配备问题。
我想我们得雇上二十个人——考虑到可能要对付土著人、海盗,以及讨厌的法国人——可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六个人。但天无绝人之路,让我碰上了那个求之不得的人。
我是在码头上碰巧与那个人攀谈上的。我发现他是一个老水手,现在改行开了一家小酒馆,几乎与布里斯托尔的每一个水手都打过交道。他在陆地上呆着反而每天都病恹恹的,希望能上船当一名厨子。据他说,他那天一拐一瘸地来到码头上,只是为了嗅一下海风的咸味。
我听了他的话大为感动——换了你也会感动的——出于同情心,我立即安排他充当我们船上的厨子。他的名字叫高个儿约翰,姓西尔弗,只有一条腿,但我认为这是对他品质的最好证明,因为他是在不朽的霍克淤麾下为祖国服役时失去了那条腿的。他没有养老金。利夫西,你想想这个世道是如何的不公啊。
先生,当时我以为我只不过是找了个厨子而巳,哪知道无形中竟配齐了水手班子。在西尔弗的协助下,我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凑齐了一班名副其实的老水手。他们的外表可能不那么中看,但浑身充满了勇往直前的精神,我敢说他们打斗得过一艘军舰。
在我挑中的六七个人中间,高个儿约翰甚至劝我清除去两个,他没费多大功夫就让我明白,在我们即将开始的重大探险活动中,这种淡水中泡大的废物是万万要不得的。
目前我的身体和情绪都十分不错,吃得好,睡得香,但是,在听到我的那些老水手推动起锚机的响声之前,我是一刻也静不下心来的。嗬,出海去!让宝藏见鬼去吧!使我心向往之的是那壮丽辉煌的大海。啊,利夫西,快来吧,一刻也不要耽误了,如果你还敬我如友的话。
你让小霍金斯马上去向他的母亲辞行,叫雷德鲁斯陪他一同去,然后让他们两人马上赶到布里斯托尔来。
约翰·特里劳尼
又及:我还没有告诉你,勃兰德里一顺便提及,他同意如果我们八月底还不回来,就派另一条船去接我们——为我们找到了一位出色的船长。此人脾气相当倔强,对这一点我表示遗憾,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行家里手。高个儿约翰·西尔弗为我们寻到了一个十分称职的大副,此人名叫埃罗。利夫西,我物色了一位水手长,此人擅长于发号施令。在伊斯帕尼奥拉这条出色的船上,将来的一切管理都会像军舰上一样有条不紊。
我忘了告诉你,西尔弗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人物。据我亲身所知,他在一家银行里有存款,而且从来没有透支过。他将小酒馆留给了他老婆去打理。由于她是一个黑人,恐怕这和健康原因至少在同样程度上迫使他再到海上漂泊一像你我这样的光棍汉作如此猜想应该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再及:霍金斯可以在他母亲那里住一晚上。
约·特
读者可以想象这封信使我兴奋到何种程度,我高兴得都几乎有点忘乎所以了。如果我在这世界上鄙视过什么人的话,那就是老汤姆·雷德鲁斯了。他除了怨天尤人外,其他什么事都干不来。总管手下的任何一名猎场看守在他的位置上都会比他干得好,但乡绅派定了他,而乡绅的指令在他们的心目中犹如法律般神圣不可侵犯。除了老雷德鲁斯外,任何人都不敢在乡绅面前有所抱怨。
第二天早晨,我和雷德鲁斯徒步前往本鲍将军客店。到了那里,我发现母亲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长期以来闹得我家鸡犬不宁的船长,已去了这个坏蛋再也不能惹是生非的地方。在乡绅的安排下,店内损坏的物品都巳修复好,客厅和招牌都巳装饰一新,还添置了一些新家具,并特地在酒柜后面给我母亲摆上了一把漂亮的扶手椅。他还为我母亲招了一个学徒,在我离开家后她也就有一个帮手了。
直到见过那个学徒后,我才明白我巳处于两难的境地。在此之前,我满脑门子想的都是即将开始的探险活动,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即将离开这个家。现在,当我看见这个顶替我留在母亲身边笨手笨脚的小男孩时,我直觉得眼泪禁不止地要夺眶而出。我本可以让这个小男孩的日子不好过的,因为他是一个新手,我有的是机会教训他,出他的丑,而且我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
我们在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吃过午饭后,我和雷德鲁斯又徒步上路了。我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我出生以来就一直住在那儿的小海湾,告别了那块可爱的本鲍将军客店老招牌一重新刷上漆后,它变得反倒不如以前那么可爱了。最后,我又想起了船长,他生前经常戴着一顶三角帽,脸上带着一条弯刀砍的伤疤,胳膊下夹着一副铜框的望远镜,在沙滩上散步。不一会儿我们拐了个弯,就看不见我的家了。
黄昏时分,我们在乔治国王旅店旁石南丛生的荒地上搭上了一辆邮车,我被夹在了雷德鲁斯和一位肥胖的老绅士中间。尽管车速挺快,夜晚又冷,我想我一定是上车后就打起了瞌睡。随着邮车翻山越岭,过了一站又一站,我索性酣睡了过去。因此,当我肋骨上被人戳了一下,睁开眼睛一看时,发现邮车巳停在城里某条街上的一幢大房子前边,天早就大亮了。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问道。
“布里斯托尔,”汤姆回答。“快下车吧。”
特里劳尼先生下榻于码头尽头的一家客店里,以便就近监督帆船的备航工作,我们只能步行到那儿去。一路上,我们看到码头上停靠着许多大小不一、装备不一、国籍不一的船只,这使我感到兴奋不巳。这只船上,水手们在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在另一条船上,有些水手正站在我头顶上的桅杆高处,从下面望上去,仿佛像蜘蛛般攀附在细微如丝的帆索上。虽然我打小就生活在海边,却好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般亲近过大海。柏油和盐的气味使我感到十分新奇,我看到了各种奇妙的船头雕饰,而这些船全都有着飘洋过海的经历。我还看到了许多老水手,他们戴着耳环,蓄着虬髯,辫梢上涂了柏油,目中无人地迈着独特的水手步。即使我见到的是如此多数量的国王或大主教,那股高兴劲儿也莫过于如此。
现在我也要出海了,乘上一艘水手长会吹哨传令,水手都会摇晃着辫子唱歌的纵帆船,乘风破浪,去到一个凡人不知的岛上挖掘埋藏的宝藏!
当我还沉浸在如此令人兴奋的遐想之中时,我们巳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家大旅店的门前,见到了特里劳尼乡绅。他身穿质地厚实的蓝色服装,看上去像一个高级海员。他满面笑容地迎着我们走来,一面还刻意模仿着水手的步伐。
“你们都到了,”他大声招呼道。“大夫昨晚也从伦敦赶了过来。太好了!船员们都到齐了。”“哦,先生,”我喊道,“我们什么时候出海?”
“出海!”他说道。“我们明天就出海!”
在望远镜酒店里
我吃过早饭后,乡绅吩咐我去望远镜酒店给约翰·西尔弗送一张便条。他告诉我,酒店很容易找,只要沿着码头笔直走,看见一家小酒店门口招牌上画着一幅大大的铜框望远镜的便是。我立即出发,为能够再次得到一个观察船只和海员的机会而手舞足蹈。码头上此时一派繁忙景象,我在人群、大车、货包中间择路而行,直至找到了那家小店。
这是一处场面不大但温馨舒适的消遣场所。招牌刚重新漆过,窗户上挂着整洁的红窗帘,地上铺了一层洁净的沙子。店的两面临街且都开有门,因此尽管店内烟气腾腾,从街上仍能将空间低矮的大房间内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店内的食客绝大多数都是水手,他们大声喧闹着,使我怯生生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我正在犹豫不决的当儿,有一个人从偏房里走了出来,我一眼就能断定他就是高个儿约翰。他的左腿一直截到了大腿根儿,但他摆动那根拐杖的灵巧劲儿却令人叹为观止。只见他拄着拐杖一蹦一跳的,灵巧得像一只小鸟。他的身材高大魁梧,脸庞高大的像块火腿肉。他相貌平常,面色苍白,但笑容可掏,并无愚态。确实,他看上去精神十分愉悦,吹着口哨在桌子之间穿来梭去地忙着,碰上喜爱的顾客或是开上几句玩笑,或是友善地拍拍他们的肩膀。
说句心里话,自打我从特里劳尼绅士的信中第一次听说这个高个儿约翰,我便暗自担心他可能就是我在本鲍老店久候多时的那个独脚海上漂,但只那一瞥就足以使我安下心来。我见识过船长,见识过黑狗,也同瞎子皮尤打过交道,我想我对海盗是个什么模样心中有数。在我眼里,这位衣着整洁、态度和蔼的酒店老板与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一下子鼓起了勇气,一脚迈进了门坎,径直朝这个拄着拐杖正与一个顾客交谈的人走了过去。
“您是西尔弗先生吗?”我一边问,一边将便条递了过去。
“是啊,孩子,”他回答道,“不错,我叫西尔弗。你是谁?”这时他瞥见了绅士的便条,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吃了一惊。
“哦!”他惊叹了一声,朝我伸出了一只手。“我明白了,你是新到的实习生。见到你真高兴。”
说着他将我的手握在了他那宽大厚实的手掌中。
就在此时,坐在房间另一端的一个顾客突然站起身来匆忙朝门口走去。门离他很近,转眼间他就走到了街上。但他仓促离开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正是最早到本鲍将军客店来找船长的那个面色如蜡、缺少两根手指头的人。
“快,”我喊道,“抓住他!他是黑狗。”
“我才不管他是谁呢,”西尔弗嚷道。“不过他没付账。哈里,快去把他抓回来。”
坐在离门最近的人中有一个跳起来追了出去。
“他就是霍克将军,也必须付账,”西尔弗嚷道。然后,他松开了我的手,问道院野你说他叫什么来着?黑什么?”
“黑狗,先生,”我答道。“特里劳尼先生难道没有向你提及那帮海盗的事吗?黑狗就是他们中的员。”
“是吗?”西尔弗喊了起来。“在我店里!本,你快去帮哈里的忙。他是那帮坏蛋中的一个,是吗?摩根,你刚才是在和他一起喝酒吧?你过来一下。”
他称之为摩根的那个人一一位一头银发、面孔晒成红木色的老水手一乖顺地走了过来,嘴里还在嚼着烟草块。
“喂,摩根,”高个儿约翰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以前见过那个黑一黑狗吗?见过没有?”
“没有,先生,”摩根回答道,同时举起手来行了一个礼。
“苍天保佑,汤姆·摩根。算你走运!”酒店老板煞有介事地嚷道。“你如果和这帮人搅在了一起,你就别想再踏进我酒店的门,你可别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也没听明白,先生。”摩根答道。
“你说你肩膀上长的究竟是脑袋还是榆木疙瘩?”高个儿约翰斥责道。“没听明白,是吗?你可能连自己说了些什么话也没弄明白吧?你刚才到底嚼了些什么牙巴骨?航海,船长,船只?快点讲出来!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们在谈吃龙骨酱。”摩根答道。
“吃龙骨酱,是吗?确实应该让你们品尝一下那种滋味,你记住我的话。滚回到你的位子上去吧,汤姆。”
等摩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后,西尔弗以一种在我看来十分信任的态度对我附耳低语道:
“汤姆·摩根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家伙,就是有点傻头呆脑的。那么,”他重又提高嗓门说道,“让我想想一黑狗?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没听说过。不过,我好像一对,我想我见过这个混蛋。他以前陪一个瞎眼乞丐来过店里几次。”
“一定是他,没错,”我说道,“我也认识那个瞎子。他的名字叫皮尤。”
“一点都不错,”西尔弗喊道,情绪重新又变得亢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