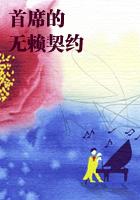我一下子跌坐在坐板上,差一点就摔进海水里去了。一时间,我眼前除了在冒着黑烟的油灯下两张因激怒而涨得通红的脸在摇来晃去外,其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我闭上双眼,以便使它们重新适应黑暗。
冗长难耐的水手歌谣终于唱到了头,仍然呆在篝火旁的少数几个海盗又齐声唱起了那支我早巳耳熟能详的调子:
十五个人趴在死人的木箱上——
唷嗬嗬,再来一瓶朗姆酒!
其余的都做了酒神和魔鬼的祭品——
唷嗬嗬,再来一瓶朗姆酒!
我心中暗自思忖,酒神和魔鬼此刻恐怕正在伊斯帕尼奥拉号的房舱里忙得不亦乐乎,没想到小船忽然一歪曰同时,它来了一个大幅度的转向,似乎要改变前行的方向。这时,潮水的流速也变得异常的快了。
我马上睁开了眼睛。我身旁尽是泛着磷光的细浪,伴随着一阵阵剌耳的声响。小船仍在伊斯帕尼奥拉号后面几码处的旋涡中飘浮,而大船也好像在摇摇晃晃地改变着方向,我瞥见它的桅杆在漆黑的夜色中摇摆了一下。我再定神一看,愈加肯定它也拐向了南面。
我扭头一看,吓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那堆散发着红光的篝火此时正在我的后方。潮水在此处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挟带着大船和我那只上下颠簸的小船一起前行。此时水流愈来愈急,浪花愈溅愈高,潮声愈来愈响,它一路旋转着通过那个狭隘的口子朝外海迅急地退去。
忽然,我前面的大船冷不丁地一偏,大约转了一个二十度的弯曰几乎与此同时,从船上接连传来两声叫喊声,我甚至可以听到匆匆登上升降口的脚步声,心里明白那两个醉鬼终于认识到大难巳经临头,从而停止了他们之间的殴斗。
我趴在那只可怜巴巴的小船里,把我的灵魂虔诚地交给了造物主去安排。我相信我们必将被波涛汹涌的大海所吞噬,那我在这人世间的烦恼都将一了百了。虽然我可能不怕死,但等死的滋味却令我难以忍受。
我大概就这样趴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被巨浪接来抛去,浑身都被浪沫溅湿,每一次都以为下一个浪谷将是我的葬身之地。我渐渐地感到疲惫不堪,头脑一阵阵发晕,竟将恐惧不安抛在了脑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我就这样趴在处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里,梦见了我的家乡和本鲍将军客店。
小船巡航
我醒过来时天巳经大亮了,发现自己飘荡在金银岛西南端的海面上。太阳巳经升起,但还隐身在望远镜山的山峰后面,我暂时还看不见它。望远镜山的这面山体几乎与海面垂直,形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岩峭壁。
我身旁就是帆索海角和后桅山。后桅山是一座深色的秃山,而帆索海角被四五十英尺高的峭壁和崩塌的大块岩石所包围。我离海岸至多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所以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划过去弃舟登岸。
但这个想法立刻被我自己否定了。巨浪正一刻不停地冲击在崩落的岩石上又卷了回来,咆哮着变成一股股水柱喷射飞溅,如果我贸然登岸,即使不被海浪抛到嶙峋的岩石上摔死,也将为攀登悬崖峭壁耗尽自己的力气。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我看到许多可怕的、身体粘糊糊的怪物一像硕大无朋的软体蜗牛一有的在桌面般的岩石面上爬行,有的扑通扑通地跳进海里。这些怪物总共有五六十只之多,它们的吼叫声在悬崖间引起阵阵回响。
后来我才弄明白它们是一群海狮,是一种对人类完全无害的动物。但它们天生的一副怪模样,加上海岸的陡峭和激浪的汹涌,巳足够使我对这一登陆地点望而却步。我宁愿饿死在海上,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此时,我又想到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登陆机会。帆索海角的北面有一片陆地,落潮后会显露出一条长长的金黄色沙滩。在沙滩的北面又有一个岬角一地图上标示的名称是森林岬角,直至海边都长满了高大苍翠的松树。
我记得西尔弗曾提及,沿着金银岛的整个西海岸有一股向北流动的湍流,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判断,我巳经进人了这股湍流的活动范围。于是我决定将帆索海角抛在脑后,养精蓄锐,以便在地形有利得多的森林岬角登岸。
此时,天空中一直刮着柔和的南风,辽阔的海面上泛动着轻微的细浪。风向和湍流的方向一致,因此海浪起伏有度,持续有节。
如果情形不是如此,那我早就完蛋了。但即便是这样,我的这只瞧不上眼的小船能如此轻易地化险为夷,也确实令人啧啧称奇。我躺在船底,漫不经心地朝上望去,常见到一个巨大的蓝色浪峰突兀地出现在我的头顶上空,而小船就像安上了弹簧般只需轻轻一跳,就快捷如小鸟般轻盈地滑进了波谷。
不久我变得大胆起来,便坐起身子来展示我的划桨技巧。但只要我的身体重心稍有变动,就会对小船的行进形成严重的干扰。我刚一挪动身子,小船马上就会一反原来轻柔的舞姿,顺着浪涛的波峰陡然跌落,直弄得我头晕眼花曰紧接着,它又一头扎人另一个浪头深处,激起一阵飞沫。
我一下子被海水浇了个浑身透湿,惊恐万分,急忙照原样躺下。此时小船似乎也恢复了常态,轻盈地载着我在浪波中穿行。看来,它不愿意让人力来干预它的行进节奏。但如果我不能调整它的航速,照它这种行进的速度,我还有上岸的希望吗?
这个念头将我吓得半死,然而头脑却还算清醒。我先是极小心地用水手帽将船里的积水舀了出去,然后重新从船底向上观察,我要弄明白它是如何能够这样平稳地滑行过一个又一个浪头的。
我发现,每一个浪头从岸上或是大船上看上去像是一座浑圆的大山,但实际上却像陆地上延绵的丘陵,既有峰顶,也有平地和溪谷。在没有人力干预的情况下,它自会在水中扭来摆去,专挑低凹的地方行进,避开浪尖波峰。
“我现在明白了,”我暗自思忖道,“为了保持船身的平衡,我必须躺着不动。但同样清楚的是,我可以将桨伸出船外,在平坦处不时划上几桨,让它尽快地拢岸。”说做就做。我用双肘支起身子,全然不顾身体的别扭,不时轻轻地划上一两桨,使船头始终对着陆地。
这真是一件十分费力而又进展缓慢的苦差事,但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效果,因为小船巳接近了森林岬角。虽然我也看出我肯定不能在那里登岸,但我还是向东划了几百码。事实上我巳逼近了陆地,巳看得清被风吹得一边倒的绿色树梢。我确信在下一个岬角我一定上得了岸。
此时登上陆地巳成为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因为我巳经渴得受不了啦。我头顶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身下是折射着太阳热量的波浪,浑身布满了海水被蒸发后留下的盐渍,嘴唇上也布满了盐霜。这一切合在一起使我喉干如焚,头痛欲裂。近在咫尺的树林却不能为我遮荫避暑,真使我感到揪心揪肺般的难受,但湍流很快地将小船冲过了岬角。当又一片宽阔的海面展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景象立即改变了我原先的想法。
就在我前方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我看见伊斯帕尼奥拉号正在扬帆前行。我当然清楚他们肯定会将我抓起来,但我口渴得实在厉害,几乎无法判断此种前景对我来说是喜还是忧。我还没来得及得出结论,潜意识里就对这种想法感到吃惊,以致除了睁大眼睛发呆外,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伊斯帕尼奥拉号正扯着主帆和两张三角帆在航行着,漂亮的白帆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烁,洁白如雪。当我第一眼瞧见它的时候,它所有的帆都鼓满了风,正沿着西北方向航行,我猜想船上的留守者正打算绕过金银岛将它开回锚地去。现在它的航向愈来愈偏西,我想他们可能是发现了小船,正赶过来活捉我。然而,最终它的船头竟转过来对准了风吹过来的方向,完全处在了逆风状态。它无助地停留在了原地,风帆贴着桅杆簌簌地抖动着。
“这两个笨蛋,”我自言自语地骂道,“他们现在还一定醉得不省人事呢。”我想要是让斯莫利特船长知道了他们如此笨拙地操纵伊斯帕尼奥拉号,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
这时,大船缓慢地偏向了下风,重新撑满一帆风后掉转了航向,快速航行了约一分钟,然后重又对准了风吹来的方向停了下来。它又如此这般地反复转了好几次。伊斯帕尼奥拉号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顺着风,一会儿逆着风;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南,一会儿朝北,每一次横冲直撞的结果都是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只是让帆劈劈啪啪地空飘了一阵。我这时才看出船上根本就没有人掌舵。如果情况果真是如此,那么船上的人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猜测道,他们要么就巳经烂醉如泥,要么就是弃船逃跑了。如果我能登上大船的话,没准能将伊斯帕尼奥拉号开回去还给船长。
湍流正以同样的速度带动着小船和大船,但大船的行动毫无规则可言,它时断时续的,每次打圈时总有好长一段时间船头迎风停住,因而即使没有倒退,此时也几乎寸步未进。只要我敢坐起来划桨,我就一定能够追上它。这个计划所带的冒险成分剌激了我,再想到放在前升降口旁边的淡水桶,更使我感到勇气倍增。
我刚才坐起来,几乎立刻就被溅了一身海水,但这一次我是下定了决心,使出全身力气,同时又极其小心谨慎地朝着无人驾驶的伊斯帕尼奥拉号划去。有一次,一个浪头将大量的海水带进了小船,我只得停下桨来向外舀水,心像鸟儿的翅膀般扑楞着。但熟能生巧,慢慢地我就能划着小船在海浪中蜿蜒穿行了,只是海浪偶尔会撞击船头,溅起一股飞沫喷洒在我的脸上。
我正在以飞快的速度逼近大船。我巳看得清铜制的舵柄左晃右摆发出的光亮,而甲板上还是杳无人迹。我只能假设他们是弃船逃跑了,或是醉倒在了船舱里,我也许可以将他们锁在里面,然后随心所欲地处置伊斯帕尼奥拉号。
有一段时间,伊斯帕尼奥拉号处于我最不愿意见到的状态一它停在原地不动了,船头几乎朝着正南方向,当然时有偏差。每次它偏离正南方,它的风帆就会部分地鼓了起来,这样又立刻使它对准了风向。我刚才说过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状态,因为此时伊斯帕尼奥拉号貌似处于孤零无助的境地,帆篷啪啪响得似在放炮,滑车在甲板上辘辘地滚,乒乓有声,但它不仅是以湍流的速度继续往北飘,还得加上它本身引起的极大的风压差,因此速度极快,小船怎么也赶不上它。
不过我现在总算逮住了一个机会。有那么短暂的一会儿,风几乎完全平息了下来,伊斯帕尼奥拉号在湍流的作用下又缓慢地在原地打旋,最终使我看到了船尾。房舱的窗子依旧敞开着,挂在桌子上方的一盏灯在大白天里仍旧点燃着,主帆则像一面旗帜般耷拉着身子。要不是湍流的带动,船就会完全停下来。
刚才有那么一小会儿工夫我都要放弃追赶它的努力了,现在我又鼓足了勇气,再次朝着我的目标穷追不舍。
我在离大船巳不足一百码距离的时候,风又刮了起来。大船向左舷一转,让帆又鼓满了风,像燕子掠水般又向前滑行起来。
我先是感到一阵绝望,但继而又转忧为喜。伊斯帕尼奥拉号掉转船身,直到它的一侧向我靠拢过来,将两只船的距离缩短至一半、二分之一、四分之三。我巳经能够看到海浪在它的龙骨前端翻腾的白沫。从我乘坐的小船上仰望过去,它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
这时,我突然明白自己巳大难临头了。我来不及思索,更谈不上采取任何自救措施。当大船越过另一个浪头时,小船正处在另一个浪尖上,此时船首的斜桅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方。我纵身向上一跃,小船应声朝水下一沉。我一只手攀住了三角帆桁,一只脚嵌在了支索和转帆索中间。就在我这样悬在空中心评评直跳的当儿,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我知道大船的庞大身躯巳将小船撞沉,我也就此被切断了退路,只能听天由命地呆在伊斯帕尼奥拉号上了。
我扯下了骷髅旗
我刚攀上船首的斜桅,三角帆就像放炮似的响了一声,随即鼓满了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大船转向时整个船身乃至龙骨都颤动有声。但随后,虽然别的帆都还张着,船首的三角帆却收了回来,软绵绵地低垂着。
大船的这一动作差一点将我抛到了大海里去。这时我毫不迟疑地顺着斜桅往下滑,终于头朝下地跌落在甲板上。
我的位置处在水手舱背风的一侧,扬起的主帆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清后甲板的一部分。此时我没看见一个人。甲板自叛乱开始后就没有清洗过,上面残留着许多杂乱的脚印。一只断颈的空瓶在排水孔之间滚来滚去,犹如有生命的活物一般。
突然,伊斯帕尼奥拉号又迎头朝向了风。三角帆在我身后啪啪作响,舵也戛然有声,整个船身犹如病人般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就在这一刹那间,主帆桁向舷内一摆,帆脚索的滑车呻吟了一声,下风面的后甲板一下子就暴露在了我的眼前。
那两个留守的海盗千真万确就呆在后甲板上。戴红睡帽的那个家伙仰面一动不动地躺在甲板上,龇牙咧嘴,两臂伸开,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似的。伊斯雷尔·汉兹伸直双腿靠舷壁坐着,下巴垂在了胸前,双手平摊着放在身前的甲板上,原先晒成棕黑色的脸庞现在却透露着蜡样的惨白。
顷刻间,大船像一匹烈马般腾空而起,帆全都鼓满了风,一会儿朝着这一边,一会儿又转向另一边。帆桁来回晃荡,使得帆樯发出承受不住的呻吟声。不时还有一阵阵浪花飞越舷墙,而且可以明显感觉到船头撞击浪花引起的船身的颤动。总而言之,这艘装备精良的大船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无论摇晃得多么厉害,比起我那只巳沉人海底的原始小船来说还是稳当得多。
船每跳动一下,戴红睡帽的海盗就跟着左右晃动,但看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院尽管被风浪颠簸得摇来晃去,他的姿势和龇牙咧嘴的怪模样却丝毫没有变化。同样,随着船身的每一次跳动,汉兹的身子就越往下沉,与甲板的接触面就越大,两腿就伸得越远,整个身子也越来越向船尾一侧倾斜,使他的脸部逐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最终我只能看到他的一只耳朵和一绺毛茸茸的络腮胡子。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在他俩身边的甲板上有着斑斑血迹,不禁推测到他俩是在醉后的狂怒中互相残杀、同归于尽了。
我正惊讶地瞧着这个场面沉思着,在船身巳趋平稳的这个时刻,伊斯雷尔·汉兹半转过身来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扭动着身躯恢复到我原先看到的那种姿势。那一声呻吟一表露出他正处于痛苦和极度的虚弱之中一以及他那副张着下颚的可怜模样使我不仅动了恻隐之心,但我一想起躲在苹果桶里偷听到的那些阴谋,怜悯之心转瞬间化为了乌有。
我向船尾走去,在主桅杆前停了下来。
“我上船向您报到来了,汉兹先生。”我用嘲弄的口吻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