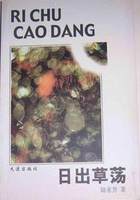我在岸上的惊险奇遇是如何开始的
第二天清晨我重新登上甲板时,那个岛屿完全变了一副模样。虽然微风巳逝,船还是行驶了一大段距离,此时正停在地势较平坦的东岸东南约半公里处。海岸上有很大一部分覆盖着一片灰蒙蒙的森林,单调的色彩中间杂着一条条带状的黄沙低地,并有不少松柏科参天大树,或独自屹立,或三五株共生,但整个色调略显单调凄冷。山顶没有植被覆盖,怪石嶙峋。望远镜山比其他山的海拔要高三四百英尺,山势奇特,四面呈刀削斧劈状,山顶却平坦如砥,犹如一个安放雕像的底座。
伊斯帕尼奥拉号在涌浪中颠簸得十分厉害,排水口在水中时隐时现,帆的下沿像是要把滑车撕扯下来,舵左右摇晃着砰然作声,整个船身像开工的作坊叽叽嘎嘎直响,又像一个病人呻吟翻滚着。我只觉得一阵天晕地转,不由地紧紧地抓住了后牵索。尽管在航行过程中我巳习惯了船身的颠簸,但船现在却像水中的一只瓶子般在原地打转,这却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再加上清晨肚子中空空如也,我不禁感到一阵阵恶心。
也许是出于这个缘故,也许是由于瞥见了岛上色调单一的森林和岩石裸露的山顶,耳闻目睹了飞浪拍击陡岸的白沫和轰鸣,此时尽管阳光灿烂温暖,无数只海鸟在我们身旁鸣叫觅食,按常理说我们又在海上漂流了如此久的时间,任何人都会乐于上岸,然而我的心情却不可理喻地坏到了极点。从我瞥见它的那一刻起,我就恨上了金银岛。
这天上午有一大堆活等着我们去干。海面上全无起风的迹象,我们只得将划子放下船去,每只划子上配备一些人手,用绳索拖着伊斯帕尼奥拉号行进三四英里绕过岛的一端,顺着一条狭窄的海峡驶进骷髅岛后面的港湾。我自告奋勇地坐上了一只划子,其实在上面我并无事可干。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水手们一边干活,口里一边抱怨个不停。在我乘坐的划子上管事的是安德森,他不但不管束手下的水手,自己的叫骂声反而比谁的都响。
“走着瞧吧,”他夹带着一句诅咒说道,“这活儿很快就会干到头了。”
我想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到目前为止,水手们干起活来还是主动卖力的,但一见到金银岛,纪律就松弛下来了。
在进港的途中,高个儿约翰始终站在舵手身旁给船引航。他对这条航道的情况了如指掌,尽管用测链测得的水深每一处都比图上标的要深,约翰却显得胸有成竹。
“这里退潮时水泻得很急,”他解释道,“因此航道被冲刷得愈来愈深了,就像用铁锹铲过一样。”
我们将船停在海图上标明的锚地上,相距两岸各约三分之一英里,一边是主岛,另一边是骷髅岛。水底是清澈的沙地。船锚落水的响声惊起了大群的海鸟,它们在树林上空盘旋惊叫,但不一会儿又都飞回了原处,四周又重归静寂。
这个港湾完全被陆地所环绕,被森林所覆盖,树木一直延伸至海潮线上。海岸的地形大致平坦,远处的几座山峰呈半圆形环抱着这片陆地。有两条小河一更确切地说是两块沼泽地一的水流人这个平静的像池塘般的港湾。这一带植物叶子闪烁的光泽看上去仿佛是蕴含着毒素似的。从船上望过去,陆地上既看不见房屋,也瞧不见栅栏,因为它们都掩映在树林之中。要不是升降口上挂着那张图,我们还会误以为自己是这个岛屿形成以来的第一批造访者呢。
空气里没有一丝风流动,也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半英里外传来的海湾拍击沙滩及峭壁的轰鸣声。锚地上空飘浮着一股怪味一树叶和树干腐烂的臭味。我瞧见大夫不停地皱着眉头东闻西嗅,就像一个人在吃臭鸡蛋似的。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埋有宝藏,”他抱怨道,“但我敢肯定这里一定有热病。”
如果说水手们在划子里的所作所为巳引起我的警觉的话,那么他们在登上大船后的举动在我看来就更具有威胁性了。他们在甲板上游来晃去,扎成堆地密谈着,哪怕要求他们做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招致他们的白眼,即使勉强去做也是敷衍塞责,马虎了事。甚至连最老实的水手也会照着样子去学,因为船上巳没有是非曲直的观念了。显然,暴乱的危机就像雷雨前的乌云笼罩在我们的头顶。
并不仅仅是我们几个在房舱里开过会的人预感到了危机的降临。高个儿约翰也正忙忙碌碌地从一堆人那里扎向另一堆人群里,竭尽全力地进行着游说活动,在这一点上他可真算是做到家了。他的态度十分主动热情,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如果有人吩咐他做某件事,他会忙不迭地应道院野哎,哎,先生!”并立刻拄着拐杖遵命而行。如果实在是无事可干,他会不停地唱歌,仿佛想掩饰住其他人的不满情绪似的。
在那个危机四伏的下午所呈现出的全部不祥征兆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高个儿约翰所显露出的焦虑不安的态度了。
我们在房舱里开会商讨对策。
“先生们,”船长说道,“如果我再贸然下任何命令,全体水手就会揭竿造反了,这形势你们大概也看清楚了。先生们,刚才不是有一个水手粗鲁地拒绝了我的命令吗?如果我呵斥他,马上就会有人向我投长矛;如果我装聋作哑,西尔弗就会瞧出里面的猫腻,那就露焰了。现在我们只能依赖一个人了。”
“谁?”乡绅问道。
“西尔弗,先生们,”船长回答道,“他与你我一样急于将局面稳住。他们只是在某一点上看法不一致,如果逮住了机会,他会说服他们的,我建议我们故意给他这个机会。我建议下午放水手们上岸。如果他们真上岸了,船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他们不上岸,那我们就占住房舱,上帝自会帮助正义者的。如果只有几个水手上岸,先生们,我敢保证,西尔弗会像赶绵羊般将他们带上船来的。”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下来。我们给可靠的水手分发了装上弹药的手枪,并向亨特、乔伊斯、雷德鲁斯等人交了底,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感到吃惊,相反却显得斗志高昂。然后,船长走上甲板对全体水手训话。
“朋友们,”他说道,“今天的工作很累,大家都干得格外辛苦,上岸去逛逛对大家的身体有好处。划子都还在水中,如果大家愿意,你们下午都可以上岸去。在日落前半小时,我会鸣炮通知大家返回船上的。”
那帮蠢货大概以为一上岸就会拣到金银财宝,所以他们一扫郁闷的表情,一个个笑逐颜开,欢呼声竟在远山间激起了回响,并再次将鸟群惊飞了起来,它们呱呱乱叫地在锚地上空盘旋着。
船长十分识趣,他立刻抽身走开,以免碍了他们的事,谁上岸谁留守任由西尔弗去安排。船长也只能这么行事。如果他继续留在甲板上,事情巳明摆在了那儿,他也不可能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模样了。船长实际上是西尔弗,手下有一帮欲跟随他造反的水手。那些诚实的水手一我发现船上还是不乏这样的人一却长着个榆木脑袋,或更确切的说法是院全体水手都或多或少地受了这个首领行为的影响,只是作恶的程度不同而巳。有几个水手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在斜路上看来不至于会滑得太远,毕竟吊儿郎当、偷懒耍滑还算得上是于法无碍,但夺船害命却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人员的去留问题最终定了下来。六名水手留在了船上,其他十三名水手,包括西尔弗,开始乘划子上岸。
这时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第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一这以及以后一系列疯狂的想法最终才使我们得以死里逃生。如果西尔弗留下了六名水手,我方显然巳不能将船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样的道理,既然船上只留下了六名水手,房舱里的一方也没有必要让我留下来帮忙。我立即决定和他们一起上岸去。我眼疾手快地一骨碌翻过船舷,蜷缩着身子坐在了艏座上。几乎与此同时,划子驶离了大船。
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行动,只有前桨手说了一句院野是你啊,吉姆,把头低下去。”但乘坐在另一只划子上的西尔弗用犀利的目光朝我这边扫了一眼,试探地喊了一声,以便确定我是否上了划子。从那一刻起我就对我的贸然行动感到了后悔。
水手们争先恐后地朝岸边划去。我乘坐的那只划子启动的时间略早,船身又轻,桨手们也划得更卖力,所以遥遥领先。靠岸时,划子一头钻进了岸边的丛林。我攀住一根枝条纵身上岸,将身子隐进了一片丛莽之中,而此时西尔弗和其他的水手起码落后于我有一百码之遥。
“吉姆,吉姆!”我听见西尔弗在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
我没有理睐他。我连蹦带跳,忽而猫着腰钻人草丛,忽而在灌木丛中劈荆开路,头也不回地向前奔跑,直到再也跑不动为止。
第一次打击
我暂时逃出了高个儿约翰的掌心,心中不禁有几分得意,居然颇有兴致地观赏起我刚踏足其间的这块陌生陆地的自然风光来。
我刚穿过一片长满杨柳、芦苇及许多卑湿怪异树木的沼泽地带,来到了一片沙土起伏、约一英里长的开阔地带边缘。这里松柏长势稀疏,却生长着大量树干虬曲略似麻栎,但叶色淡如杨柳的树木。开阔地带的另一端是一座双峰小山,它那两个形状奇特的山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此时我心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探险的乐趣。这座小岛荒无人烟,同行的水手巳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除了不谙人语的鸟兽,谁也不会阻挡我的进路。我在树林中间东走西逛,一路上不时遇见各种叫不上名称来的花木,间或也能碰上几条蛇。有一条蛇从岩石缝隙里昂起头来,朝着我发出有点像陀螺旋转时的咝咝声,我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能致人于死地的响尾蛇,那声音正是它振动尾部的环而发出的特征响声。
接着我走进了一处幽长的、尽是那种状似麻栎树的丛林。后来我听说这种树叫做常青栎或常绿麻栎。它们像荆棘般贴着沙地生长,丫枝扭曲成奇形怪状,叶子茂密得像茅草扎的屋顶。这片丛林从一个沙丘顶上蔓延下来,愈往下生长得愈浓密、愈高大,一直延伸到一片广阔的芦苇塘边,附近的一条小河就是由此地流人锚地的。沼泽地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雾气腾腾的,望远镜山在这片雾霭中时隐时现着。
芦苇丛中骤然响起一阵沙沙声,一只野鸭嘎的一声腾空而起,紧接着又飞起了一只,旋即在整个芦苇塘的水面上空腾起浮云般的一大群野鸭,嘎嘎叫着在半空中盘旋。我立即猜测到我的几个同伴正沿着塘边走了过来。我的判断没有错儿,很快我就听到远处传来一个人模糊的低语声曰我继续凝神倾听,那声音是愈来愈清晰、愈来愈近了。
这下可把我吓得不轻。我钻到离我最近的一棵常青栎的顶盖下,蹲在那里竖起耳朵屏息静听,活像一只受惊的老鼠。
另一个声音在应答着,然后,第一个声音一我听出那是西尔弗的嗓音一接了过去,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另一个声音不时地附和着。从语调上听来,两人谈得十分投人,但我一句话也没听明白。
最后,两人似乎都住了口,也可能是两人一块坐了下来,因为我不仅再也没有听见他们逼近的脚步声,而且连野鸭也安静了下来,重又回到了芦苇塘中原先栖息的地方。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失职了。既然我莽撞地随这帮亡命之徒上了岸,至少可以去偷听一下他们密谈的内容。目前我要做的就是院以这片丛树林作掩护,尽可能悄悄溜到靠近他们身边的地方。
我可以准确地判定那两个人所处的位置,因为除了他俩说话的声音外还有一个标志:还有几只野鸭在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头顶上空不安地盘旋着。
我手脚并用,缓慢而沉着地朝他们那边爬行着,直到我抬起头,从树叶的缝隙里朝外望去。清晰地映人我眼帘的是沼泽旁一小块草木葱茏的谷地,高个儿约翰·西尔弗和一个水手正站在那儿交谈着。
太阳光正直射在他们身上,西尔弗巳将帽子摘下来扔在了身边的地上。他那宽大、光滑、白皙的脸庞热得冒油,正急切地对着另一个人的脸,仿佛在努力说服他。
“伙计,”他说道,“我是把你当成人中豪杰才向你说这番话的。人中豪杰,你可以相信我的话!要不是我认为你是一条汉子,我又何必与你多费口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你是无法改变的。我说这番话完全是为了救你一命。要是这话被那帮不顾死活的家伙听去了,他们会怎样收拾我?汤姆,你说呀,他们会怎样收拾我?”
“西尔弗,”那个水手说道,我注意到他不仅脸色涨得通红,而且嗓音像乌鸦鸣叫般的嘶哑,像绷紧的绳索般发颤。“西尔弗,”他说道,“你巳上了年纪,并且诚实,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你有钱,而别的水手都很穷。如果我没看错人的话,你还十分勇敢。你为什么要与那班蠢货搅在一起呢?你实在是犯不着!换了我,即使砍掉我的一只手我也不愿违背自己的职责,我可以以上帝的名义起誓——”
他的话被突如其来的一阵声响所打断。我在此处才发现一个诚实的水手,同时另一处又传来了同样的好消息。在远处的沼泽地里蓦地响起一声激怒的呼喊声,紧接着又传来了一声,随后是一声拖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望远镜山的峭壁被激起了数声回响。芦苇塘里的野鸭群再次一起振翅惊飞,黑鸦鸦地遮蔽了半个天空。那声濒死前的哀嚎还良久地在我脑海中回荡,尽管四周又重归寂静,只有野鸭重归芦苇塘的扑翼声和远处大海汹涌澎湃的怒涛声扰动着这午后令人倦怠的静寂。
汤姆听到这声呼喊,犹如马被靴剌剌了一下似的蹦了起来,但西尔弗连眼皮都未眨一下。他半倚着拐杖站在原地,像一条伺机蹿起噬人的毒蛇,两眼死盯着他的同伴。
“约翰!”那个水手高声喊道,同时伸出他的双手。
“不许动!”西尔弗大声喝道,同时身体向后霍地跳出了一码的距离,身手之敏捷犹如一个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
“我不动,约翰·西尔弗,”那个水手说道,“你如果心里没有鬼,就不用怕我。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问我那边发生了什么事?”西尔弗诡笑着反诘道,此时他的那双眼睛在他那宽脸庞上显得只有针尖般大小,但却如玻璃珠一般发亮。“是吗?我想那一定与艾伦有关。”
一听这话,汤姆立刻勃然大怒,显露出了惊人的勇气。
“艾伦!”他大叫道。“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他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手,至于你,约翰·西尔弗,我长期以来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朋友,但现在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即便命中注定要悲惨地死去,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你们巳经谋害了艾伦,是吗?如果你们办得到,把我也杀了吧,但我鄙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