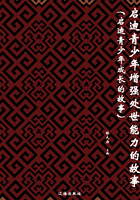我把日常生活安排得称心如意。我的主人吩咐,在离它家大约六码远的地方,按照它们的式样给我盖了一间房。我在四壁和地面涂了一层粘土,然后铺上我自己设计编制的草席。我把那儿的野生麻打松做成被套,里边填进各种鸟的羽毛。我用小刀做了两把椅子,比较笨重的活是栗色小马帮我干的。我的衣服都穿烂了,我就用兔子皮和跟兔子一样大小的一种美丽动物的皮另做了几件新衣服和几双蛮不错的长统袜。我用从树上砍下来的木片做鞋底,上到帮皮上,鞋帮穿烂了就再用晒干的“野胡”皮作鞋帮。我常常从树洞里找到一些蜂蜜,有时掺上水喝,有时和着面包吃。我身体非常健康,心境平和。没有朋友会来算计我、背叛我,也没有公开或者暗藏的敌人来伤害我。我不必用贿赂、焰媚、诲淫等手段来讨好任何大人物和他们的奴才。我不用提防会受骗受害。这儿没有医生来残害我的身体,没有律师来毁我的财产,没有告密者在旁监视我的一言一行,没有人会受人雇佣捏造罪名对我妄加控告。这儿没有人冷嘲热讽、批驳非难、背地里说人坏话,也没有扒手、盗匪、人室窃贼、论棍、鸨母、小丑、赌徒、政客、才子、性情乖戾的人。说话冗长乏味的人、辩驳家、强奸犯、杀人犯、强盗、古董收藏家;没有政党和小集团的头头脑脑以及他们的扈从;没有人用坏榜样来引诱、唆使人犯罪;没有地牢、斧钺、绞架、答刑柱或颈手枷;没有骗人的店家和工匠;没有骄傲、虚荣、装腔作势;没有花花公子、恶霸、醉汉、游荡的娼妓、梅毒病人;没有吹牛。淫荡而奢侈的阔太太;没有愚蠢却又自傲的学究;没有啰啰嗦嗦、盛气凌人、爱吵好闲、吵吵嚷嚷、大喊大叫、脑袋空空、自以为是、赌咒发誓的伙伴;没有为非作歹却平步青云的流氓,也没有因为其德行而被贬为庶民的贵族;没有大人老爷、琴师、法官和舞蹈教师。我非常有幸能和一些“慧”见面,并一起进餐,这种时候它总是十分仁慈地准我在房里侍候,听它们谈话。它和它的客人常常会屈尊问我一些问题,并且听我回答。交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言简意骇,最讲礼貌,却丝毫不拘于形式。没有人说话不是自己说得高兴,而是同时又使听的人听着开心;没有人会打断别人的话头,会冗长乏味地说个不停,会争得面红耳赤,会话不投机。它们有一个看法:大家碰在一起的时候,短暂地沉默一会儿确实对谈话有很大好处。这一点我倒发现是真的,因为在那不说话的短时间的沉默里,新的见解会在它们的脑子里油然而生,谈话也就越发生动。它们谈论的题目通常是友谊和仁慈,秩序和经济,有时也谈到自然界的各种可见的活动,或者谈古代的传统,它们谈道德的范围、界限,谈理性的正确规律,或者下届全国代表大会要作出的一些决定,还常常谈论诗歌的各种妙处。
我坦白承认,我所有的那一点点有价值的知识,全都是我受主人的教诲以及我听它跟朋友们谈话中而得来的。我听它们谈话比听到欧洲最伟大、最聪明的人物谈话还要感到自豪。我钦佩这个国家的居民体力充沛、体态俊美、行动迅捷,这么可爱的马儿,有着灿若群星的种种美德,使我对它们产生了最崇高的敬意。
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同胞或者全人类,不论从形体上还是从性情上看,他们还确实是“野胡”,只是略微开化,具有说话的能力罢了。可是他们只利用理性来增长罪恶,而他们在这个国家的“野胡”兄弟们倒只有天生的一些罪恶。有时我在湖中或者喷泉旁看到自己的影子,恐惧、讨厌得赶快把脸别过一边去,觉得自己的样子还不如一只普通的“野胡”来得好看。因为我时常跟“慧”交谈,望着它们我觉得高兴,渐渐地就开始模仿它们的步法和姿势,现在都已经成了习惯了。朋友们常常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我走起路来像一匹马,我倒认为这是对我的极大的恭维。我也不得不承认,我说起话来常常会模仿“慧”的声音和腔调,就是听到别人嘲笑我,也丝毫不觉得因丢面子而感到生气。
我正过着快乐的生活,想自己就此安居度日,可是一天早晨,比平时还更早一些,我的主人把我叫了过去。我看到它的脸色就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事。它说,上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起“野胡”问题时,代表们都对它家里养着一只“野胡”(指我冤而反感,而且养“野胡”倒像对待“慧”一样。大家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大会郑重劝告它,要么像对我的同类一样使用我,要么命令我还是游回我原来的那个地方去。凡是曾经在主人家或者它们自己家见到过我的“慧”都完全反对第一种办法。它们认为,我除了那些动物天生野性外,还有几分理性,这就要担心,我可能会引诱“野胡”们跑到这个国家和森林或者山区里,到了夜里再带着它们成群结队地来残害“慧”的劳动成果,因为我们不爱劳动,生性贪荽。
我的主人又对我说,附近的“慧”天天都来催促它遵照代表大会的劝告,它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它希望我能做一种像我曾经向它描述过的、可以载着我在海上走的车子。它自己的仆人和邻居家的仆人都可以帮我的忙。但是,它自己很愿意留下我来一辈子给它做事,因为虽然我天性脾劣,却也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效仿“慧”,并因此改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坏习惯和坏脾气。
听了我主人的话后,我非常悲伤,痛苦得无法自支,就昏倒在了它的脚下。我苏醒后它才告诉我,它刚才都断定我已经死了,因为这里的“慧”不可能天生那么没有用。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真要是死了倒是莫大的幸福。我虽然不能埋怨代表大会作出那样的劝告,也不能怪它的朋友们来催促它,然而从我微弱、荒谬的判断来看,我想它们对我稍许宽容一点,也还是符合理性的吧。我游泳一里格都游不到,而离它们这儿最近的陆地可能也要在一百多里格以外的地方。做一只小小的容器把我运走,所需要的许多材料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为了顺从主人的意见,我还是想来试一试。我请求它给我以充分的时间来做这项艰巨的工作。
我的主人只简单的回答了我几句。它答应我两个月的时间让我把船造好,同时命令那匹栗色小马听我的指挥。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它陪着我到当初反叛我的那些水手逼我上岸的那一带海岸去。我爬上一座高地,向四面的海上远眺。我好像看到东北方向有一座小岛,于是我拿出袖珍望远镜,结果清清楚楚看出大约五里格以外(我估算)还真是一座小岛。但是在栗色小马看来那只是一片蓝色的云,因为它不知道除了它自己的国家外还存在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能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可以熟练地辨认出大海远处的东西,我们却是熟谙此道的。
我发现了这座小岛之后,就不再多加考虑了。我决定,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就是我的第一个流放地,结果会怎样就只好听天由命吧。
回到家里,我和栗色小马商量了一番之后,就一起来到不很远的一处灌木林里,开始砍树造船。六个星期之后,在粟色小马的帮忙下,我制造成了一只印第安式的小船,不过要比那种船要大得多。我用自己搓的麻线将一张张“野胡”皮仔细缝到一起把船包起来。我的帆也是用“野胡”皮制做的,不过我找的是最小的“野胡”,老一点的“野胡”皮太粗太厚。我还准备了四把桨。我在船上存放了一些煮熟的兔肉和禽肉,还带了两只容器,一只盛着牛奶,一只装着水。
我在我主人家旁边的一个大池塘里试航了一下我的小船,把不妥的地方改造了一番,再用“野胡”的油脂把裂缝堵好。最后,我见小船已经结结实实,可以装载我和我的货物了。当我尽力将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我就让“野胡”把小船放到一辆车上,在栗色小马和另一名仆人的引导下,由“野胡”慢慢地拖到了海边。
一切都准备好了,行期已到,我向我的主人、主妇和它们全家告别。我的眼里涌出泪水,感到心情十分沉痛。我的主人一方面出于好奇,一方面出于对我的友好决定要去海边送我上船,还叫了它邻近的几位朋友随它一同前往。
一七一四(也许是一七一五)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九点,我开始了这一次险恶的航行。风很顺,不过开始我只是用桨在那里划,但考虑到这样划下去人很快会疲劳的,而风向也可能会改变,我就大胆地扯起了小帆。就这样,在海潮的帮助下,我以每小时一里格半的速度前进着。我的主人和它的朋友一直站在岸上,差不多无法看到我时才离开。我还不时听到那匹栗色小马在喊:“赫奴伊·伊拉·奴哈·玛加赫·野胡。”(“多保重,温顺的野胡!”)我本来打算,只要有可能,就找那么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岛,依靠自己的劳动,度过自己的余生。我一想到要回到那个社会中去受“野胡”们的统治,就万分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