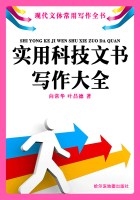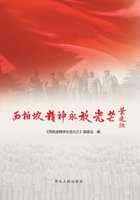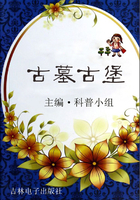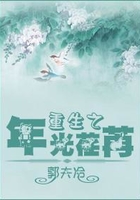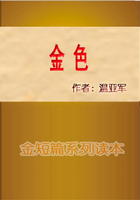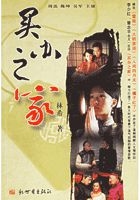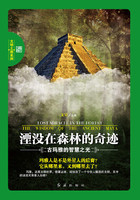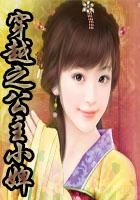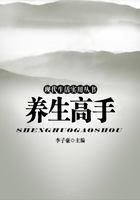德沃夏克是捷克卓越的民族主义音乐家。捷克历史上被称作波希米亚,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广出音乐人才,波希米亚乐师流入欧洲各地文化城市,对德奥古典音乐传统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这里有“欧洲的音乐学院”的美称。捷克名城布拉格的居民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许多音乐家曾在这里获得最初的成功,如莫扎特、帕格尼尼、老约翰·施特劳斯等。这里的人民也有分明的爱憎,1848年欧洲革命,老约翰·施特劳斯投向保皇党,写了着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遭人唾弃,出走国外,在布拉格演出遭当地市民抵制,甚至砸了他演出的场所。德沃夏克1866年到1873年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乐队拉中提琴,乐队指挥是斯美塔那,后来两人都成了享誉世界的大作曲家。
德沃夏克是一位多产作曲家,在创作旺盛的中年时期在欧洲名声远扬,曾九次访问伦敦,1891年他50岁,英国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音乐学博士名衔,也是在这年,美国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的创始人萨尔伯夫人向德沃夏克发出邀请,诚恳地请他主持音乐学院,聘期是两年。德沃夏克经再三犹豫,最后,还是接受了萨尔伯夫人的好意。年薪15000美元的职务是不好轻易拒绝的,这是他任布拉格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年俸的25倍。
1892年9月27日,德沃夏克登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欢迎他的有300人组成的庞大合唱团和多达80人的管弦乐团,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规模。德沃夏克对主人的热情好客并不感到意外,倒是纽约港口停泊的大轮船给他印象深刻。19世纪末的美国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庞大的金融体系,百老汇大街上电话线、电报线密布如织,街面上车水马龙,灯光彻夜通明,金融机构鳞次栉比,证券交易所里不断上演着欲望的悲喜剧。这一切与安然闲适的布拉格形成强烈的反差。德沃夏克到纽约恰好比海顿到伦敦晚一百年,但工业化社会对人的冲击作用大致相当。
德沃夏克不愧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他总是以民族音乐家的角度观察事物。在美国他很快注意到黑人音乐的旋律,并断言在黑人音乐的基础上将产生属于美国的新音乐。他写道:“在美国黑人的曲调中,我发现了一个伟大而高尚的音乐学派所需要的一切。这些美丽而丰富的主旋律是这块土地上的产物,它们是美国式的,是美国的民歌,你们的作曲家必须求助于它们。”在纽约音乐学院的作曲课上,德沃夏克尽力把学生引向民族主义乐派。
到美国后三个月,德沃夏克开始为一部新的交响曲起稿,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八部交响曲。美国音乐界的朋友们热切地希望德沃夏克写一部能代表美国精神的作品。历史短浅、缺乏文化根基的美国人急切地需要一部奠基之作,来建立自己的音乐文化。1893年5月,交响曲总谱完成,这年的12月,第九交响曲在纽约首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闻媒体对演出的盛况作了热情的报道,并宣布“属于美国自己的交响曲”诞生了。应萨尔伯夫人的请求,德沃夏克在出版第九交响曲时加上了“自新世界”的副标题。
《第九交响曲》在中国一直通行着两个副题,一个是根据原文译出的“自新世界”,另一个是含糊其辞的“自新大陆”,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据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德沃夏克是其中之一。中国响应号召,决定演出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当时中国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美国被当作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解放初期人们常用“新社会”、“旧社会”,“新世界”、“旧世界”来作今昔对比。当此之时演出《第九交响曲》,副题的“新世界”很有美化敌人之嫌,主事者便搞了个文字游戏,换成了“新大陆”,从那以后,“新大陆交响曲”这个名称便在中国流传下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以避一时之讳的“新大陆”一直沿用,许多很严肃的正式出版物上,还在使用这个假的、错误的曲名,李德伦先生认为应该纠正。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公演以后,各种溢美之词蜂拥而至,其中主要夹带着按照美国人的愿望的评论,他们为了证明这是一部“美国交响乐”,对《第九交响曲》作出曲解的分析和评论,对乐曲本身妄加穿凿,说音乐素材取自于美国黑人音乐。对这些评论,作曲家本人予以坚决反对。他说:“我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黑人或印第安人旋律,我只是在作品中写了体现印第安音乐特色的自己的主题。我用现代节奏、和声、对位和乐队音色的一切手段来发展他们。”
作为民族主义音乐家的德沃夏克一向珍视民间音乐的节奏、旋律,对黑人音乐的评价更是充满热情,但他首先是一位捷克人,他具有浓厚的捷克人气质,不会去写一部“美国交响曲”。德沃夏克对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有强烈的印象,对这块迅速发展的土地上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命运深表同情,这些在《第九交响曲》里都有情绪化的表现,而非形态上的表现。德沃夏克在美国尽管待遇优厚工作愉快,但他总在怀念遥远的波希米亚家乡,《自新世界》交响曲里也大量地寄托了怀乡情绪,表现最突出的是第二乐章中,着名的英国管奏出的主题。所以,德沃夏克的音乐,不论是在英国写的还是在美国写的,都是捷克音乐。德沃夏克在美国两年半时间的生活应该说是愉快的,在那里他尽享一个成功者受到的种种礼遇,但是他总被思乡情绪包围,他在美国写的另一部成功之作《大提琴协奏曲》里也浸透着这种情绪。所以,尽管人们想方设法一再挽留,德沃夏克还是回到了波希米亚家乡。
在德沃夏克离开美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本土产生的音乐逐渐成长起来,出现了戈什温、科普兰、巴伯、格罗菲等一批世界知名作曲家。美国音乐也正如德沃夏克当年预言的那样,从黑人音乐和印第安音乐里吸取丰富的营养,黑人灵歌、布鲁斯、爵士乐对美国现代音乐的形成发生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不管德沃夏克本人同意与否,美国人还是把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当作美国交响音乐的基石。他们的交响乐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中演奏最多的是这部交响曲,近二十年来,几个美国大型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数次演奏此曲,精心安排之下,似乎还是暗含着把此曲献给自己的意味。
《新世界交响曲》里有两个音乐主题被改编成流行的短曲,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歌曲《思故乡》,是由第二乐章改编的,另一段是第四乐章高亢兴奋的主题改编的铜管乐,经常在各种庆典活动中演奏,也是学生乐团喜爱排演的曲目。
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
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是他音乐生涯的掩卷之作,也是他一生精神历程的艺术总结。《第六交响曲》使他达到个人的艺术顶峰,也把他带上西归之路。在他指挥首演这部交响曲之后九天,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突然去世,按照音乐家传记上的记载,他死于霍乱。关于柴科夫斯基的死因,还有一些传闻和揣度,但都只是猜测,无法证实,根据他临终时医生的诊断,他的直接死因是霍乱。
《第六交响曲》的标题是“悲怆”,这两个字很贴切地表明了这部交响曲的情绪基调,而这样的音乐内容又是柴科夫斯基性格的表现。有评论家说他是“感伤作曲家”,这只部分地说出了柴科夫斯基的性格特点,在他心灵深处也有着开朗奔放的一面,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影子。“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这样的文学命题用到柴科夫斯基身上是很恰当的。
《第六交响曲》最初没有标题,柴科夫斯基写完全曲之后对这部作品很满意,经过首演之后总谱即将送到莫斯科去出版,他想给交响曲定一个标题,又拿不定主意。作曲家的弟弟莫代斯特提议用“悲剧”作为标题,但柴科夫斯基不太满意,就在他犹豫不决时,莫代斯特又想起另一个词“悲怆”,柴科夫斯基听了如获至宝,当即在总谱上添上了这个标题。但是,在谱子寄出之后,他又改了主意,写信给出版商,说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请改成“第六交响曲”,不加标题。然而敏感的出版商决不会放弃“悲怆”这个抢眼的字眼儿,他对这个补充请求置之不理,于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就以《悲怆》这个标题留传于世。
《悲怆》交响曲反映人的生活苦难,人对悲剧命运的抗拒,其中有生命的激情,有追求的冲动,有对幸福和欢乐的向往,而残酷的现实则无情地压抑人性的活力。作品着力表现人类命运的苦难历程,但音乐不采用戏剧性的冲突,没有疾风暴雨式的强烈斗争,只是营造一种阴暗的力量,给人的精神以无形而沉重的压力,好像在用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慢地宰割人的灵魂,想要抗拒是不可能的,只有反复咀嚼内心的痛苦,生命之火在极大的痛苦中一点点地熄灭。这就是《第六交响曲》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柴科夫斯基写《第六交响曲》是在1892年到1893年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整个心灵都放到了这部作品中”,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现在全力投入新作,简直离不开它,我相信它正在诞生,成为我的最佳作品。”这部交响曲的确堪称柴科夫斯基的登峰造极之作,社会公认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同时也用这部作品的内容与柴科夫斯基的个人生活进行对应的联系,尤其认为梅克夫人中断与柴科夫斯基的关系这件事,是引发柴科夫斯基写《第六交响曲》和他死亡的关键。
封·梅克夫人是柴科夫斯基的精神支柱和经济后盾,从1876到1890的14年里,她给予柴科夫斯基无数的帮助,两人几乎完全不曾谋面,往来信件多达数千封。柴科夫斯基把梅克夫人视为理想的化身,也把她当作世界上最理解他的人。两人保持关系的十几年是柴科夫斯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每有新作,都在信里先向梅克夫人介绍,对重要作品,则经常征求梅克夫人的意见,报告自己的想法和作曲的进展,梅克夫人也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这些信件后来成了研究柴科夫斯基的重要资料。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世所罕见,但是这个保持了十几年的友谊突然中断,梅克夫人以经济危机为理由停止了对柴科夫斯基的赞助,连通信也不再继续。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柴科夫斯基不明白为什么梅克夫人会出此断然之举,而且,即使经济援助停止,友谊也仍可保持。他一直试图恢复与梅克夫人的联系,但毫无结果。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发现梅克夫人并没有破产,她经营的铁路运转正常,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侮辱,加剧了他的心理病态,本来就神经质的内向忧郁性格更加发展,这加速了他的死亡。因此,在《悲怆交响曲》里,没有凯旋雄壮的末乐章,取而代之的是阴郁绝望的告别,是悲怆的安魂曲。
仅仅把对《第六交响曲》的理解局限于作曲家个人生活的遭际,就会低估柴科夫斯基音乐的思想价值。柴科夫斯基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处于一个黑暗时期,这个时期的俄国君主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对军队和警察感兴趣。两个沙皇同样地没知识,同样地看不起知识,而这个时期来自西欧的自由民主思想正由俄国知识分子传播到俄国社会,社会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地反映到知识分子与沙皇的黑暗统治的冲突上了。当局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杂志被查封,进步知识分子被流放,柴科夫斯基虽然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但是他对阴郁黑暗的社会现实没有无动于衷,他曾说过:“做一名艺术家是幸运的,因为在我们切身体会到的极为残酷的时代里,只有艺术,能使我们摆脱沉闷的现实。”有人评论说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把他带到了“坟墓的边缘”,而真正把他送进坟墓的则是沙皇统治下的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暗。柴科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里说:“天气很坏——有雾,无涯的雨,潮湿。一举步就碰到哥萨克的巡逻兵,好像我们是被围困似的。……这是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柴科夫斯基一生中创作的音乐里贯穿的忧郁、感伤和压抑,都来自于这个恐怖的时代,可怕的时代。
《第六交响曲》的“悲怆”情绪最集中地表现在乐曲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缓慢的柔板乐章,弥漫着痛不欲生的悲哀气氛,音乐虽然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不是消极地走向死亡,而是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作痛苦的诀别,从而表现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反映了19世纪晚期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专制下悲愤绝望的情绪。
舒曼: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舒曼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由十三首小品组成,这部套曲说起来知道的人不少,但熟悉全部内容的不会太多,一般人们只是熟悉其中的第七首《梦幻曲》。这是一首美丽温馨的小品,如同摇篮曲一般恬静安详,它的曲调在世界各国家喻户晓,即使不太关心音乐的人,听到《梦幻曲》也能随着哼唱,人们常说的脍炙人口,大约就是这个境界。《童年情景》之所以成为一部名曲,主要得益于《梦幻曲》的流行。
套曲《童年情景》是一部很私人化的作品,确切地说,是舒曼写给他热恋中的情人克拉拉·维克的情书。舒曼18岁从家乡茨维考到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同时,跟钢琴家弗里德利希·维克学钢琴,这时维克的女儿克拉拉只有9岁,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钢琴已经弹得很出色了。两年以后,舒曼的母亲不再阻挠他学音乐,舒曼全身心地投入音乐,他住到老师维克先生家里,专注于钢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