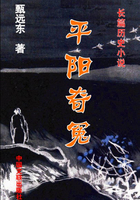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纠缠,您说的?这是不可想象的。据他说,阿克尔曼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能干人,活动能力强的人。”
“阿克尔曼?他根本不再是股东了。现在的股东是波特尔。他并不是德国人,而是美国人。”
“他为什么跟这个可靠的德国人翻脸,而且……”
“为什么?”她打断我的话,“我现在才想起来,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下车的时候,没注意我们门上的牌子吗?”
“没有。”
“意思就是说,您不知道我的丈夫现在是各州商业银行的股东?”
“一无所知。但是,他应该附带拥有油泽。”
“不。他与阿克尔曼及其公司分道扬镖了。”
“为什么?”
“他不再喜欢沼泽了。我们认识了波特尔,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生意人,并且服从我的丈夫,虽然他把许多工作都推到我丈夫身上。我丈夫以三百万美元出让了油泽的产权。我们迁移到城市里,用这笔钱成立了各州商业银行。”
“波特尔付了多少?”
“没有付。我丈夫出钱,波特尔出力。您知道,维尔纳没有太多的商业知识。”
“那他为什么愿意放弃可靠的,换成不可靠的?”
“那您现在认为我们现在的地位是不可靠的?”
“对现在的生意,我不能做出判断,因为不了解。我只知道,我非常信任他以前的邻居阿克尔曼。”
“波特尔也赢得了信任。我听见我父母来了。当着他们的面,别谈这类事情。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他们的担心可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升降设备把两个老人送上来了。
“我们到了。”老福格尔一边对我们说,一边带着他的妻子进来,“我还不会说英语。懂德语的车夫很少。我们不断地兜圈子,那小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门。你们不要立刻离开。”
“可惜的是,我们只能与亲爱的同胞分享短暂的欢乐,”马尔塔说,“他很快要走。”
“那他就别再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让他马上离开。”
“我们已经谈过了。首先,我们想请先生们至少待到吃晚饭。我和母亲去做饭,爸,您带先生们到抽烟室去参观一下,聊聊天。”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抽烟室也布置得和别的房间一样金碧辉煌。老福格尔在这些家具、图画、壁灯之间,觉得一点也不自在。他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比较好,最后只好坐到一个摇椅上面,因为它是最低的,也是最舒服的。因为在家乡的茅屋里,他通常坐在矮板凳上。
我拿起一支雪茄,温内图照着我做。很可惜的是,他不能参加我们的谈话。
“现在,我们是单独谈话了,”老人开始转入正题,“可以开诚布公。您对百万富翁,即我的女婿究竟是怎么看的?”
“我不是很了解他。”
“我认为,您是在那边认识他的。对吗?”
“时间很短。从那时以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唔,是的!他至少应该给您写封信。但是他不公开谈论您,我的女儿一提到您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
“他生气的理由是什么?”
“没有,没有任何理由。他抽烟喝酒,整天云里雾里。”
“哎呀!这是非常糟糕的。”
“是的,很糟。可能是母亲的遗传,他母亲死于震颤性谵妄。”
“您的女儿究竟是怎么看的?”
“她说了根本不管用。只能恳求他别做傻事。”
“是这样?那太可悲了,这一辈子……”
“简直像狗和猫一样!”他插嘴说,“您知道,我们可以赚数百万。他住在下面,我女儿住在上面。他们整天不说一句话,顶多是吃饭的时候说上一两句。”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在油泽时,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时,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和睦。自从有了这个波特尔和公司以来,生活过得奢侈多了。您知道,这个波特尔使我很伤脑筋。他经常给我的女儿大包大包的东西。”
“是不是您的女儿抱怨她丈夫事情太多?”
“那是胡说八道,您不要相信。波特尔管着全部业务,跑腿,写字,日夜忙个不停。维尔纳只会发牢骚。他是什么俱乐部和其他社团成员,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他不会工作,虽然是百万富翁,却不会理财。波特尔什么都帮他干!”
谈话一直进行着。无论天南海北,老人的话题都是围绕百万财富和女婿,却不知道,他这些话,让我看到了生意与家庭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害怕和担忧。马尔塔是不是爱她的丈夫,这我不能肯定,即使不爱,她也会竭力掩饰。这两口子开始时还相处得非常融洽非常好。后来,出现了波特尔。我怀疑这个美国佬看中了维尔纳的财产。维尔纳看来对他非常信任,一步一步掉入了他设计的陷阱。在这个陷阱里,他肯定会破产。波特尔极有可能也把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弄到手。
我能够做什么呢?揭露这个人,需要时间,而且可能为时已晚。因为,那样我得充分了解生意上的情况。他们两个无论如何会反对,从而很容易使我感到恼火。老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进行了反复思考,决定不卷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福格尔太太来叫我们吃饭。马尔塔没有派佣人来,她想要我们全部保持在自己人圈子里。这是一顿简单的饭菜,我观察到,这个年轻女子内心又有了愉快的感觉。饭后,我们被允许在餐厅抽一支雪茄。马尔塔引我们到旁边的音乐室。刚开始是风琴演奏,然后响起了这位前女歌手美妙的嗓音。她唱的是一曲德国民歌。
我背对大门,温内图面向我,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听。他不懂德语,却被悦耳的歌声所陶醉。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异样的表情。我发现他锐利的目光对着门口,仿佛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很快扭过头,只见我后面敞开的门口站着两个男人,我马上判断出那是石油大王和波特尔。波特尔衣冠楚楚,面部表现出一种潜在的紧张情绪。维尔纳两眼通红,像公牛一样盯着我,晃来晃去。我们马上看出,他喝醉了。
由于我穿的是墨西哥服装,在我扭头之前,他没有辨认出我。现在,他看到我的脸,马上握紧两只拳头,一边跌跌撞撞地扑过来,一边叫:
“你这个恶棍,想迷惑我的太太。这个人已经在她身边?她唱歌给他听?统统是魔鬼。波特尔,抓住他!把他的骨头全部砸碎!”
波特尔也朝我扑来。这时,马尔塔飞跑过来,站到我和他们中间,伸开手臂挡住他们:“不要再过来一步,你不仅是在侮辱我,也是在侮辱你自己。”
“都给我滚开!”维尔纳推开她,“我先和他讲话,然后也会找你谈。”
“我偶然碰上了这位先生,便邀请他来。你想骂我们的客人吗?”
“客人?”他嘲笑道,“波特尔才是我的客人。我邀请他一个人。波特尔,过来!我们打他,打到他再也不能叫喊为止。滚开,你这臭婆娘!”
他抓住她的胳膊,却马上松了手,因为在他旁边站着温内图。这位首领威严的表情,一下就足以让两个进攻者后退好几步。
“你们谁是这栋楼的主人?”阿帕奇人用英语问。
“我。”维尔纳回答,这时他极力使自己不跌跌撞撞,站稳脚。
“我是温内图,阿帕奇人首领。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你们全是魔鬼!温内图,温内图!”
“您认识我,就请您注意我对您讲的话。这儿站着我的朋友,老铁手兄弟,我们遇然遇见您的太太,她邀请我们到这儿来。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为的是能荣幸地见您一面。我们坐在这儿,她唱了一支歌。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你要报酬,温内图将给以报酬。我的权力一直达到这个伟大国家的中部。你只要对她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的阿帕奇部落中就会有人用刀子来做出相应的回答。现在,你知道我想干什么?”
然后,他从腰带里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桌子上:
“这是我们在你这儿吃东西的钱。老铁手和温内图不想让你赠送,因为他们比你富。我的话讲完了!”
维尔纳不敢说话,像个挨惩罚的小学生一样端正的站着。波特尔看来很生气,却暗地里感到高兴。我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问他:
“老板,您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他回答。
“我看出了您的意图。您可要真心实意对待您的股东,否则,您不会得到我的恩惠!我还会来找您的,不是按照你书上和公文上的规定,而是按照严格的北美草原法律。您的商业朋友将会听我讲述您的情况。不要错误地以为他不了解您,也不要以为,我会像在那边对他一样宽宏大量。为了让您了解我的认真程度,我要在您的肌肉上盖上老铁手的图章。”
我把右手压着他的上臂,压得紧紧的,他发出痛苦的叫喊声。然后,我和温内图向门口走去。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厅。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感,这座金壁辉煌的宫殿有一天将会变得家徒四壁。
第二天,我们前往旧金山。三个月后,我们在红罗克湾告别,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别居然多达两年半之久。在我们分别之前,我们准确地商量了何时、何地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