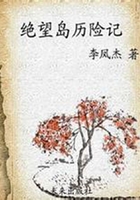提起伽玛,我不由就会想起曾就读的中学和大学所在城市的画面。欧洲有些地方总会给地理和历史老师惹麻烦,尤其像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Trieste),靠意大利东北岸和南斯拉夫西北岸、萨尔盆地萨尔盆地(Saarbeckengebiet),1920-1935年间,法国和英国受国际联盟委托所占领及管治的德国地区。1935年经全民公投,回归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16个邦中最北面的一个邦。等地。维尔诺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也常给人添堵,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今天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而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下隐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俄国人正有效地实现沙皇扩张领土的指令。
我上中学、大学时,维尔诺城归属于波兰,它隐藏在林木葱郁的大盆地中,在远处的低谷中掩映着繁茂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高耸入云的数十个天主教教堂塔尖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旅行者眼前,相互衬托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以金黄和白色与松树幽暗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传说有一位立陶宛统领去密林中打猎,在篝火旁睡着了,做了一个预言性的梦。受到梦的影响,这位统领在自己睡着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那就是维尔诺。经过若干世纪,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特色,即“森林覆盖之城”。在它周围铺展开的是欧洲的一个偏僻省份,居民使用波兰语、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或是三种语言混杂着说,并保留了其他地方早已遗忘的风俗习惯。当然,我用的都是过去时,因为,这座我童年生活过的城市,如今就像庞贝城被熔岩掩埋了一样,多数世居此地的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被迫迁到德国人离开后的西部地区。那些出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如今行走在维尔诺的街道上,而那些立陶宛王公和波兰国王建造的教堂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在我求学的那段时间,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大屠杀和大放逐。那时,维尔诺城的生活按照某种慢于政府更迭、王国边界改变的节奏发展。大学、主教的宫殿和大教堂是城里备受尊崇的建筑,它们混合了意大利和近东的建筑风格。星期天,成群虔诚的信众挤满了狭窄的街道,街道上方的城门上建有一座礼拜堂,礼拜堂上挂有一幅着名的、曾经发生过奇迹的圣母马利亚画像。星期五晚上,在犹太人居住的狭窄街道上,你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们家家都围坐在烛光旁,希伯来先知们的教诲则在古老的犹太教教堂里回响。这里曾是欧洲犹太文学与犹太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假日期间,盛大的市集吸引了来自邻近村庄的农民,他们在小广场上展示自己的手工木器雕刻和草药,以及用细线串在一起的名为“奥布瓦然卡”的小脆饼,无论这些小脆饼是在哪里烤制的,人们都叫它“奥布瓦然卡”,一直以来,它都是这座小镇的特色小吃,证明这儿有非常好的面包房。很久以前,这里还曾有座“驯熊学校”,他们会在此地训练狗熊。冬季,有些坡度较大的街道就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滑雪场,他们红红绿绿的外衣,与太阳光照射下带有玫瑰色的白雪相互辉映。
大学的建筑墙壁厚实,教室都是低矮的拱顶。浓荫蔽日的校园恍若迷宫,初来乍到者很容易迷路,那些拱顶建筑物和长廊可以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Bologna),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和帕多瓦帕多瓦(Padova),位于意大利北部,为帕多瓦省的首府以及经济和交通要冲。媲美。从前,这里是由波兰国王庇护的耶稣会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那位国王曾与莫斯科进行过浴血奋战,并取得了胜利。当我到这里念大学时,教授多是世俗的,在此求学的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小地主、小承租人家庭或犹太商人家庭。
我就是在那里,在那座大厦里认识伽玛的。伽玛是个举止粗鲁、满脸通红的男孩,性情暴躁,嗓门很大。如果说维尔诺城是个外省城市的话,那么对那些离开偏僻乡村到此读书求学的人们来说,他们就更具有双重的外省人身份。泥泞的乡村道路,尤其在春秋两季,简直无法行走;农民的马常常被机动车吓得惊恐不已;在许多村庄,人们家里仍按旧习用松明火把照明。除了农活以外,人们只知道去森林伐木和制作手工产品。伽玛出生在农村,父亲是波兰军队的退休军官,家里拥有一座农场,这个家族很久以前就住在这个地区,当地的古老贵族名册里还可以找到他家族的姓氏。伽玛的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环境下长大,且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不像他的多数同学那样信奉天主教。
我们之间第一次交谈时,我并没有预感到日后密切的交往。对文学的共同兴趣虽然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他的举止、刺耳的大嗓门(他不懂得用正常语调说话),还有从他那粗嗓门中所表达出的观点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粗藤杖,那是参与排犹活动的年轻人都喜欢的一种武器。伽玛是一个强烈的排犹主义者,这是他的政治纲领,但我十分鄙视这类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傻瓜。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除思考的责任而大叫大嚷,激发不同民族群体的相互仇视,以转移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他们某些言论能留给人特殊的印象。亲身经历后,你会感到,他们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论到种族主义时,伽玛双脚站在街道的圆石路面,把随身携带的藤杖靠在排水沟边上,大肆议论起血统和土地来。他说不应该把国家权力交给全体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讲何种民族语言,国家的权力只能交给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这个民族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自身的血统遭到玷污。也许他的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弥补他自身的缺陷。他是混血儿,半俄罗斯血统以及东正教信仰必定会使他那些土生土长的同学感到不快。伽玛的声音飞过我头顶,明显带有高人一等的味道。我提出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让他感到不悦,他认为我是那种长于思考却拙于行动的人;至于他,则是一心要做点什么事的人。那是1931年,我们两个人都很年轻、贫穷,对于今后我们将身陷其中的种种特殊事件仍一无所知。
1949年,我到西方某国的首都去拜访伽玛,那时他担任红色波兰驻西欧某国大使,是个受党信任的人物。他的大使官邸锻铸的铁门紧锁着。我按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从铁门的窥视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铁门打开时发出“嘎嘎”声,眼前出现的是宽敞的院子,院里停着几部锃亮的汽车,大门入口的左边是值班卫兵的岗亭,他用手枪武装自己,站在那里应付一切意外情况。站立在院子中央,整栋建筑的正面及其两翼尽收眼底。这是该国富有魅力的首都最漂亮的宫殿之一,是18世纪某位大贵族为其情人建造的。建筑物内依然保持着自己过去的特点。宽敞的大厅,墙壁覆盖着镀金的墙裙,家具、地毯及挂毯等也都是来自18世纪的古董。伽玛在一个金碧辉煌、大理石缀饰的房间里接待我,他显得诚挚大方,岁月的磨砺改变了他从前那种粗鲁的风格,他似乎变得有些矫揉造作。在这座宫殿里,伽玛有自己的起居室、会客厅和办公室,西方科学和艺术界许多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常客。一位着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谈到他时,形容他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思想自由,摆脱了盲从。不少知识精英也都抱有同样看法,这些人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至于那些着名的共产主义文学巨擘对伽玛更是赞赏有加,既是因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东方使者,而且也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洞察力,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学问题做出评价。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伽玛的过去,也不知道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从一个在欧洲最偏僻的角落受教育成长起来的粗野年轻人,成为这栋18世纪宫殿的主人。
伽玛在这个西欧国家的首都过得称心如意。他喜欢逛夜总会、酒吧和卡巴莱餐馆卡巴莱餐馆,有歌舞和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只要他一走进那些地方的大门,老板便会向他鞠躬并领他到最好的座位上去。每当看见这位男子放肆地眯起一双细眼、透过浸在冰桶里的香槟酒瓶来打量人们时,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成功保全了自己部分产业的英国乡绅。伽玛个子很高,稍微有点驼背,有一张某类男人特有的红润长脸,通常这类男人会随身带着猎枪和几条猎狗消磨时光。他的外貌很符合他出身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过去那种波兰小贵族,他们热中于打猎、豪饮,从事政治活动时会在波兰语中混杂着拉丁语发表演说,并能以合唱式的抗议喧嚣战胜对手,而在必要时——则会拔出佩刀站在掀翻的桌椅中间进行决斗。他那种安闲自得的动作显示出他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优哉游哉之人。对自己的下属——那些出于对公事的责任感陪伴他流连各家夜总会的人,伽玛的态度是既仁慈又轻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伽玛有时会因为情绪极佳而捏捏使馆秘书的鼻子,或在他们屁股上重重地拍一下;有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这时他红润的脸膛会涨得发紫,蓝眼睛里充满血丝,而他的嗓音则会重现过去那种尖利狂野的声调。如果西方的外交官、学者、艺术家认为他是个打心眼里想过奢侈生活而又不太复杂的轻浮儿,这也不足为奇。甚至他某些不得体的举动,在这些人眼中也是出自他宽宏、开放的天性,这种天性有时会因过分真诚而构成冒犯,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伪善无关。当他谈及其他共产党人认为敏感的话题时,他却能表现得泰然自若、毫不窘迫,因此赢得了对谈者的信任。访问大使馆之后,这些人互相交流看法,认为伽玛绝非共产主义者,即使是——也仅属于那种视野开阔、思想文明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在这里却犯了一个错误。对伽玛来说,这只是他出于本性的表演。他有意识地利用他的乡绅外表,以娴熟的技巧来表演他的纯朴和善良。只有那些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才能穿透其表面的坦率,洞察到他的冷酷算计。伽玛怀里时刻藏着一把无形的匕首,随时都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打击。不过,这把与他日夜形影不离的匕首的寒气同时也冻冷了他的心,意识到自己是在装腔作势做游戏也让他永远快乐不起来。
伽玛以能迷死人的微笑,让那些曾被怀疑不想回到铁幕统治下的外交官相信了他的关怀。伽玛常会在那些外交官面前猛烈抨击华沙的那帮傻瓜,说他们根本不懂应该如何在西方处理事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提议陪同一个不愿回国的外交官返回华沙,用几天的时间去向那帮白痴说明,该如何解决成为大量电报往来原因的某个问题。此时,这个轻率的人心中暗想:明摆着,伽玛是善意的,而我每次返回华沙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政府的,因此还一再延长了在国外的任期。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这样做没有任何危险。于是在欢快的气氛中,该外交官与伽玛说笑着一起登上了飞机。一到华沙机场,外交官就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从此把妻儿留在了国外。每当伽玛完成了任务,他就会立即返身搭下一个航班飞离华沙。监视自己下属的忠诚是伽玛的职责中最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那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得到信任的标志。伽玛的匕首功效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是,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智慧时,他的匕首就会去履行政治警察的任务。
我们还是再回到从前去看看吧。那时伽玛还从未尝过香槟的味道,我们用餐的大学食堂,就像这座保存了古老传统的大学的许多机构一样有个拉丁文名字,叫“门撒”(即天文学的山案座)。那时食堂的饭菜很便宜,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便宜没好货。”那时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写打油诗,讽刺“肉丸硬得像石头,菜汤清淡有如水”。在劣质烟的弥漫中,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诗歌,并互送月桂冠,这些东西除了我们之外没人会感兴趣。我们这一群人——有些是初学写作的作家,希望在未来能够出人头地,也希望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当大多数同学只关心自己的功课,或将来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时,我们则渴求名扬四海,幻想改造世界。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获得聪明才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打乱了内在的平衡。我们这群人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都曾受到过深刻伤害,每个人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但基本处境却一样:有些事情使得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无法与其他同年龄的人和谐相处,有些事情则使我们自觉与人“有别”。这驱使我们想要寻求某种补偿,而追究一个人成为野心家的内在原因,并非易事。我觉得,当时还是文学系学生,并已开始写诗的伽玛,对自己的家庭境况有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此外,伽玛念中学时,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意外打死了一位朋友,此事所引起的负疚感可能对他今后所做的决定影响很大,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